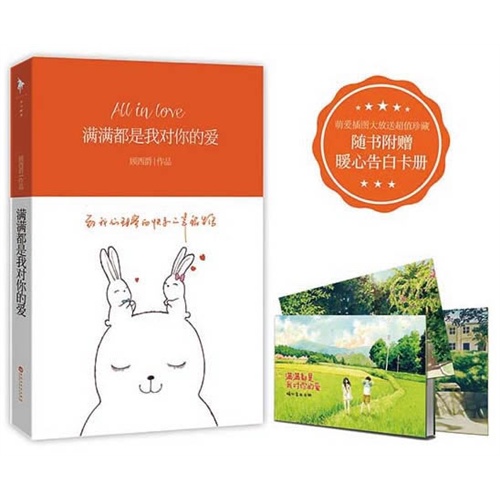对你是离别,对我是等待 故影(出书版) 作者:渥丹 脉脉-第1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还是有点慌,心里没底,但不管怎么说,事情总还是要做。”
“上午等你的时候隔着门上的玻璃看了一眼,涂完油漆准备做什么?”
“用喷枪上色……设计图的要求是要喷成烟花的效果。我之前没做过喷绘,林永年倒是有这方面的经验,等一下回去看看油漆干得怎么样了,如果不行,我们就准备等刘老师来了问问他的意见。”
“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我去看一看?”
郁宁一时没有接话,看神色也有些为难。
贺臻做这一行这么久,业内的规矩和忌讳都很清楚,见郁宁犹豫不决,笑一笑又补充说:“不要紧,就算你不说,设计图我也是不会看的。”
“贺臻,我当然不是信不过你,其实是在抱怨自己没用,听到你说要去看一眼,暗自还有些窃喜,以你的性格,如果别人有求于你,或是请你出个主意,你总是会乐于答应的。我是在犹豫惭愧这个,这不是你的工作,不该麻烦你的。”
贺臻大笑,伸手轻轻拍了拍郁宁的肩头:“你不要想得太复杂了,就是去看一眼,我未必能给你提什么意见,朋友之间——现在又算是半个同行,互相切磋启发一下,总是可以的吧。”
“你看,你总是能把自己的善意说得让人无可拒绝。”
“这也算是我为数不多的优点之一了吧。”贺臻已经走在了前面,“走吧,去看一眼。”
回到作业间的时候林永年已经先一步到了,看见跟在郁宁身后进来的贺臻,不由得露出诧异的神色。郁宁先行解释:“贺臻是我在严可铭那里工作时候的同事,我带他来看一看,不会破坏规矩的。”
林永年半晌才点了一下头,脸色稍霁;贺臻吸了口气,鼻翼抽动了几下,才走到已经上好漆的其中一块木板前,伸出手来摸了一下,然后点点头,自言自语一般说开了:“还没干透,但是要赶进度的话,已经可以上第二层了。准备用这个喷枪?”
他弯下腰,拾起放在林永年脚边的喷枪,又转头对郁宁说:“我没看图纸,不知道最终他要的效果是什么样的。如果是‘像烟火一样’,与其用这个,不如找个老式拖把来,直接在上面刷,玫鑫和天平不一样,无论是舞台还是观众席都大太多了,背景的颜色要适当鲜艳一点,也方便灯光师打光。”
在实地经验上郁宁和贺臻自然不能同日而语。听他这样建议,她还没来得及表示别的意见,就忍不住噗的一下笑开了,一边笑一边解释:“我就是想到了写字用的提斗。”
“有点这个意思。你是学国画的,大可以当作书法或者写意山水来搞。现代艺术嘛,又是做背景,成品和图纸总是会有偏差的,取其真意未尝不可。”他前一刻姿态还很是潇洒,忽然脸色一变,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背,下一刻就露出苦笑来,“对不住,我油漆过敏,这屋子不能再待了。”
郁宁眼尖,瞄见他手背上的皮肤红了一大块,顿时吓了一跳,二话不说牵着人就往外走:“……你不早说!”
短短的几分钟工夫里贺臻连脸上的皮肤也开始起反应了。郁宁没想到他对油漆的过敏程度这么深,皱着眉头瞪他:“你怎么不说过敏的事?难受吧?要不要去医院?”
贺臻连眼白都红了,却还是一副混不在意的架势:“很久没发作,以为问题不大……我拿了东西后去一趟药店好了,不要紧,你别瞪我啊。”
“明知道过敏还去摸油漆,简直是胡闹。”
听到郁宁这样说,贺臻倒是笑了:“‘明知道’可还要去做的事情多了,不就是靠‘心甘情愿’撑腰嘛……这儿还是有油漆味儿,我先逃了,周末再见。你多保重。”
郁宁被他那句话说得一个激灵,正要再说,贺臻已然洒脱地挥挥手,快步走了。
因为告别前那一句话,郁宁回到工作间时有些心不在焉,不防耳边又来了一句:“和男朋友吵架了?”
她猛地抬头,林永年的视线锐利得陌生。她不由愕然,然后失笑着摇头:“他不是我男朋友。”
“那你见他这么欢天喜地他见你又双眼发光?”
他说起话来也是美院里那些才子们的路数,也不知道是太一针见血还是在恃美装疯,平时郁宁听他这样说话还觉得有趣,真正落到自己头上才知道真是刺耳,她敛了笑容,语调也冷淡下来:“很投缘的朋友,也算我半个老师,有一阵没联系了。刘老师昨天说他三点会来,我们先试试看喷涂的效果吧?”
因为这两句没头没脑的话,郁宁这个下午都没怎么和林永年搭话,她自己也知道这是在发没道理的虚火,但这阵火硬是下不去而林永年在学校里被身边的仰慕者们也是宠坏了,郁宁不搭理他,他自然不会先去讲和。喷涂试了很久效果还是不尽如人意,两个人又都憋着气,直到刘师傅过来,看了他们实验的几个样本,最后拍板说:“不用喷枪了,拿大号的美工刷直接刷吧,或者先试试看直接泼油漆上去,如果效果可以,这么搞也行。”
没想到“简单粗暴”的方法用起来效果当真不错,最初郁宁还有点束手束脚,泼得矜持,林永年却赌气似的半桶油漆直接往白漆木板上泼,一下子就像是打翻了染料铺,满目姹紫嫣红,别有一种天然的放诞和喧嚣。
到后来两个人干脆把所有的木板一起排开,尽量摆成它们将在舞台上呈现的最终形态,商量起哪一块应该先泼哪一种颜色,又该泼多少,简直是有一种幼儿淘气使坏的快感,而之前那点莫名而起的冷战,也早不知道抛到哪一重天外去了。
那一次的工作完成得很圆满,自此以后她在新诚的实习愈发顺利,有了更多的工作机会,结识了更多的朋友;同时她开始着手毕业设计,和导师商量之后,定下仿宋人院本笔意,画一幅团扇的扇面。绢面设色,白上画白,最是考验眼力和笔力,郁宁白天去实习,夜里就坐在画室里一笔笔地描绘那一双误入白芍药深处的白鹭,心情是从未有过的安宁。
到了周末,如果得闲,又或者是贺臻得闲,总是要找个机会见一面的。自从她请他吃饭还邀了魏萱作陪,这件事情就变得绵绵不绝起来,她请他吃个饭,下次贺臻就要找个机会请回来,再不然就是魏萱做东,看场夜电影然后吃宵夜,吃完还能再看一场通宵电影,然后三个人在深夜的街头笑着聊很久的天走很长的路,才打车去取车回程。在一起吃得多也玩得熟了,有一天酒足饭饱之余魏萱提议,这种有益于身心健康人类团结世界和平的聚餐活动必须固定下来,于是就这么干脆变成了每周必有一次的固定活动。再后来,随着郁宁在新诚待的时间变长,渐渐也有了些娱乐公司员工会有的福利,什么没完售的戏票啊,公映前的排练场啊,总能分到一两张。这些票大多时候是约着魏萱一起去,有时魏萱和男朋友约会,郁宁起先是把两张票都给贺臻,但每次贺臻都退回一张给她,还笑着问“怎么和魏萱能去看和我就不行”,郁宁想想也是,从此要是魏萱不能赴约,她就直接找到贺臻,两个人结伴看戏听音乐会去。
用这个办法,郁宁几个月里看足了新诚主办或是赞助的各种演出,贺臻手头也有票,张张位置都好,最好的一次回是他和严可铭参与设计的《蝴蝶夫人》,竟弄来舞台左侧三楼小包厢的票,他们两个再加上魏萱和伊凡,四个人正好坐满,听得如痴如醉,明明来之前大吃了一顿,歌剧散场后个个兴奋得双眼发亮,又不约而同提议再去吃喝一顿……
那个春天和随后而来的夏天,在接下来的很多年里都是郁宁记忆里最快活最肆意的时刻,有无尽的精力,欢笑,胃口和欲望,后来她离那段岁月无可避免的越来越远,终是要挥手作别,但对它的印象,却从不曾有过一刻的褪色。
第八章
这个城市的春天很短,总是一过了冬,春天就跟着悄悄溜过去了,夏天又很长,漫长得让人觉得能一辈子都活在这个夏天里。
郁宁走进约好的餐厅的时候心思有些游离,搜了一圈没看到人,正要打电话,身后传来一声:“郁宁,这里。”
她闻声回头,看见贺臻后脚步停了一停,才匆匆迈动步子,走到他在的这张桌上:“魏萱和伊凡呢?”
“魏萱打电话来,和伊凡吵架了,她说不来了,免得扫兴。”
郁宁听完第一反应是去翻手机,上面并没有魏萱的电话和留言。她抬起头来对桌子另一头的贺臻摇头:“我这儿没消息。怎么回事?不是不吵的吗?”
“她在电话里头冲我大哭,说得不清楚,五分钟前来的电话,只说不来了。你再等等,要是晚点她不来找你,你再打电话过去问问吧。”
“嗯。”
“今晚是专门庆祝你答辩通过顺利毕业的,现在看来这顿饭只有我们两个人吃了。喝点什么?”
酒水单推到眼前郁宁半晌才反应过来,她察觉到贺臻目光中的询问之意,忙打起精神:“哦,我看看。”
她没有心思,随便点了冰红茶,又不愿意让贺臻看出破绽来,点完东西也不抬头,可没想到贺臻已经在问了:“今天我出门没看黄历,也不知道有没有忌出行,不然为什么魏萱发好大一通脾气,你气色也难看?”
被说中心事的郁宁僵了一下,抬起头勉强笑了一下,却见他眼中并无语气里那份故作轻松,关切之余甚至有些隐隐的焦急,她不禁愣住了,思虑再三,还是说了:“下班前新诚的人力资源部找我去谈过了,问我对薪水有什么意见。”
“新诚要雇你?他家老板算盘太精,用一大批廉价的实习生,到最后也留不下几个,你能留下,这是好事,应该庆祝才对,怎么反而愁眉苦脸的?”
贺臻语气中的愉悦并没有让郁宁更加振作,相反,她的语气更加苦涩:“嗯,谢谢。我也已经拿定主意了,过几天应该会把合同签了,过来之前我给家里打了个电话……”
贺臻一愣,想起郁宁刚开始实习不久和自己提过的家里人的意见,知道这个电话肯定是凶多吉少。他无意催促,耐心地等郁宁收拾好情绪,继续往下说:“我和你提过我妈希望我作画家……总之现在她知道了,很不高兴。”
知道她在外面求学辛苦,妈妈对她从来是没有重话的,每次打电话回家,也是叫她多注意身体,不要太拼命。但这一次当她试图解释舞台设计这份职业并不算脱离本行时,她那几乎从不对她发火的妈妈,依然没有发火,却也不听她的解释,而是很失望地在电话里就哭了起来。
“……我将来是没有面目去见你爸爸的了……”
对于在她一岁多就意外去世的生父,郁宁是一点记忆也没有了,小时候关于父亲的印象,就是他留下来的一些画稿和为数不多的照片。后来她长大了,学了画,再去看生父留下的遗物,苦涩地发现那些画并不算多好,母亲怀念着的英俊有才华的男人,不知道有多少是被岁月和回忆美化了的幻像。
五岁那年母亲改嫁,再三年有了一个弟弟,继父在家乡做一点小生意,家境还算殷实,对母亲和她也很好,她是一直叫他爸爸的,尽管从小在母亲的教育下她很清楚那个面貌普通不善言辞的男人和自己没有一点血缘关系,但郁宁对他的亲近,仍然远远胜过照片上那张俊俏的面孔。
这个和她没有血缘的男人供她读书,学画,一直养育她,直到高考后要填志愿了,一天在晚餐桌上,很少就她的教育发表意见的他犹豫了很久,当着母亲和郁宁的面说:“……虽然美院的专业线过了,但小宁一直成绩很好,这次估分也不错,是不是考虑一下,要不要念别的专业呢?女孩子读美术不苦,将来要做画家,一个人打拼还是苦了点,我也不认识什么人,能在关键的时候帮她一把,而且她是她,路还是要自己走的,要是有别的喜欢做的事情,也可以考虑一下……”
几年后郁宁再去回想当天他说的那番话,忍不住会想,他一定是想了很长一段时间,谨慎又谨慎,才说出口的。但这场谈话的结局实在太不愉快了,只要一想到那天妈妈绝望的哭声,郁宁都觉得有人在拿针戳自己的心口——她和继父像两个做错了事情的孩子,看着她那从不高声的母亲伏在桌上失声痛哭,嘶声哭诉着“……我没本事,没本事一个人拉扯大女儿,我对不起你……”,他们惊惶地交换着目光,像是在瞬间成了共犯。
郁宁最后还是进了那所母亲一直希望她考上,也是生父毕业的美院,但大学录取通知书来的那一刻,她也隐约想过,长到这么大,除了继父在餐桌上被中断了的谈话,其实谁也没有问过她想要的将来是什么,而她也从来没有被给予选择的机会。
又或许是她自己没争取过,也就失去了要求的权利。
进了大学之后继父一如既往也毫无怨言地负担她的学费和生活费,每年放假回家,他也总是说“父母供儿女读书是长辈的责任,你要是钱不够用,一定要打电话告诉我们,家里不缺你的学费,就怕你在外面吃苦头”,郁宁知道他没有把她当作外人,但那一天他的话和母亲随后的恸哭曾几何时还是成了心头的刺,她想不出法子排解,也无法和任何人,甚至是父母恳谈,思前想后,最后决定把家里给的每一分钱都存起来,靠自己打工和奖学金来读这个大学。好像这样做了,这个选择就是自己做的,而她也正在为它负责一样。
“……别哭了。”
那天,继父笨拙地劝解着母亲,脸上的神色比哭还难看;她吓得也哭了,弟弟在边上更是嚎啕,拉着她的裙角说,“姐姐你别哭”,她拍拍他的脸,死命地忍眼泪,咬牙反复对自己说:“我没哭。”
“我没哭。”
“哦,那就是你眼睛在流汗。”
她悚然一惊,定睛再看,原来还是坐在餐厅里,正沉默看着自己并静静递来一张面纸的,是不知道等了她多久的贺臻。
郁宁狼狈地匆匆抓住面纸盖住脸,擦掉已经流到腮边的泪水,很久都没有抬头:“对不起……我太没用了,想到家里的事情,走神了。”
贺臻提也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