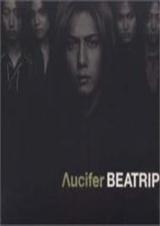第三部 宛若归去-第1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当然,”无非还没说,绮丽先顶了上来:“人家是心静自然气色佳,哪像你,整肚皮坏水,脸上所以发黑。”
“什么?”我沉下脸来,她也太过分了,就算护着心上人,也用不着这么损我吧,我招谁惹谁了,不由看她一眼,谁知她也在看我,眼里俱是狡黠:“昨晚怎么了?肚子痛?三番四次的爬起来,要真的不舒服,就跟我说嘛,干嘛这么累。”
“哦,”我明白了,昨晚我第二次出房又让她给瞧见啦,这丫头,怎么像只大老鼠,她是不用睡觉的呀。瞪她一眼:“是有些不舒服,所以起得勤了点,怎么你也有这个症状么,那么我们真得好好聊聊,看看到底毛病出在哪里。”
“好呀,”她笑了,哄我:“你要保重身体呀,我很关心你的。”
一边的无非听得满头雾水,终于插上句话来:“二位不舒服么?我会点医,可以帮你们看看。”
“不用,”绮丽回头,挟起一只我早看中的煎得嫩嫩的荷包蛋,笑着放到他碗里:“我们很好的,不过是晚上在外面立得久了,有点着凉,不用担心,马上就好了。”
“不错,”我说,二眼瞪着那只荷包蛋,看无非一口咬下去,蛋黄乳汁般流了出来,立刻心痛起来,“我们没事的,无公子放心,快吃蛋,那个蛋黄可不错,千万别浪费了。”
“呀,”无非皱起眉来,“这蛋没煎好呢,生的,我不习惯。”他挑出蛋黄,丢在桌上。
“什么?”我气闷,这小子,娘娘腔!就差绮丽把他抱在腿上,用调羹一口一口地喂了。看着那只牺牲了的蛋黄,我咽了口唾沫,碗里的其他二只都煎得老了,一摊摊地好不讨厌,我赌起气来,索性三口二口把粥吃了,自己起身就走。
到皇子府不过辰时三刻,时间早了点,晔也在吃早饭,“这么早,”他笑:“金兄用过饭了么,不如再一起吃点?”
“好,”我正是没吃饱,马上有人端了个位子上来,又有人要去盛粥,“不用”,我道,“有没有荷包蛋,嫩点的。”
晔立刻吩咐人去煎,我总算顺过这口气来,笑着看他:“我想过了,到了太子府,我们见机行事,若是他强要留饭,我们就坐下吃,你看我眼色,我吃什么,你就吃什么。”
“好,”他微笑:“一切都仰仗金兄了,希望这次如无非所说,一切都是我们多虑。”
“未必,”我摇头:“皇上最近身体不好吧,前阵子听说派了几桩差事给太子做,虽然差事未完成,可耳碑却是不佳,说不准太子是在想法子治你,来给自己保条后路,我们都得小心了,况且那次子桓平白无故地跑来警告我,本身就有问题,若不是真的有些门路在里头,他又何苦多此一举。”
“不错,”晔连连点头,又见有人端上菜来,忙住口不说了。
太子竮十八岁时已成了大礼,府邸也在宫内,骑了马过去,不过一炷香的功夫。
在大堂中,我们见到了太子竮,不过二十四五的年纪,除却了那身富贵荣华,人是长得端正平常,立在风华正茂的晔身边,那股皇室的气势竟完全镇不住,打量着这位貌不惊人的太子,我开始有些明白,事情为何会演变至此。
“十一弟这么早就来了,”他笑得和善,眼角眉稍透着柔弱:“礼部的人也来了,你准备什么时候才开始呢?”
“既然来了,自然马上入手,”晔微笑,更显得气度雍容,漫透着华贵的底子。
太子唯唯喏喏着,把他引进了大书房。
我怀里抱着书册,一路紧跟着,冷眼旁观,这位太子是真的愚钝?我倒情愿相信他是在装腔作势。
他把我们带入书房,便走了,走时与见时一样,口齿既不出众,举止更是平庸,最不能忍受的便是他的这份小心翼翼,知道自己不行,便先低了口气,可偏偏又要在下势中摆出太子的架式,真真叫人看着尴尬的一个人。
“如何?”乘着暇隙,晔问我:“有何印象?”
我笑笑,摇头,记得从前曾在皇上眼前见过他几眼,不过远远的瞥了个影子,当时就觉得人物一般,可是如今离得这么近一看,是连我都要替晔不平了。
晔止了笑,复叹了口气,终是没有再说什么。
一路忙到了下午,晔才带着我离开,走出太子府,望着身后那扇朱红的漆门,他低低耳语道:“你看好,总有一天,这座府邸会是我的,这个府里的人亦会来朝拜我。”
我不置可否,若是光凭太子的人选,这当然是可能的,那个太子竮是庸碌得叫人乏味,可不知怎么,我总是不放心,老是觉得这件事太过容易,这个人怎么会如此简单。
13
回了自己住处,一进园子,便看见绮丽立在门口与无非说话,她满目飞彩,手舞足蹈地比划着什么,瞧得那个缺心眼目瞪口呆。
“干什么呢?”我道:“才看完了戏班子唱戏,难道自己也疯了?”又向无非笑:“今天排得是什么牌目呀?”
“是‘太真外传’,”无非忙笑:“金兄不知,那套‘骊宫衣’实在耀目,彩衣绣襦,行头精致华美非凡。”
“哦,”我也笑了:“原来看得是太真,刚进门我一看她的手势,还以为‘嫦娥奔月’呢。”
“回来啦,”绮丽似笑非笑,又向无非道:“麻烦公子去看看我放在房里的东西好了么?”
“好,”他转身走了。
“又怎么了,”我睨她:“这么快把人支开了,到底有什么话呀?”
“我来问你,”她叉起腰来:“无非为什么来我们这住?昨晚你又去了哪里?我猜还是皇子府吧,无非是个君子什么都相信你,你却是一肚子花花肠子,有什么事还想瞒过我去?”
我苦笑,这个丫头,真是精得过了头,想了想,还是把她拉过来,凑在耳边一五一十地把事情都告诉了她,不过特意隐去了晔承认要夺皇位以及我意属少相的事情,又笑“不是存心瞒你,这事太过危险,又是在宫里,当然要保密才行。”
“就这些?”她半信半疑,轻道:“不可能罢,看你这么热心周到,定是自己是也有好处,再说我看那个皇子晔整天夸夸其谈的,肯定也是个有野心的人,太子防他根本没错。”
“你也看出来啦,”我忙赔笑,想要眶她还真不容易,“这皇府之事本来就是一团糟,我不过当他是朋友,担心他的安全,反正我一个人质,闲着没事,看看热闹也是好的。”
“哦,”她仍是不信,但也住了口。
“所以说你还是尽早回府吧,”我又低劝:“你到底是个女孩子,宫里现在乱着呢,不知道以后又要出些什么事,还是回去等我的信比较好。”
“不,”她也干脆“如果真是这样,你现在也需要帮手呀,再说无公子心肠这么好,在这些人之中肯定要吃亏的,有我在,我可以帮帮他。”
我一听,道‘哼’。
“怎么了?”她奇怪:“想说什么就说呀?”
“我说什么呀,”我冷笑:“你这个人是很没有良心,现在眼里就是一个无非了,对不对,究竟有了几分把握呢,想得这么周到齐全的,别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我看这股子亲热劲呀,还是很该留着几分的好”。
“你别吃醋了吧,”她也不生气,‘咯咯’笑了起来:“你这个人呀,心眼真是太活络了,我才不用替你担心呢,依我看,你像条泥鳅,放到哪里都滑得掉,无非却是块玉石,端端正正的,很容易被打碎。”
“泥鳅?玉石?”我好气:“就这么比方我,好,我认了。”
抬腿就要走。
“别走呀”,她又缠了上来,拉着我衣袖柔柔地求:“上午生的气到现在还没有消么?我说不替你担心,是夸你聪明呢,其实在这个宫里呀,还是你最吃得开,我要是那个皇子,也要狠狠地巴结你,捧着你不放。”一转眼,看无非走了过来,又笑:“你是不是最喜欢吃糖梅子的,刚才我从园子那头来,树上结了好多个呢,我摘了些来,叫人用糖腌了,等会拿给你好么?”
“这还差不多,”听了这些好话,又道是有梅子吃,我方才被哄得气顺了,伸出手去刮她的脸,取笑:“你这个丫头,可惜生错了,若投胎作了男人,这样的手段,就是讨了三五个老婆也摆得平。”
“这倒是的,”她咯咯笑着,躲开了去:“你是摆不平的,只要看你对宝福的那个样子,就是摆不平。”
我一口气上来,险些又堵住了心口,那个梅子还没吃到呢,就酸得我心都痛了。
说笑归说笑,我暗自鼓着劲,一连陪晔在太子府往返了近大半个月,居然平安无事,太子依然平庸如旧,也曾邀约饭局,我与晔小心翼翼应付,只浅尝水果与小食,每次一回府便抠着指头将喉中的食物吐尽,似这般苦心经营,又挨了近半个月,眼看礼曲颂词都整编完毕,终于等来了庆功宴,却仍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第二天,便要在太子府里饮酒庆功,到时皇上也会来,这天晚上,在晔的皇子府里,我抱着头,痛思苦想。
“肯定有什么地方不对,”我对晔说:“一切都太顺利了,难道真如无非所说,太子并没有不安好心?”
“我也想不通,”晔叹气:“可是你看,真的什么事也没有,一丝痕迹都不曾露出。”
我们商量到半夜,完全找不到要领,我郁闷起来,皱着眉,只好回了自己的住处。
回到房间,已近三更天,我倒在床上,直愣愣地瞪着房顶,还是睡不着。良久,隐隐地听到房外有衣袂飘动的声音,我奇怪起来,也不点灯,轻手轻脚地凑在窗口,向外张望。
房外有人,一袭白衣,只一闪,便消失在园门外。
我好奇起来,看那身影竟是无非,这么晚了他会去哪里?心里一串疑问,手脚并不停下,打开门,紧跟了出去。
夜色中他一身白衣异常地醒目,隐约在月下深浅的树丛中,一路直跟到后园的护城河旁,方见他停下了,立在水边,呆呆出神。
我找了片树丛藏起身来,探头往外看。
映着水纹流光,他脸上的表情是痛苦而专注,痴痴地瞪着水面,往日丛容优美的面目居然有些变了形,这付模样使我担心,难道他想要投河?
正犹豫着要不要现身,忽又听到脚步声,有人正慢慢走过来。
我警觉地屏气不动,一面四处转动眼珠,却见绮丽一身红衣,正自分花拂柳,浅笑而来。
“这么晚了,找我有事,”一见无非,她便叫了起来,娇嫩的嗓子在静夜中宛如黄莺。
“嘘,”无非急,上来拉住她,一把把她拉到河边:“你轻声点,不要惊动别人。”
“干什么呀,这么晚约我出来?”绮丽笑得柔媚:“我知道你们中原人喜欢夜会后花园,看看月亮顺便私定个终身什么的,你不是也想这样吧?”
“你别胡说,”无非又急,原想上去掩她口,可一触到她花瓣似的唇,手又被烫似的弹了回来,看上去是汗也要出来了。
我捂住嘴,拼命忍住笑,今天晚上看来有场好戏。
“绮丽姑娘,”无非低下头来,紧张,尴尬,像个小学生:“我有话想对你说。”
“说吧,”绮丽到底比他大方多了,微笑着,从袖子里拉出方丝巾:“你着急什么呀,来,我给你擦擦汗。”
她的手还没有擦到他脸上,无非马上又弹了开来:“别…,”他是真急了:“男女授受不亲,姑娘别这样。”
“怕什么,”绮丽‘咯咯’地笑了起来,“好,不碰你,你说呀?究竟是为了什么事?”
“绮丽姑娘,”无非终于狠下心来:“我们以后还是少见面吧,这些日子承你照顾关爱,我很感激,但…,但我毕竟不能娶你为妻的,我们不能再出去看戏赏花了,我们应疏远一些,免得影响到姑娘的名誉。”
“名誉?”绮丽笑得可爱:“无公子,你是不是想得太多了?”
“什么?”无非一呆,方才这话大约已是他这辈子说得最严重的几句了,没想到对方根本没当它是一回事。
“我并没有想要嫁给你呢,”绮丽柔声道:“我不过很喜欢和你在一起,所以总约你出去玩,难道你不觉得和我在一起很开心么?”
“哦,”无非道:“姑娘是把我当大哥了吧,要是这样,我们就结拜兄妹吧,我愿意当姑娘的大哥。”
“没门,”绮丽是想也不想:“我已经有金大哥了,再多也不需要。”
无非脸‘腾’地红了出来,吃吃道:“那么…,那么…”。
“我只是想接近你,”不知何时,她已伸出手捂住他嘴,凝视着他的眼睛,双眸亮过今夜的星辰:“你看这外面花这么美,晚上又这么静,我们身边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风光,你为什么总是要去想什么关于名誉的事情?如你这么聪明的人,只要肯安下心来看看四周,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个世上有许多东西是漂亮过书本上的道理,有很多人,是很亲切与有趣。只要你觉得和我在一起很舒服,我们就一起去玩去乐,为什么总要去在乎别人的眼光呢?”
她的声音温柔而诱惑,无非这个书呆子哪里听到过,他眨着眼,说不出话来。
“我妈妈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绮丽的手指开始轻轻抚摸他的唇,顺着那轮廓鲜明的唇线,慢慢沿着他如玉的面颊,柔软地探了上去:“她说,世界上有许多东西,像是名誉啦、伦理啦、还有诸如此类的许多大道理,它们就像是苍蝇,虽是不重要的,可偏偏总是无所不在。一个人,只要记住千万要爱惜自己,懂得保护自己,不去害人做亏心事,就不用在乎这一切,只要你肯转过身去,它们就会消失的,关键只是,你愿不愿真的不在乎它们,愿不愿只相信自己。”
她渐渐靠了上去,贴着无非的耳旁,声音轻柔而甜蜜:“你是这么美丽的一个人,应该享有世上最可爱的东西,美丽的花,漂亮的衣裳,还有开心的日子,为什么总要去想那些烦人的规矩呢?它们本就是别人订出来的,它们的主人又不是你。”
她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