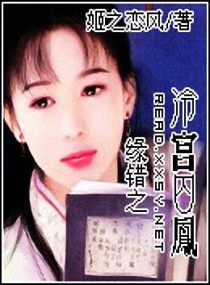樱桃错-第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们答应了玫姆。她开出的条件很不错,每晚两小时,一百元。最主要的是,她这里的客人不少,如果客人要点歌,开出的小费她分文不取。
玫姆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谜。她的美是原始的、野性的,如同泸沽湖边的水草,自然天成,充满勃勃生机。我觉得,大美,均源自于天然,所以我说玫姆是最美的女人。
但加贝不这样认为。他一向喜欢静美,不喜欢张扬叛逆,所以在他眼中,挂在树上的樱桃才是最美的。这当然纯属情人眼里出西施了。
玫姆住在光华路的一幢高档公寓里,那是北京非常高尚的地段,据说那里的房价让人咋舌。她还有一辆大红色跑车。不过可能身为摩梭人,所以她绝少开车,而是经常走路。她的体态非常健硕,双腿丰满匀称,走起路来像非洲大草原的羚羊,快而矫健。
我无法想像一个仍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女子如何从原始部落中走到北京,并拥有不菲的财富。看过杨二车娜姆的一本书《走出女儿国》,如果作者没有夸张,作为杨二车的族人,玫姆的经历估计也能写出一本天方夜谭的故事并经历一千零一夜的煎熬。
从女儿国走出的玫姆当然会有不少的阿夏。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阿拉伯人,说着一口地道的北京话,拥有一个著名又可怕的名字——约翰逊。不过他肯定没有NBA球星约翰逊的艾滋病。他非常干净,有时裹着纤尘不染的白袍子,有时穿着舒适清爽的亚麻套头毛衣。约翰逊在北京语言学院学语言,放学后经常带一捧鲜花来酒吧。一看到玫姆,两个人便没完没了地接吻,声音大得像火灾前的劈啪声。
在人们眼中,这个阿拉伯人是玫姆最钟情的阿夏,但我却不这样看。我注意到酒吧中有一个位置是任何人都不能碰的——火盆正前方。我知道,在摩梭人家,这是祖母的位置,也是最尊贵的位置。位置上的坐垫绣着斑斓绚丽的菩提扶桑凤凰,有着浓重的尼泊尔风情。每周总有两三个夜晚,一个身材略微发福的中国男人坐在上面。男人显然上了年纪,若非保养得道,估计皮肤早就松弛了。男人很安静,但他的静却有一种雷霆万钧的气势。他从来都是独来独往,而且从来都是一壶铁观音。品完这壶茶,悄然离开。不一会儿,玫姆也离开酒吧。
看过雅克贝汉拍摄的纪录片《迁徙的鸟》,为了心中的目的地,鸟儿们一直不停地迁徙、飞翔。我觉得很多移民都像迁徙的鸟,从这个城市迁到那个城市,在迁徙的过程中,心中隐匿太多的故事与忧伤,终于有一天,自己会被心中的负荷压得再也飞不动。
摩梭女子玫姆便是这样一只鸟。经常看到她疲惫的眼神与慵懒的姿态,我想,她是有些累了。
13
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地,加贝获得了一些面试机会。但都是一些非常小的广告公司,有的刚刚成立,办公家具还没有买;还有的,干脆就在地下室办公。
至于我,则一直杳无回音。加贝与思嘉都劝我放低标准,不如先从国内普通企业做起,积攒几年工作经验后,再寻找进入外企的机会。但我认为,起步是决定命运的关键。于是仍然坚守原则不放松,并报名参加剑桥商务英语与国家英语六级的考试。兆龙饭店的那个男人提醒得对:一方面有缺憾只能通过另一方面来弥补。人只有“谋事”之后,天才会助你。
就这样,白天,我们依然四处参加招聘会、投简历;晚上便来“心湖”。加贝唱歌,我在昏暗的灯光下学英语。
第一次看我捧着商务英语学习,玫姆哈哈大笑。当我告诉她缘由后,她笑得更欢了。她说:“亲爱的,两张破证儿有这么重要吗?买假的不就成了吗?”
“假的?”
“现在连处女膜都是造假的,这世上还有多少真东西?”
“被发现怎么办?风险太大了。”
“哈哈哈,害怕风险就别飞那么高。人生就是赌博,我们全是赌徒。”
我摇摇头。其实我不是害怕,而是不屑那样的风险。
玫姆果然很讲信用,按天付报酬。来“心湖”的客人们品位不俗,他们喜欢听加贝唱老歌,也非常尊重他,从来不提无理要求。所以除了玫姆的一百元,每天晚上我们还能赚到不少小费。听说,后海不少酒吧歌手的小费需要与老板五五或三七分成,玫姆从来没有向我们提及此事,真是一位豁达的女子。
有一天夜里,玫姆有事外出了。加贝坐在吧台旁唱英文歌,我依旧躲在暗处学英语。听着熟悉的歌声,偶尔与灯光下唱歌的“王子”会心一笑,感觉真是幸福无边。快结束时,一群带着三分醉意的男女闯进来,拍着桌子要酒喝。酒刚端上,其中一个挺着圆滚滚的啤酒肚的男人突然站起来冲加贝嚷嚷:“唱歌的,你过来一下。”
加贝抱着吉他走过去。害怕出事,我也急忙跟上前。
“小伙子唱得真不错!”男人喷着满嘴的酒气,朝身边人指了一圈,“你们说是不是啊?”
“是啊是啊!”那些人怪叫着拍起巴掌。
“我们点歌你唱,行不行?”
“对不起,我不见得什么歌都会唱。”加贝矜持地拒绝。
“肯定会唱,我们只点流行歌。”
“这——”加贝犹豫。我知道他骨子里的清高又发作了,他一定不愿意给这样的人唱歌。
“什么这这那那的!老子给钱,唱一首一百元,够了吧?”男人一手拎酒瓶一手拍胸脯。
天哪!一首一百元!我们一定撞到财神了!我想这些人肯定喝醉了,醉鬼的钱不挣白不挣!于是我狠狠掐了一把加贝的后背,他非常勉强地点了点头。
他们点的第一首歌便是“纤夫的爱”,不允许换歌。加贝的脸色很难看,但他强迫自己用力划拨琴弦,大声吼了一句:“妹妹你坐船头,哥哥我岸上走——”
听到他痛苦的歌声,我的心像被刀划过一样疼。不过,我们的伤口很快便被钞票贴住了。男人果然不食言,一曲终了,心满意足地往我掌心中放上一张百元大钞。我捏着这张粉红色票子,与加贝面面相觑,几乎有种做梦的感觉。
第二首歌是“一无所有”。这首歌尽管加贝也不喜欢,但他还是非常投入地唱了,于是男人又在我手上放了一张红色钞票。
就这样,这群人点一首,加贝唱一首,我手中也被放入一张大钞。或许在钞票的鼓励下,我们俩都越来越惊喜,加贝唱得也更尽兴了,张张堆积起来的钞票被我激动得几乎攥出水来。
正在狂躁兴奋时,我手中的钞票突然被硬生生抽去。扭头一看,竟然是玫姆。不知何时,她从外面回来了。她拿着钞票对着光线一照,立刻满脸紫胀,气得浑身都哆嗦起来。她把手腕狠狠一挥,一大沓钞票如巴掌般甩到那群人脸上。
“不要脸!滚——”她叉着腰,怒骂。
我胆战心惊地捡起一张钞票,仔细一看,竟然是假钞!刹那间,我的脸像被人抽过似的,火辣辣地疼。
那群人的酒也被骂醒了,自知理亏,小声嘟囔:“牛什么牛,小心我去工商告你。”
“骗子!这话还有脸说出口?我不告你使用假钞就算便宜你们了。滚,我这里不招待骗子!”玫姆骂着,将桌布奋力一扯,满桌酒瓶酒杯哗哗啦啦地碎了一地。
被玫姆豁出一切的怒火震住,这群人终于灰溜溜地离去,留下我们几个人,静得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声。
终于,玫姆低着头蹲下去收拾玻璃碎片。我也急忙蹲下帮她,没想到,手刚伸出去,她就猛地冲我大叫一声:“樱桃,你以后不许强迫贺加贝!”
一圈人全部都愣怔住。
玫姆非常欣赏加贝,这是显而易见的。每天夜里加贝唱歌时,她总会尽量推却一切事情,盘膝坐在火盆旁静静地听,手握一杯红酒,非常享受的样子。
有时听着听着,她会突然对我说:“樱桃,你要看好你的阿夏,千万别让别人抢走了。”
“哈哈哈,不会的,我的阿夏啊,扔都扔不掉。”这话一点儿都不夸张。加贝拥有一幅浪荡的外表,但感情却专注坚定。他最崇拜的偶像便是金庸笔下的杨过,那个等了十六年的呆子。
“别这么自信。”玫姆嘲笑着警告我,“摩梭人的萨满都不敢断言自己明天能不能再进阿夏的花楼。”
“我们不是摩梭人,是汉人。”
“摩梭人坦坦荡荡地走婚,汉人偷偷摸摸地走婚。只怕汉人,还不如摩梭人。”她咬牙冷笑。
我觉得玫姆肯定是在深爱着一个汉人。这份爱,一定是畸形的,这令天真率直的她,痛苦不已。
14
天气渐渐转暖,来酒吧消遣的客人也越来越多。或许因为加贝唱得实在好,没多久,不少客人竟然慕名来“心湖”。看着日渐增多的小费,我们找工作的紧张与迫切终于稍稍得到了缓解。
一个夜晚,因为客人不停地点歌,加贝一直唱到后半夜。回去的路上,我紧紧地按着着鼓鼓的背包,喜笑颜开。我们穿过一条胡同,黑暗中,突然窜出来几个流里流气的男人,有两个还背着电吉他与键盘。
“你们是新来的吧?”为首一个染着蓝公鸡发型,披挂层层钢链的男人问。
加贝急忙把我推到身后,问:“什么意思?”
“你们到底懂不懂规矩?”背电吉他的捏着嗓子问,瘟鸡似的。
“规矩?什么规矩?”
“哈哈,别装傻了!到什么山唱什么歌,保护费好像从没见你们交过吧?”
糟糕!我脊背一阵冰冷。原来我们遇到地痞的了。难道天子脚下÷皇城根前也有这种事?我吓坏了,下意识按住背包。就这么一个微小的动作被背吉他的男人发觉了,他尖着嗓子叫了一句:“在女的身上!”立刻,几个男人虎视眈眈地盯住我。我不禁惊出一身冷汗。
加贝紧紧搂住我,冷静地说:“别怕,给他们,全给他们。”
我万分不舍。因为不放心地下室的安全,我们把大部分的钱都带在身上了。本打算这两天存起来的,可这下子——
“快点快点,别拖拖拉拉的!”估计害怕被夜间巡逻的警察看到,“蓝公鸡”不耐烦地催我。
我偷偷瞥了一圈四周,发现不远处有隐隐绰绰的影子,心头一喜。于是故意放慢动作,慢慢地脱下背包,慢慢地拉拉链,慢慢地从这个口袋找到那个口袋……我想蘑菇到有人经过时,就大声尖叫。
然而,我的计划落空了。看到有人过来,“蓝公鸡”情急之下,伸手便抢我的包。可他的手还没有挨到我,脑袋上就被盖上一把吉他,“砰”一声巨响。是加贝砸的。他一定误以为“蓝公鸡”要伤害我。
刹那间,四周炸开了锅。纷乱迷离的光影中,加贝被几个人同时按倒在地,我惊恐万分地尖叫,毛发飞张、不顾一切地扑上前……
待一切喧嚣平定下来时,世界静得可怕。黑暗中,男男女女的腿从我们眼前昂然经过,可没有一双腿停下来看我们一眼。
钱包被抢走了。加贝像被抽了筋的鱼,软蹋蹋地趴在地上。我拼足了力气,挣扎着拉他,可刚一碰到他的头,手上就黏黏糊糊的一大把——
血!
“加贝、加贝、加贝——”我尖叫,疯了般用力推他。
静寂的夜色中,他微弱的声音缓缓地轻轻地传来:“樱桃,别担心,我没事,真、真的没事。”
我大哭。摸出手帕紧紧捂住他的头,浑身筛糠似的发抖。
不想让我担心,加贝努力爬起来,可稍稍一动,脑袋上的血像泉水般汩汩外涌,刹那间功夫,我的手帕便拧出血水来。
远远地,依然看得到后海的灯红酒绿、歌舞升平。可一切繁花似锦,都像被冰冻住的冰灯,诡丽、冷酷、遥远、可怖。
咬紧牙关,我摇摇摆摆走向最近的一个IC电话亭。当电话那头传来一声温柔的“喂”时,我泪眼滂沱,失声痛哭。
我找了思嘉。在最失神时,我想起了那个协和医院的江帆。
二十分钟后,那辆纯白的本田在我们身边缓缓停住。门开了,思嘉与江帆快步跑过来。一看到趴在地上血流不止的加贝,江帆急忙伸手按住他耳鬓前的两个穴道。
“得赶紧去医院。”江帆命令。他拉过我的手按住加贝头上的穴道,和思嘉一起用力把他往车上拖。
江帆的车技很好,车开得又快又稳。一路上,思嘉不停回头安慰我:“别担心,江帆已经把一切安排好了,他是最权威的脑科专家,一定不会有事的。”
我流着泪,频频点头。加贝虚弱地靠在我肩上,本就苍白的面色,如今更青得可怕。
“实在太麻烦您了,江教授。”我感恩戴德地冲着江帆的后脑勺说。
“后脑勺”一声不吭。略有些稀薄的头发在昏黄的车灯下,泛着尊贵的光泽。
江帆的确不是普通人物。车子刚一停靠在协和医院急诊大楼前,两位一袭白衫的男医生拎着一把折叠轮椅跑过来,毕恭毕敬地说:“江教授,已经准备差不多了。”
“嗯,先把病人推过去。注意止血。”江帆吩咐。
“是。”两个大夫合力把加贝放在轮椅上,一人按住他的穴道,一人推着他疾步跑进电梯。
江帆熄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