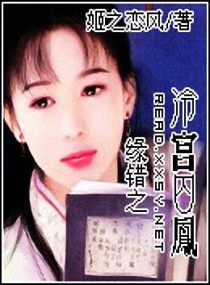樱桃错-第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硕士”、“双学士”、“博士”,“BEC”、“TOFAL”、“YASI”、“CET”、“CPA”、“CCPA”
,“一等奖学金”、“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满垃圾箱璀璨夺目的字眼如同巨石,一块一块砸中我的心脏,我不禁毛骨悚然。如果连这样的简历都被丢入垃圾箱,那么我的、加贝的,是不是应该丢进厕所让人如厕用?
越想越怕,唯有快步离开。不知何时,天空被蒙上一层肮脏沉重的棉絮,雾霭沉沉、淫雨霏霏,很快我的“风度”便遭到“温度”的报应。寒风如同刀子撕裂我薄薄的衣服,假毛料裙子与腈纶长袜如同电的正负极,怎么分也分不开。由于长时间走路,劣质高跟鞋更如锥子般刺着我的脚后跟,恨得我真想把它当街踢飞。
地下通道里,有个瞎子瞪着缺了黑眼球的可怖眼白,咿咿哑哑地拉胡琴;逃避城管的小贩们蹲守着一堆寒酸的小东西恍惚傻笑;卑微的妇女挺着大肚子或抱着孩子偷偷卖毛片;还有被打断了腿的脏孩子,拄着小板凳如螃蟹般乞讨……
地面上,街灯已经亮起,无数名贵私家车在被街灯点缀的路上呼啸前行。路两旁的玻璃建筑群,有时尚的风格、华美的气势、傲慢的态度与冰冷的内心。
这是一个奇怪的城市。一边是地狱,一边是天堂。而我,便是那个小心翼翼行走在天堂与地狱交界线上的女子。
身后,一个神情怪异的男人一直盯着我。我深感恐惧,于是加快步伐。没想到,男人竟然小跑上来,将嘴巴凑到我耳边,阴阴地问:“要不要办证?”
“什么?”我下意识反问。
“毕业证、身份证、驾照、各种证件……”
“不、不,不要——”我如同被烧红的烙铁碰到般急忙躲闪,但还没闪开,男人就往我口袋里强塞进一张名片,拔腿就跑。
顶着风雨,费了九牛二虎的牛劲,我终于找到回去的公交车。因为是下班时间,人挤得几乎要爆炸,整个车厢一片骂娘声。我没有骂,我在提防着自己短短的裙子,尽管这样,一双大手还是借挤车的机会,在我屁股上重重捏了一把。
我欲哭无泪。在这种时刻,被吃豆腐的只能作哑巴吃黄连状,否则流氓没抓到,自己反会惹一身腥,成为“骚娘们儿”。
公交车摇摇晃晃、颤颤巍巍地驶到“远园”,加贝已经站在公共汽车站牌处翘首张望了。我一下车,他立即撑起一把伞举到我头上。
“累坏了吧?”他关切地问。
我嘴唇青紫,浑身哆嗦,一句话也答不上来。
见我冻成这样,他急忙脱下自己的外衣罩在我身上,紧紧搂住我往回走。
被关成最小火的煤气灶上,一锅清汤阳春面正在泛着氤氲热气。加贝就有这个本事,一把挂面、几根小葱、几滴香油,在他的手里也可以化作美味佳肴。但此刻,我鼻子失灵了似的,一点味道也嗅不出来了。我看都没看一眼,踢了鞋便往床上扑。
朦胧中,加贝端着一碗面喊我吃晚饭;朦胧中,他轻轻地给我解衣服、脱袜子;朦胧中,他把被上严严实实盖在我身上;朦胧中,他拿着一块热毛巾为我擦脸擦手……
不知睡了多久,待我再度睁开眼睛时,天已经黑透了。我头痛欲裂、浑身疼痛,口腔里如同喷火般燥热。加贝正坐在我身边画一幅效果图,见我翻身,急忙过来搀扶,一碰到我的脸,他吓了一大跳。
“樱桃,你发烧了吧,怎么这么烫?”
“水、水,给我水——”我口渴难耐,一味要水。
他端来一杯水,小心翼翼喂我。不知为何,热水一流入冰冷的食道,胃竟然翻江倒海般抽搐起来,我一低头,胃里的食物竟然喷射涌出,稀里哗啦地吐了加贝一身。
“天!樱桃、樱桃——”来不及清理自己满身的秽物,加贝用力撑住我,拍打我的背,心急如焚,“怎么回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吐完后,胃里轻松了一些。我软绵绵躺下,但冰冷如海水般把我淹没,我不禁打起抖来。
“樱桃,我们必须去医院。”加贝果断地说,飞快换上干净衣服,往口袋里塞了几张大钞,帮我穿好衣服,背起我便往外冲。
夜已经很深了,我们打车来到医院。半躺在医院急诊大厅的长凳上,我疲惫地看着加贝如一只忙碌的工蜂,挂号、排队、找大夫、取单据……
化验结果出来了,还好,只是血向偏高,应该属于细菌性感染。医生睡眼蒙眬地在处方上划划写写。不过是普通发烧,他竟然划了满满两页纸。
“医生,不严重吧?”加贝轻声细语问。
“哈——”医生打着巨大的哈欠,口齿不清,“小毛病,普通发烧而已。”
“为什么会呕吐?”
“有炎症,胃弱,打两针消消炎就好了。”
加贝彻底放心,温柔地拢拢我的头发,酥酥的,麻麻的。
站在化价收费处,我懒懒地靠在他身上陪他排队。本来他让我坐着等他,但我不依,生病了真是粘人,一刻也不想与他分开。
轮到我们了,加贝把处方单递进去,很快,窗台里头便响起“吱吱喇喇”的针孔打印机的声音。接着,一句冷冰冰的声音响起:“三百六十五元。”
加贝明显愣了一下,但他什么也没说,立刻低头掏钱。一直处于迷糊状态的我突然惊醒了,一把拨开加贝,问里面的人:“什么药这么贵?”
“两天吊瓶呢!这还叫贵?这算便宜的了。”里面的小护士面无表情地说。
“为什么要打吊瓶,不是小毛病吗?能不能不打吊瓶?”
“别问我,问大夫去!”小护士“哗”地一声把处方单从窗户里推出来。
“樱桃,别争了,听话吧。”站在急诊室走廊里,加贝努力劝我。
“不,这不是抢钱吗?这还叫医院吗,和强盗有区别吗?”我快步走,愤愤不平地抱怨。
“嘘——别让人听到。”
“我就要让人听到。我是穷人,没钱给他们抢。”
“可你在生病啊。”
“在北京,我哪儿有资格生病啊?”说着,我的鼻子突然有些酸了。
不知这句话刺激到了加贝哪一根神经,他突然大步跨前,一把扭住我的胳膊,半拖半抱地把我往回带:“我贺加贝不至于穷成这样,连让女朋友看病的钱都没有——”
“加贝,你疯了,放开我、放开我……”此时,我的情绪也失控得厉害,在他怀里又踢又打。
有人放慢脚步,饶有兴致地看着我俩的表演,暧昧地微笑。在这一刻,我羞惭得恨不能从地面上消失。情急之中,我低下脑袋,冲着他的手狠狠咬上一口。
“哎哟——”加贝疼得叫了起来,急忙松手。我如泥鳅般快步溜走。
我是穷人,医院的大门是不对穷人敞开的。在医院门口二十四小时便利药房里,我买了一瓶退烧药与消炎药。回到住处,我强迫自己吃东西。尽管还在发烧,味觉明显消退,还有反胃的感觉,但我用喝一口歇三口的速度,就着榨菜,硬是把满满一大碗白粥灌进肚里。看我灌得难受,加贝的眼圈都有些泛红了。
吃完东西,为了防止再吐出来,我赶紧躺下。或许是退烧药的作用,很快我便安然入睡了。迷迷糊糊中,加贝摸着我的脸说:“樱桃,对不起、对不起……”
10
再次睁开眼睛时,已经是第二天中午了。阳光透过细细一抹窗户洒进来,竟然也暖融融的。
加贝正在门口煮东西。不知煮的什么,甜丝丝的,清香宜人。
“你在干什么?”我喊了一句。
看我挣扎着起来,加贝高兴坏了,捧金子般双手捧着一碗东西走过来。哦,原来是冰糖银耳梨羹。
银耳发过了,汤汁幼滑细腻;梨也炖透了,白白软软;透明的汁液上飘着几粒大红枸杞。加上黑漆碗的映衬,一碗简单的梨羹竟被他调制得如一个剔透的白玉工艺品,令人不忍下箸。
“是不是有些胃口了?来吃点东西,梨清火,银耳补胃。”他说着,沿着碗边舀了一勺羹,吹了吹,小心翼翼递到我嘴边。
甜,真的好甜!只是还没来得及尝第二口,我突然醒悟过来。一把掐住他的手指,紧张兮兮地问:“你去超市买银耳和水果了?你怎么可以这么乱花钱?我们——”
“放开我、放开我!”加贝咧嘴叫,满腹委屈地解释,“不是超市。天没亮我就蹬了四十分钟的车子去给你买东西,你一点儿不感动,反倒跟只母老虎似的!”
哦!原来他赶早市了。估计他一宿没怎么睡,眼底布满血丝,头发凌乱、胡子拉碴,肤色也有些憔悴。我心疼地说:“加贝,我不过是发烧而已,至于你这么担心吗?”
“是啊。你生病还不如让我生病呢。”
“那我若是死了呢?”
加贝吻住我的嘴,紧紧抱住我,不许我胡说下去。不知为何,我的心突然如被羽毛抚过一般柔软。喝着甘甜的梨羹,嗅着他身上混合了煤气与油彩特有的气息,我轻声问:“加贝,你为什么这么爱我?”
“嘿嘿,不知道!”他笑着刮了一下我的鼻子。
“说嘛。”我撒赖般搂住他脖子不放。
“爱一个人需要理由吗?”
“需要吗?”
“不需要吗?”
“需要吗?”
“不需要吗?”学着孙悟空与紫霞仙子,我俩拌起嘴来。拌着拌着,突然相视大笑。的确,爱一个人,真的不需要任何理由。只是,若想“百年好合、花好月圆”,或许还是需要一点点理由的。看着寒酸简陋的地下室,我又不禁长长叹气,自言自语:“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好日子啊?”
“我们现在就很好啊!”加贝随口说。
“好的话,为什么我连两天吊瓶都不敢打?”我冷笑。一语既出,加贝立即闭上嘴巴,低着头默不作声地搅拌梨羹。过了好一会儿,他赌咒般坚定地说:“樱桃,你放心。我一定会让你满意的。”
不想给他压力,我温柔地抚抚他的长发,笑着说:“只要能从地下搬到地上,我也就满意啦!”
“不,我们会有自己的房子的。咱们俩一起装修、一起刷墙。我们也会有自己的车,最好是绿色吉普,可以越野。当然,我们还会有——”
“还会有什么?”
他挠挠脑袋,不好意思地笑:“还会有——自己的女儿,像你!”
“天,越说越邪了!”我捂住耳朵。
然而,我们俩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还没持续到傍晚便被现实粉碎了。下午,居委会大妈过来收下一个月的房租。又交了七百元后,钱包瘪得如沙漠中风干的酒袋。
为了挣外快,加贝决定去后海酒吧唱歌。他说如果有些收入,我们找工作时会从容许多。我双手赞成。这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最重要的是,还来钱。我立刻爬起来,找出一张橘红色的美术纸,加贝用漂亮的美术字写上自己熟悉的中英文歌曲名,他还在歌名四周画了五线谱与小蝌蚪作修饰。
吃过晚饭,加贝背起吉他就要出门。尽管此时我还有些低烧,仍然忙不迭地穿上棉衣,戴上毛线帽子跟他跑出去。
刚走出地下室,远远地,我便看到一对气度不凡的男女走过来。女的一袭黑羊绒长裙,肩上披着精致的披肩,桃红色滚边,桃红色流苏,非常高贵。男的则是传统的黑西装,一看便是吓死人的牌子,笔挺的领口打着与女人披肩同样色系的暗花领带。俨然一对被上帝眷顾的璧人。我恋恋地看着,待他们稍微走近一点,我不禁大吃一惊。
女人竟然是杜思嘉!
思嘉显然早已经看到我们,想躲开时已经来不及了,于是她只好朝我们走来,似笑非笑。
“思嘉啊!”我啧啧称叹。怎么也无法把面前这位成熟优雅的女士与大学时那个格子衬衫背带裤,一脸傻笑着打羽毛球的女生联系在一起。还不到一年功夫啊!时间真是可怕。
“嗯。樱桃。”思嘉似乎也对自己这一身行头不适应,声音有些僵硬,“昨天招聘会怎么样?”
“都是货真价实的外企。可是我的条件不太符合,找工作真郁闷死了。”
“找工作?”站在她身边的男人好奇地插了一句。男人的声音很细,面孔白净得不可思议,五官还算端正,鼻梁上架着精巧的眼镜,他的眼神像深潭一样深不可测。
我不喜欢这种眼神的男人,太深奥。不知为何,我突然想起那个苗乡男孩小武了。黧黑的面孔、诚实的目光、笑时露出一对洁白的虎牙。
“是的,我们刚到北京,还没有找到工作。”加贝解释。
看我一脸奇怪的表情,思嘉似乎不太情愿地介绍:“这是江教授,协和医学院的医学教授。这是樱桃与加贝,我的大学同学。”
“教授?!”我和加贝同时瞪大眼睛。面前这个男人,虽说成熟稳重,可怎么也不像两鬓斑白的教授形象。
“哈哈,我上学早,八十年代末就去德国留学了,去年才回来。不过既然是嘉嘉的朋友,你们就叫我江帆吧。”男人矜持地笑。
“嘉嘉”,这个称呼让我听得实在别扭,感觉只有小武和杜妈妈这样亲昵地叫过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