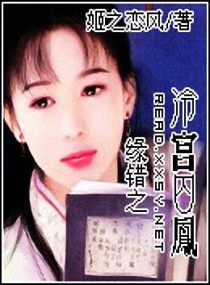樱桃错-第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杜。”
“跟你爸一个姓?”
“不,我从小就随我妈姓。”
我瞪大眼睛,恍然大悟:“呵呵,了不起,了不起。杜妈妈巾帼不让须眉——”
正聊得热火朝天时,坐在前排一直沉默不语的加贝突然扭过头问思嘉:“思嘉,小武送你的相思豆没忘记带吧?”
我俩同时一愣。这个贺加贝,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其实我们都看到了,思嘉把相思豆放在桌上后,就再也没有碰一下。而且,自始至终,她都没有提“小武”这个名字。
思嘉脸上的笑意僵住了,眼睛开始望着窗外。
“我怎么觉得你好像忘记带了呢?”加贝这会儿真是蠢得要命,竟然一点儿也看不懂别人的脸色,依然不依不饶。
“是的,我忘记带了。”思嘉冷冷地说。
“瞧你,跟樱桃一样丢三落四。要不,我这会儿下车,帮你回去取?”
我倒抽一口气,不禁惊奇地看着贺加贝,真不知此时他是故意装傻还是真的如此傻。
“加贝,你看好方向,省得以后我们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我转换话题,用力把加贝的脑袋扳向前方。但加贝这会儿真是犟得像头牛,立刻又把头扭过来,死死盯牢思嘉。
相信加贝的目光一定不好承受,思嘉的脸越来越像一块冰。终于,她一字一句艰难地说:“谢谢你。但不用了。因为我不能要。”
“为什么?!”我俩异口同声地问。
“我妈妈不同意。”
“什么年代了,还——”加贝气得满脸通红,几乎咆哮起来。
“贺加贝,你给我闭嘴!”我再次重重地、用力地把他脑袋扳过去。
呵呵,“妈妈不同意”,当一个人说出这样的理由,如果另一个人仍顽固不化,“痴心”是不是就是死缠烂打了?
相信加贝一肚子怒火被我压制得无处发泄,他“哗”地一声,重重摇下玻璃窗,面对滚滚车流,胸口剧烈起伏着,大口大口吐出浓浓白雾。
驶过一条喧嚣粗糙的酒吧街,出租车拐进一条僻静的胡同,最终缓缓停在两扇颇有西欧风情的雕花铁艺门前。门上挂着一个松木牌子,暗绿色楷体字——远园。远园果然幽远,里面国槐参天、松柏森森,铁门前还不时有荷枪实弹的“橄榄绿”们,缓缓地、肃穆地走来走去。
真好,我喜欢这份藏龙卧虎的感觉,越是内敛,越是深不可测。它让我的心蠢蠢欲动。
在居委会大妈与思嘉的带领下,我和加贝背负着满身行李穿行在迂回曲折的红砖小楼间。小楼不高,五层或六层,朴素但内涵深厚。一株株高大的柿子树士兵般静静排列,干枯的枝丫上挂着星星点点火红的柿子。私家车多得不像话,从柿子林密密匝匝挤到马路两旁,我暗暗数了一下,光奔驰、宝马就不下十辆。
“半地下室条件不太好。” 这是居委会大妈说的唯一一句话。多棒,简洁凝练,丑话在先,爱住不住。
正当我们打算走进一幢爬满常春藤小楼的地下通道时,一辆黑色奥迪无声无息地停住。车窗缓缓下移,一张妇人的脸非常优雅地浮出“水面”。
“妈——”思嘉叫道。
哦!妈妈!未见其人、久闻其名的杜妈妈。
杜妈妈果然名不虚传。一头蓬松齐整的花白卷发;一张坚毅轮廓分明的“国”字脸。鼻梁略有些鹰钩,上面架着一幅精巧的半框眼镜。目光非常锐利,习惯用眼角的尾光打量别人。这样的目光让这位迟暮的母亲显得凛然有余而仁慈不足。难怪思嘉处处一副“乖乖女”的姿态。
“嘉嘉,干吗呢?”杜妈妈字正腔圆,估计当官当久了,连对女儿说话的口气都不疾不缓。
“帮我同学找房子。看,这是我常对你说的樱桃,这是她男朋友,贺加贝。”思嘉热心地把我俩介绍给母亲。
“嗯。”杜妈妈略略点头,矜持地微笑,“你们打算租这里的房子?”
“是的。”
“这里的房租不太便宜吧?”她显然对我们产生了一点点兴趣。
“我们租半地下室。”加贝老老实实地说。
“哦!”杜妈妈眼中难得的亮光一闪而过,扭脸对女儿说,“嘉嘉,完事了快点回家。”
“好的,我知道了。”思嘉乖乖地回答。
“有空到家里吃饭。”杜妈妈不冷不热地招呼我们。然后,车窗缓缓上移,那张脸徐徐消失。
我笑着冲车窗挥挥手。我知道,没空。不是我们没空,而是她没空;也不是她没空,而是她没那闲情。
6
幸好杜妈妈及时走了。
刚一踩到地下通道的楼梯,思嘉的额头便重重撞到头顶的楼板,“咚——”的一声闷响。
我和加贝急忙冲上前,万幸,只是破皮,没有出血或鼓包。
“入口矮,以后进来记得弯腰。”大妈扭过头,淡淡叮嘱。
思嘉揉揉脑袋,冲我们苦笑。她是一个善良的女孩,此时,她肯定还觉得不好意思呢。
尽管只是地上地下,却有天壤之别。光线突然昏暗下来,高矮不一的水泥台阶令前面带路的大妈几次差点踩空。
空气不好,味道很重。朦胧的光束中,密密麻麻的灰尘虫卵般漂游。加贝有些过敏,接连打了好几个喷嚏。
长这么大,从来没有接触过地下室,没想到北京的地下室,竟然别有洞天。尽管阳光吝啬,空气污浊,但“生活”在这里依然热火朝天地持续着。狭窄昏暗的走道两旁堆着发霉的大白菜、干枯的大葱。头顶吊着女人的胸罩、男女内裤以及分辨不出性别的秋衣秋裤。由于经年拉扯,裤腿变形得厉害,夸张地从上往下吊着,踩高跷一般。地下室里静得令人窒息,房门紧闭,几乎每个房门处都摆着一个简易锅灶与煤气罐。因为空气不流通,煤气味、油烟味、洗衣粉味、厕所味、消毒水味、剩菜剩饭味、香水味、空气清新剂味……各种味道汇聚于此,琳琅满目,蔚为大观。
我们抽着鼻子,随大妈站到一扇斑驳的木门前。摸出一大串钥匙,大妈皱着眉头一个个试,好半天,门终于“吱”一声被推开了。
房间不算小,近二十平方米。两张单人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辨不清本色的塑料简易衣柜便是全部家当。窗户是细细一抹,恰好看得到路面人的脚。尽管有微弱的阳光,但依然需要开灯。北京风沙大,路面上的灰尘恰好透过那抹窗户洒进来,窗台积满厚厚尘土,它成了一个天然的土坑。
前任房主不知是谁,墙面排列有序地贴满各种高档别墅、度假村庄的宣传广告,湖光山色、光鲜漂亮。靠近床头处用红色荧光笔写着一句血淋淋的话:WHO 怕 WHO!
“WHO 怕 WHO!”我吐着舌头走上前去撕,粘得还挺紧,好不容易揭去后,下面竟然是更早期的人贴的各式豪华汽车铜版纸广告。我惊呆了,没想到这不见天日的地方竟然还埋藏着这么多伟大理想。
正在发愣呢,突然听到思嘉一阵尖叫。扭头一看,她正拉着简易衣柜的拉链惊恐万状。我和加贝急忙凑上前去看,满满一衣柜的虫,肥白温润,被突如其来的光线吓着,正飞快地四处逃命。
“是蟑螂,别怕!”大妈探探头,安慰我们。
“蟑螂怎么是这种颜色?”加贝问。看得出,他也恶心得要命,正死命拧自己的鼻子。
“见不到阳光呗!地底下的虫,都是这种色儿。”大妈说着,随手打开抽屉,一大群“白蟑螂”又触目惊心地狂奔。“没办法,地下室就是蟑螂多。喏,还有这儿——”她又走到床边,揭开床罩,果然,又是白花花一片……
我毛骨悚然,蹲下去一阵干呕。加贝急忙架住我,用力拍我的背,又气又急:“樱桃,算了,CBD又如何?CBD也有蟑螂——”
我一把推开他,擦擦嘴,努力作出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情,问居委会大妈:“大妈,就冲这里的蟑螂,您是否也该让出点杀蟑螂的钱?”
蟑螂为我们省下了一百元,我也把自己当作了CBD的一只蟑螂。
直到多年后,每当回想起那满世界肥白温润、四处乱窜的蟑螂,我还惊异于自己当年的勇气。其实我是很佩服蟑螂这种生命的,没有阳光,它们就变异自身基因;没有食物,它们便啃垃圾、水泥、木屑、玻璃,甚至钢管。它们从不怨天尤人、妄自菲薄,为了在钢铁森林中生存,它们懂得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甚至基因。顺者昌,逆者亡,所以不要嘲笑这些丑陋的小生命,它们远比人更懂得这个生存法则。
由于思嘉的担保,居委会大妈没有坚持“押三付一”的行规。交了第一个月的房租后,我赶紧把思嘉赶回家。不过短短半个多小时,她的手机已经响了三次。再不放她回家,估计杜妈妈会向国家安全局报案了。临行前,思嘉向我详细指点了附近的超市、菜场、公共汽车站牌等。末了,竟然没头没脑地来了一句:“樱桃,如果小武再联系你们,请告诉他,让他不要再来北京了。”说完,“登登登”地快速跑开。
加贝愣愣地望着思嘉的背影,突然一把抱住我,紧紧地,怕丢了似的。
“抽什么风?”我骂。
“小武完蛋了。”
“没办法。”
“我们不会成为他们吧?”
“你说呢?”
加贝捧起我的脸,目不转睛地盯住我的眼睛。昏暗的光线中,他清秀的面庞竟然有种梦境般的朦胧与不真实。最终,他长叹一口气,坚定地说:“不会的。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对不对?”
我把脑袋深深扎进他怀里。不知为何,一股忧伤的气氛如海浪般袭来,我有些害怕,只好紧紧揽住他的脖子,如同揽住大海中一块轻飘飘的木板。
7
尽管不见天日,但对于这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 “家”,加贝还是倾注了十二分的热情。
他关上门,用水浇、火烧、杀虫剂除去了大部分蟑螂。不敢面对超市触目惊心的价钱,他坐公共汽车,到很远的农贸市场买来漂亮廉价的生活用品与淡绿的纸布置丑陋寒酸的地下室。加贝的手非常灵巧,他把淡绿色的纸贴满墙壁,在墙壁钉上废弃的木板作搁架。木板排列成对称的平行线,相互错开,尽管简单,但钉在泛着青草气息的墙壁上,却有一种粗犷质朴的美感。
小区有一个巨大的垃圾箱,因为居民大多是高薪阶层,所以丢弃的东西很多都还有四五成新。在这个垃圾箱里,加贝捡回一个断腿破面的双人沙发、一个缺把的炒锅、一个被虫蛀的老式木头箱子、几个漂亮的酒瓶,还有好几盆快干死的花。回到屋里,他用在农贸市场买来的花布为沙发重新缝上新衣裳,用报纸包几块砖头垫在断腿下面,这样,我们便有了一个舒服漂亮的沙发。至于被虫蛀烂了的木箱子,往上面铺块同样的花布,摆在沙发前,便是一个最相宜的茶几。“茶几”还是多功能的,肚子里头可以装杂物。而那几盆快死的花,则成为我们生活中最奢侈的绿意。加贝把它们放在阳台上,每天松土,定期洒水,精心呵护,一两周后,在阳光微弱的半地下室里,它们竟然起死回生,有一盆长寿菊居然还开出几朵橘红色的小雏菊。
有一天,加贝甚至用20元的低价从一个收废旧家具的男人那里买回一个书柜。书柜完好无损,只不过白漆已经剥落,斑驳得不成样子。抬回屋后,加贝用白颜料重新为它刷色,用拙稚的笔法在上面画满山川大海帆船,童趣烂漫。为了配合这个可爱的书柜,他还用铁丝捏了一个灯笼状的白棉纸灯罩,在上面画满星星月亮。当这个手工灯罩套在光秃秃的灯泡上时,整个房间立刻洋溢出一种浪漫天真的情趣。
渐渐的,我们寒酸的小屋温馨起来:窗户下面摆着漂亮的沙发,搁板上放着粗朴的烛台与鲜花,房顶吊着浪漫的灯笼,还有满墙壁的木头相框,憨态可掬的椰壳娃娃以及生机盎然的植物……加贝是一个没有太多欲望的男人,每当他完成一件新手工,便会举起手中的作品,得意洋洋地对我说:“瞧,樱桃,我又为家里作贡献了。”
“嗯。可是你又犯错了,这里不是‘家’,是‘窝’。”我郑重其事地提醒。
这里当然不是“家”。地下室再漂亮温馨也不能被称作“家”啊!所以每当听到加贝说“家”这个字眼时,我就一阵心烦意乱。
我们的家,即便不能在风景优美的TOWN HOUSE里,也应该在时尚舒适的小区中。贺加贝不应该只有这么一点儿出息吧。为了刺激他,每天傍晚,我都拉着他到附近的高尚住宅区里散步。站在喷泉假山的中心花园里,我向他指点着家家户户温暖的灯光、雅致的阳台与飘逸的落地窗帘,用温柔得近乎残酷的声音对他耳语:“亲爱的,看到没?那里才应该是我们的家。”而每每此时,我这位亲爱的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他不能不憋闷,满大街豪华汽车在我们眼前招摇着,满城精彩纷呈、华美诱人的房地产广告牌冲我们抛着媚眼,满世界鲜亮的商品站在橱窗后嘲笑我们的口袋……这怎能不令我们神经焦虑、精神紧张呢?
半个多月了,工作依然没有什么动静。
刚到北京的第二天,我们就漫天撒网般向CBD的企业投出近百封应聘信,参加大大小小不下五个招聘会。为了增加竞争力,我甚至厚颜无耻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