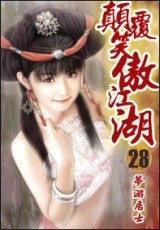阎王笑-第2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持着猛禽特有的自傲。
萧逐月不禁动了怜悯之心,他蹲下身去,试探性地抚摸鹞鹰染血的翅,近些了看,见其上羽毛纷纷脱落,翅骨也以奇异的姿态弯向一边,应是被人恶意折断。
“逢时春不喜欢动物。”
萧逐月抬头,不知何时,殷阑珊已来到他的身边。
“这只鹞鹰,想必是无意间侵入了他的领地,被他所伤,勉强支撑逃到了这里。”
她就事论事,却见萧逐月居然伸出手去,看样子,是想要抱起那只鹞鹰——
“住手!”
她厉声喝道,却慢过了萧逐月的动作。
那鹞鹰见萧逐月伸手过来,目露凶光,拼命扑翅站立,飞羽扬动,血点染上了萧逐月的袖,尖利的喙也对着萧逐月的手背猛啄了下去!
萧逐月躲闪不及,被鹰喙啄中,顿时撕拉开一道偌大的伤口,血肉模糊。
与此同时,殷阑珊已出手扼住了鹞鹰的头颈。
鹞鹰发出一声凄厉的叫声。
殷阑珊面不改色,拇指微曲,就要对准鹞鹰的头顶敲下去!
“不要!”
见殷阑珊要下狠手,萧逐月惊叫出声。
殷阑珊手上动作暂停,看萧逐月一眼,“它伤了你。”
“我很好,我没事。”顾不得手背伤口的疼痛,萧逐月急切切道,“别杀它。”
“只是一只猛禽而已。”殷阑珊的语气有些不屑,“伤人就该死。”
“万物皆有灵性,它伤人,也是人伤它在先。”萧逐月也去夺鹞鹰,“若伤人就该死,那你呢?”
萧逐月突然停下来
——情急之下,慌不择言。
果然,殷阑珊脸色一变,“你居然拿我跟一只鸟来比较?”
“我没有。”萧逐月辩驳,“无论是一个人,或是飞鸟走兽,都是一条性命,为什么非要赶尽杀绝?”
见他竟为了一只鹞鹰与自己辩说起来,殷阑珊未免有些恼起来,“没错,性命人人皆有,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保住自己的命。”
言于此,她的拇指,再次用力敲了下去。
萧逐月握住了她的手。
他的模样,竟有些悲戚。
殷阑珊一时怔忡,好一会儿,她才低低问他:“为什么你要保住它?”
萧逐月望着她,“因为我知晓,当深陷困境已无退路之时,没有人拉你一把,是多么绝望的事。”
殷阑珊怔住,只因萧逐月的眼神,那么哀伤那么无助,一张模糊的面孔,慢慢地浮现出来,且渐渐清晰起来——
那是一张少年的苍白的脸,带着三分惊惶,三分失措,三分惊恐,还有一分的决然。
——竟与萧逐月有几分相似。
头莫名地疼了起来,她抚额,手一松,命悬一线的鹞鹰,就这么直直落入萧逐月的手中。
萧逐月捧着死里逃生的鹞鹰,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轻轻将它放在一边,抬眼瞧殷阑珊,见她脸色惨淡,似乎很不舒服。
“你没事吧?”他起身,扶住她摇摇欲坠的身子,关切询问。
殷阑珊的手,重重搭上了他的臂膀,五指张开将他牢牢抓得死紧,几乎要穿透衣裳陷入肉里去。她死命地盯着他,一字一顿地开口:“萧逐月,我曾救过你,是不是?”
“你说什么?”逢时春放下手中的石棋,饶有兴趣地问垂手而立的总管,“你说殷阑珊还不能完全记起那位萧公子与她的关系?”
“是。”总管恭敬回答,“属下一直在别有洞天外的暗室听他们之间的谈话,萧公子对那只受伤的鹞鹰——”
逢时春皱了皱眉,厌恶地挥了挥手。
明白了他的意思,总管跳过这一段,继续往下讲:“之后,殷阑珊便问了那位萧公子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她问什么?”
“她问:‘我是不是救过你’?”
“照你这么说来,这‘夫妇’二人倒有些意思了。”逢时春挑起眉来,“能够让七情不动的摄魄右使出手相救的,还真鲜有人在。初那个人之外,殷阑珊竟不曾冷面对待这萧公子——看来,我也得好好会会他了。”
“候爷——”总管上前,低声开口,“那软骨粉药性虽猛,但药性至多持续十天。”他抬眼瞅了一眼逢时春,“若是殷阑珊恢复了内力,而段步飞又不肯——”
逢时春微微一笑,拾起先前的棋子,斜斜睨了他一眼,“你是说,我走错棋了吗?”
第67节:第六章 千壁崖候府(3)
总管忙低头,“属下不敢。”
“那不就结了。”逢时春落子,又吃掉了一个“士”。他满意地笑了,望着那剩下的孤“帅”,似在自言自语,“段不飞,你不傻,失掉殷阑珊,等同断你双臂伤你元气,即便对她了无情义了,为着无间盟,你又岂会坐视不理?”
“报!”
对匆匆而来的候府营卫,逢时春连眼皮也没有抬,专注地看着棋盘,似乎已经沉浸下去。。
总管代他发问:“什么事?”
营卫回答:“山下护卫禀报,发现不明人等入山,并直向千壁崖而来。”
总管望了一眼逢时春。
“瞧,该来的,不都来了吗?”早已料到这个结果,逢时春终于抬起头来,看还在等他命令的营卫,“传——放他们进来,沿途不得阻拦。”
见营卫领命而去,他的眼神阴冷了下去,缓缓收掌,握紧的五指间,被捏碎的棋子化为粉末徐徐落下——
“段步飞,我要你进得来出不去——阎王令和错儿,最终,都会属于我!”
崎岖险难的山道上,纵使是骑着马,梁似愚觉得自己被颠簸得快要散架。
他揉了揉自己酸痛不已的后腰,偷偷瞅了一眼旁边腰板笔直的人,终于小声发问了:“翟左使,你看我们是不是休息一会儿啊?”
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他居然碰到了无间盟的上三阶实权人物,没料到殷阑珊居然就是传说中的摄魄右使,而身边这个——说起来忍不住又瞅了瞅。
明明就是个发育不良的毛头小子嘛,结果人家来头好大——哈,拘魂左使!
果真人不可貌相啊……
从潼川一路马不停蹄地赶往重林山千壁崖,他是无法探知无间盟的人是不是都是铁打的,可他这身子骨确实已经受不住了。
翟向善根本不搭理他,与修罗一左一右骑马护卫着中间的马车前行。
果然是上三阶的人物啊……
见他对自己的话无动于衷,梁似愚的视线转到那马车的灰布帘子上,心思转了转,开口道:“山路崎岖,我想夫人恐怕不是很适应吧。”
马车突然停下。
翟向善和修罗忙勒绳下马,走到车前,掀起车帘。
“休息一下。”
属于阎王特有的声音响起,梁似愚望过去,见阎王扶着那名“错儿”下了车来。
看上去脸色不大好呐,莫非是被他乌鸦嘴说中了?
面纱下似乎有眼光朝这方射来,梁似愚忙转过身假装是在拴马。
错儿?也怪,哪有人给自家女儿取这么不吉利的名字的?
眼角余光见阎王扶着错儿坐在树阴下,还体贴地喂她喝水,不免唏嘘夫妻恩爱哪,可惜,那错儿——
嗯,算了算了,既然自己可以看出来,阎王又不瞎,他当然也知道啦。
摇了摇头,他朝翟向善和修罗走去,耐不住似火骄阳,随手扇了扇风,“好热啊。”
修罗瞥他,简单开口道:“是你自己非跟我们来的。”
“我当然要来啊。”梁似愚擦了擦汗,“逐月再怎么说也是我的朋友,莫名其妙地失踪,还涉及什么江湖恩怨。虽然这根本就不关他的事,可是扯上殷阑珊——哎,算了,反正也解释不清。谁知道那个什么淳于候会不会不小心就误伤来着……”
“你来能做什么呢?”这一次,问话的,是另一边的翟向善,他看那方细细呵护段云错的阎王,转过脸来,“阎王会救阑珊,可不会关心萧逐月的死活,你来,最坏的结果,是为他收尸。”
“不会吧?”没感情的话配上他骷髅脸还真是大煞风景,梁似愚不敢置信,“哪能这么见死不救的?”
“他是无间盟的阎王。”短短几个字,给了梁似愚最好的解释。
催命阎罗——他要大发善心,也就奇了。
梁似愚的脸色有些惨绿,不过显然还在硬撑,“我想应该没事的,逐月那个人,温和善良又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不会短命。退一万步来说吧,假若真有那个什么什么的,他无亲无故,我跟了来,好歹也能料理。”
“萧逐月有你这个朋友,倒也幸运。”翟向善轻轻地说。
修罗哼了一声,不置可否。
前方光滑如镜的千壁崖半腰,突然出现了一点亮光,在阳光的照射下,上下移动,格外刺人眼目。
翟向善和修罗二人迅速围拢到阎王与段云错身边。
虽然不大确定那是什么,但见翟向善与修罗瞬间警觉的模样,梁似愚大约也能猜到那不是对己方有利的东西。
“紧张什么!”阎王开口了。
“阎王?”翟向善回头看他。
阎王示意他二人推退开,他则牵了段云错的手,慢慢走上前来,指着前方的千壁崖,柔声对她开口:“错儿,你看那是什么吗?”
段云错眯眼望那亮光,格格笑出声来,“哥哥,那崖壁好光滑,好像一面镜子哦。”
“是吗?”阎王的大掌抚过她的秀发,黑纱下谁也看不见的眼中有一抹杀机立现,“等我们接出阑珊,重林山千壁崖淳于候府,从此便是你的了——你爱把它当什么,都可以。”
——狂妄中带着目空一切的不可一世。
对阎王与段云错的对话,翟向善与修罗没有反应,只有梁似愚,听得不寒而栗。
他誓要踏平淳于候府,究竟是为了救殷阑珊于水火,还是仅仅为了替他殷殷所唤的“错儿”找寻一个万物而已?
若是后者,那又是怎样的一种执念能令人疯狂可怕到如此地步?
第68节:第七章 两相对决时(1)
第七章 两相对决时
“你救过我,是我的恩人。”
那一日,他如是平静地回答她,明明白白却又令她如坠云里雾里。
殷阑珊半依石壁上,瞥了一眼忙碌的萧逐月。
他坐在石桌前,心思全在那只受伤不轻的鹞鹰身上。
从别有洞天回来之后,这几日来,他清理了鹞鹰身上的血迹,小心翼翼清理完伤口之后,又找了两方薄薄的石片,夹在鹞鹰的羽翅之上,见它并无大碍了,才放下心来。
——甚至顾不上自己手背的伤口。
“喏,吃吧。”他将一碗肉粥推到耷拉着头的鹞鹰面前。
或许见萧逐月并无伤它之心,鹞鹰从最初的凶悍变为温顺,任萧逐月抚摸它的羽毛,尖尖的喙啄了两下肉粥,嘶鸣一声,便不再吃了。
“怎了了?”见鹞鹰无精打采,也拒绝吃粥,萧逐月有些急了,干脆自己拿起勺子,看样子是准备亲自为鹞鹰喂食。
殷阑珊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她下了床,径直走到萧逐月面前,在他迷惑的注视下,一把夺走他手上的肉粥重重放下,转而看耷拉着头的鹞鹰。
见她来势汹汹,萧逐月有些慌了,张开双手护住鹞鹰,“阑珊,你答应放了它的。”
怎么?莫非她脸上明明白白写着“反悔”二字吗?
“放心,我说到做到。”先说一句让他定心,殷阑珊瞪他一眼,“就你这点能耐还想救它?我担心它伤好了反倒被你饿死了。”
萧逐月缩了缩脖子,“可是它不吃……”
“你见过哪只鹞鹰是喝粥长大的?”殷阑珊没好气地说,“这是野生野长的猛禽,不是豢养在家的公鸡,它要吃肉的。”
“哦。”萧逐月恍然大悟状,“可是,我去哪里弄肉呀?”
“说要你弄吗?”他还真是没一点头脑,“待会儿找那总管要些便是了。逢时春说了,我们是客人,需要什么,尽管开口,不需要跟他客气。”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呐。”萧逐月欣喜,“可是那个候爷不是最恨动物吗?要是他知道我们救下了这只鹞鹰,他会不会——”
“行了,就说这只破鸟是我要可以了吧。”殷阑珊打断了他的话,摊开手,“拿来!”
“什么?”萧逐月愣了愣。
“手啊。”殷阑珊白他一眼,拉过他的手来,见手背的血迹已经凝固,虽损了些皮肉,倒也没伤及要害,便放下心来,“你这人,顾前不顾后,就算是要救吧,也先考虑一下自己好不好?看看,弄得伤成这样。”说归说,她还是低头吹了吹他的伤口,“痛不痛?”
“不痛。”她的发髻在自己眼下晃动,呵在自己手背上的热气暖暖的,早已驱走了那灼热的疼痛感觉。
阑珊,跟以往的冷漠无情相比,好像改变了一点呢。
“伤成这样怎么可能不痛?”殷阑珊狐疑地望着萧逐月,结果一抬头就看见了他傻呆呆注视她的模样。
触及殷阑珊的视线,萧逐月飞快地别过脸去。
嗯,红了呢——有些好笑,不过,更多的,是舒缓的心情。
怎么形容呢?轻飘飘的,仿佛自己是在云端行走。
被人重视,原来就是如此这般吧。
“可能是受伤了,感觉有点热。”萧逐月咳了咳,欲盖弥彰。
受伤流血了都会发冷,怎么可能热呢?
明知他是在说谎掩饰,反正心情正好,殷阑珊也懒得去揭穿他,“这样啊,那你早些歇息好了。”
萧逐月站起身来,匆匆走进内室。
殷阑珊气定神闲地坐下来,手指打转了一圈,缠上鹞鹰的尾羽,想起萧逐月之前的表情,忍不住轻轻笑起来。
养神的鹞鹰被惊醒,张开眼来,许是见了她,眼神又警惕起来,低哑地叫了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