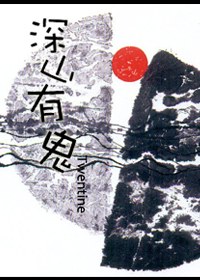山有木兮木有枝-第3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真是妇人之仁。他朱棣若不拘了徐氏,又怎能保得了她,保得了他自己?他拘她,并非仅为她谋害眼前人,除却这一桩,她尚有数桩重罪在身,包括私通书信于她的兄长,再通过徐辉祖将他燕王府内的绝密线报,不断秘呈于那位儿皇帝。
若不是他一早警觉在先,他差一点就为此白送了性命,就连他装疯称病一计,也差一点随之全盘输尽。但,此刻,尚不到杀她的时候,他留着她,尚有大用,又怎会轻易杀她?
他看一眼鬓发已霜染的内侍,沉声命道:“刘成,你且留下。马三保,你随本王走。”
“是。”
地上的二人即刻领命,尤其是马三保,可说是大喜过望,一双狭长的朗目内掩不去的喜色,却不敢去望那抹小小的身影,深怕犯忌,只那一声“是”字,答得尤其响亮。
待再回转眼眸,那一双素手,仍紧紧抓着他的马鞍一角不放。纤细的手腕上,衣衫不及处,是再触目惊心不过的几道旧伤。他不禁痛极生怒,再一挥长臂,手中的铁鞭,硬生生拂落了她的手掌,击下一道深深的红印。
她被迫丢了手,却丝毫觉不出痛,只是,因着这股强大的外力,身子再也支不住,一个趔趄,跌落于他面前。
他一夹马腹,座下铁骑随即会意,昂起脖颈,应声长嘶,再扬开四蹄,绝尘而去。身后,是百步之外随侍的众护卫,以及随他而去的马三保等人。
渐行渐远,不一会,身后的茅屋,便已融入天幕之下。一行铁骑,踏起漫天的烟尘,笔直地朝向远处的队列疾驰而去。
第四卷 崔嵬 第七章 海棠依旧
一撇,一捺,横勒,竖弩。
笔锋,在素白的绢纸之上,圆润健劲地起承转合。
轩窗外,是如此皎洁的满月,仿似一盏金轮,高悬于秋凉的夜空。所有的下人,都已经被他屏退,此刻,亥时已过,整座府邸都已经安静了下来,只剩下秋虫的低吟,陪伴着屋内的人影。
一袭半旧的袍衫,衣襟及袖口,微露出白色的里衣。
墨香阵阵,沁于鼻尖,男儿的长臂,在那一方长案上,不疾不徐地挥动着。案前的夜烛,映着他清隽的面容,刻下淡淡的阴影。
一阵微风拂过,拂乱了横幅,也扰乱了人心,笔尖一颤,竟鬼使神差地改了笔触,换为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字。
他低头望着纸上这两个如此熟悉却也如此惊心的字迹,默然凝视良久。遂,丢了狼毫,走至窗前,抬头望向那一轮明月。
有道是白云还自散,明月落谁家。而他的明月,早已随流水逐天涯。
犹记得那一年,他自外返家。没想到数载之前尚是黄毛丫头的小小人儿,竟然,出落为一枝豆蔻。虽不是绝色,但,一张俏生生的小脸上,黑白分明的眸子,却望乱了他的心湖。
他隔了满堂的家人,朝着自个面前的侄女微笑。
她扶着门槛,随在一众嬉闹争抢的孩童之后,自外而入。仰起小脸,带着一丝羞涩,迟疑着,软声问他:“你是谁?”
他俯下身,和颜道:“我是你二叔。”
一袭绿衣,身量尚未长足,眨着一双明眸,定定地望住他,却不肯叫人。他看了不禁失笑,扭头看一眼自己的妻子,低头打趣她道:“来,给二叔看看你的天足?”
她登时涨红了小脸,提起裙裾,当着一屋的人众,也不管规矩,奔出厅房。
婉如忙嗔怪他多事,在旁低低道:“寒枝一向面嫩,之前才叫东山嘲笑过,你又来。”
东山,是他三弟的幼子,仅比她小上一岁。数载内的每一封家书中,但凡提到他,无不以“性情顽劣异常”来总括。
到彼时,他才得知,他虽因了她的高热松了她的缠足,却也铸成了她少时的伤痕。为了此一桩,她非但时常被府内诸人诟病,连无知的孩童,都屡屡以讥诮她的天足为乐。
当他在后园的荼靡架下找到那抹小小的身影,果然,同婉如所说的一样,她正蜷缩于假山石前,望着自个面前的蚁窝发呆。
他矮下身躯,轻轻为她撩开腮畔的碎发,含笑轻道:“寒枝怎么了?”
她转过小脸,眼角,尚有未干的泪痕,低低问他:“你果真是我的二叔么?”
他笑答:“是。”
她望着他,却不肯再讲话。他只得再问:“寒枝不信?”
她咬紧唇瓣,半晌,才道:“二婶说,是你让他们放了枝儿的缠足,是么?”
他忽地心一痛,柔声道:“寒枝伤心了?”
她摇摇头,望向他的乌黑瞳仁忽然避开他的眼眸,小脸上,晕出一层红霞,小声嗫嚅道:“可东山笑话我,说天下间没人会娶这么大脚的女子为妻。”
他强抑着笑意,正色更正她道:“谁说的,连皇后娘娘尚且是天足,谁说我的寒枝会没人要?”
她听了,不禁露出喜色,一双杏目,欢喜不胜地望着他,小声道:“当真?”
他含笑点头应承:“那是自然!”
她顿时羞红了面颊,一朵笑靥,却再也抑不住,绽开于唇畔。
女儿家的心事就这样表露无遗,竟丝毫不知遮掩。仿似一朵小小的凝露海棠,虽素颜,却娇美鲜妍得不输于任何一枝牡丹国色。
他被她望得有些怔忪,随即掉转视线,直起男儿的七尺身躯,拍一拍襟袍之上沾染的青泥,含笑道:“枝儿还不走,看二叔为你带了什么?”
她不解地望着他,虽满脸期盼之色,却强忍着,足下却不动,一只小手藏在衣袖中,掩着裙裾。
他低头望着她,渐渐识破她的心意,终于忍不住,朗声大笑。
第四卷 崔嵬 第七章 海棠依旧(2)
那一年,他始为太子的侍讲,她,十二岁。
闲来无事时,他给了她府内其他稚子都不曾有过的特许,许她出入自己的书房,并悉心教诲。
他少时曾师从大学士宋濂。先师,向被先帝尊为“五经”之师,曾为太子讲经。因着爱他才具,故荐于高祖与前太子朱标。
彼时,他恨不能再将自己胸中所有锦绣,尽数哺入她心内。
一半,是出于对兄嫂早逝的疚愧之意,而,另一半的究里,只有他自己心内,才知道真正原因。
那一段短暂的时光,曾是他一生中,最须臾的刹那,也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才教了一课,他就察觉到自己门下收过的这唯一一个女学的聪慧。非但许多文章能够过目不忘,诸多教义,即便他只教一遍,她也能举一反三,窥及全貌。
他因着要辅佐太子,能够给予她的时间,越来越少,也越来越晚。
很多时候,当他回到府中,再步入书房之内,始发现——她已经等他等得伏在案前沉沉睡去。
她白日里还要研习曲艺和女红,许多次,他竟不忍心叫醒她,只让婉如领着丫鬟过来抱她回房。
有一次,婉如病了,他遂自己亲自抱起那个小小的身影,送她回卧房。
肌肤始接的那一刹,他听到自己的胸口处,跳得比重鼓还要凌乱不堪。他仓皇地放下她,交待了丫鬟了几句,逃也似地回到书房。
一个人,独对窗外的月色,独坐至天明。
待天际泛出鱼肚白,她循了笛音,寻至后园的松漪亭,却看见他一个人立于亭内,吹着手中的长笛。
她望着他,小脸上,满是毫不掩饰的倾慕与依赖之意。是,他的笛音,比之她的教席,只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她却不懂得他的心思。
她听了片刻,忽然拎起裙裾,就在那石阶之下的方寸之地上,翩然,起舞。
日轮尚未升起,月轮,宛如月白色的玉盘,低悬于长空。天地万物,在那一瞬间,皆失却了颜色。
他停了笛音,只淡淡一笑,借口早朝,就丢下她旋即离去。
自此之后,他停了她的书法课,不再像之前那般亲自教她习字,另为她请了西席。
但,渐渐地,还是露出了一些端倪。
府内人,都道他宠她,可说是异口同声。就连婉如,都笑言他偏心,说他对阖府内的所有晚辈,甚至是自己的幼子,都不曾如此上心过。
他并不否认,也自认瞒得滴水不漏,只,在那一日。
婉如因着患病,一直未能再孕育,见他自外返家,遂,再一次提出要为他纳妾。这一次,他没有再拒绝。
他也需要藉着外力,如果另一个新鲜的女子可以帮着他,他愿意再试一次。
当听到他的喜讯之时,他刻意隔着人群去辨她的眼目。
果不其然,那一刻,在众人的喜色中,她的沉默那么突兀,只立了片刻,那抹小小的身影便已消失不见。
一连数日,他借故忙于公务,停了她所有的课业,避而不见。他看出她的失落,于她,或许只当他为父,为父兄,可是他不能。
直至那一夜,终于熬到那一夜,他喝得大醉。
一身大红的喜服,竟不辨路径,不带一名家佣,醉醺醺地独自立于她的绣房前。
她在窗内,他在院中,一双人,默然对视。
屋内,燃着夜烛,映照出他身上的红,如此的浓艳和哀伤。他清晰地看见她眸中有一点光芒落下,仿佛,狠狠砸在他心内,生生地痛。
不知过去多久,他刚欲移步,忽听有人在身后惊呼了一声。
他回转身躯,竟看见婉如携了两个贴身的侍女,捂着嘴巴,呆立在廊下。一张容颜之上,惊恐失色,仿佛天地都倾颓。
是,他的天地,早就倾颓了,天崩地裂,万劫不复。
第四卷 崔嵬 第七章 海棠依旧(3)
她提着裙裾,自屋内走出,走至他跟前。他望着她,强忍着心内的剧痛,哑声,斥责道:“跪下。”
话音甫落,她似惊了一下,却什么也没有说,屈膝跪于他面前。
他低头看着自己足下蜷缩在一起的小小身影,强自镇定道:“二叔,平日是怎么教你的?”
他的话语很冷,他从来没有对她如此厉色过,一是怜其自幼罹丧,二来,她素来乖巧畏生,根本无需他多约束。
但此刻,他不得不为之,他必须要力挽狂澜。
不管眼前人信不信,她尚是个孩子,年方十三岁的孩子。即便,她心内对他亦有依恋,或许于她,只是一种兼了对父兄的倚仗之情。
他日,她终还要嫁人,还要为人妇,为人母,他不能因了一己之私,毁了她一生。
果然,婉如似松了口气,在他身后,好言赔笑道:“希直,刚才席上弟妹不过就是一说,小孩子间拌嘴那是常有的事,而且东山确实顽皮,平日里,向来都是他欺负寒枝的多。”
见他不答,遂,又向她道:“枝儿,你赶紧和你二叔说句软话!”
他遂加重了语气,沉声再接道:“寒枝,你没有听见你二婶的话么?你年纪渐长,规矩都长到哪里去了?!”
婉如赶紧在旁打着圆场,笑道:“还不是你平日里惯的她?如今,借了酒,偏偏要这个时候教训她,等酒醒了,又宠上天去。”
她瑟缩了一下,终于开了口,抬起眼睫,只望着他一人,轻道:“二婶,寒枝错了。”
婉如素来知道他的脾气,即刻长舒了一口气,轻拍着自个的胸脯,告慰道:“算了,你三婶也是为你好,女孩子家,心性最要紧,要懂得礼让,怎能由着自个性子来,连长辈都敢冲撞?刚刚在席上,你三婶好生抱怨了我们好几句。你自幼失诂,都是我和你二叔教养你,你三婶当众那样说,连老太太听了都不开心。你二叔此刻教训你几句,原本是该的。还不和你二叔认个错?”
他心内一颤,却咬着牙,不开腔。
果然,停了有片刻,他的寒枝终于应道:“二叔……侄女知错了。”
他硬是被她的话噎得生疼,盯了她半晌,终于拂袖而去。步履,却踉跄着仿似逃离,其实是如履薄冰,举步维艰。
她秉性聪颖之至,此刻,这样称他,再自称,无疑是伤他,伤己。
但,自他新婚那夜起,一连多日,她都高热不退,请了几个大夫,直拖了数月,才渐渐大好。
而,他以为可以藉此瞒得过一时,可是,在她大好那一日,他终被母亲叫了去,屏退了屋内所有佣仆,才细细锁了门窗,叫他跪下。
确实,自她病重起,他再也不曾碰过新纳的何氏,包括婉如在内。听说她为此被母亲叫至房内斥责,终是,忍不住,泣不成声。
原来,那一夜,她不过是陪着他,演了一出好戏。
他们三个人,都是台上的戏子,只为演给身旁的佣人看。
事已至此,他并不想再否认。在那一刻,看着泪流满脸的老母,他始知,有些东西,纵使他再怎样力挽狂澜,注定是无可挽回。
素白的纸张,就了烛焰,随即,在他手中,一点一点,燃成漆黑的灰烬。
曾经每一个夜阑,只要他打开书房内的轩窗,就可以听见那一阙《越人歌》,与他不过只隔了一道街市。
她的笛音,他岂会不识得?
他掩了狂喜,走至门前,打发小厮去对面府邸问。看门的守卫听到相问,反倒先问他们的底细道:“敢问你们是哪家府邸的?”
小厮指一指斜对面的方宅,赔笑应承。
听到此言,对方始含笑接道:“哦,原来是对面方大人府内的。我们这座宅子,是四皇子燕王殿下名下的,小官可有事?”
他怅然而退。
燕王。
黄雀捕蝉,当以螳螂诱之。他朱棣心计深远,自是堪比黄雀,他的寒枝,乃成了他与太子间夺嫡的筹码,只为诱他方孝孺入瓮。
一街之隔,一脉之隔,无论于何时,在何处,他与她,都一样隔着沧海契阔,永难逾越。
第四卷 崔嵬 第八章 关山度若飞
她刚把一件单衣覆在他身上,他便惊醒了。抬眼望见是她,遂笑道:“你怎么来了?”
她看一眼身后的丫鬟和小厮,轻斥道:“怎么在书房就睡了,天气越发的凉,怎么连个下人也不在身边,都怎么服侍的?”
众人无不低眉噤声不敢言语。
他淡然一笑道:“无碍,是我让他们各自去的。”
再看向窗外的天色,已隐隐透出光亮,他直起身,准备去洗漱。再过片刻,便该是他赴早朝的时辰了。
婉如随在他身后,看着他净面梳洗,忍了许久,终是在身后,低低道:“听说……南军又败了?”
他将手中的面巾交给一旁的佣人,一面接过漱口的青盐和茶水,在俯身的刹那,反问她道:“你听说了?”
她忧色道:“街上都传遍了,我也是听那些下人说了些。”
朝廷于八月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