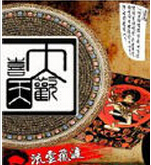欢喜-独木不成林_完结_派派小说-第3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尔夏。”欢喜喃喃唤道。
尔夏把手慢慢地放在欢喜的小腹处,他觉得似乎比昨日摸起来大了一些。他充满了怜惜地轻轻抚*摩着欢喜的肚子,欢喜侧过头,看到尔夏那样专注的目光,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温情。她突然给尔夏讲起了自己的母亲,讲起了已经亡了的景和国,那里的绵绵细雨,那里的脉脉春情,甚至是冬日里呼啸着的北风,都透着几分美。
欢喜鲜少提起自己的事情,尔夏认真地听欢喜的讲述,他眼睛里始终含着暖暖的笑意:“等这孩子出生之后,我们便去景和国看看吧。”
尔夏一边说着,一边褪去欢喜的罗裙,他故意把欢喜的手引到自己的亵裤上,用眼神央求着欢喜。欢喜解开尔夏的裤带,那个庞然大物不期然地撞进了她的眼睛。屋内只有一盏橙色的烛灯,一切都朦朦胧胧让人看不清楚。
欢喜太累了,一阵倦意袭来,她闭上眼睛。尔夏长大嘴巴,看着身边的女子陷入了梦乡,他真想掐住欢喜的脖子,好好地惩罚她一番。但他又不舍得,只能郁闷地半卧在欢喜身边,注视着她的脸。
不知过了多久,欢喜幽幽转醒,她一睁开眼睛,正对上尔夏那有些霸道的目光。
“你的胳膊?”欢喜发现自己还枕着尔夏的胳膊,她赶忙起身坐了起来。
尔夏耸耸肩膀,轻描淡写地说道:“只是麻了而已,一会儿就好。”
“你一直没睡?”欢喜惊讶地问道,尔夏探过头,含住欢喜的嘴唇,深深地吻着。
他们二人手牵着手躺在床上,又说了一会儿话,这才睡去。
第二日清早,欢喜醒来时发现,她和尔夏的双腿纠缠在一起,而他们的手,竟然整夜都未松开过。欢喜有些动情,她俯下身,顽皮地用自己散落在腰间的长发轻扫着尔夏的鼻尖。
她见尔夏的睫毛上下飞舞着,便知他已经睡醒。欢喜见头发攻击没有效果,便用自己的鼻子在尔夏的鼻子上磨蹭着。她玩得忘乎所以,被尔夏逮到了机会,不清不重地咬了一口。
“你这小娘子,竟敢趁朕睡觉的时候图谋不轨。”尔夏得意洋洋地睁开眼睛,哈哈大笑着。
水草站在房门口,焦急地转着圈子,她犹豫着要不要把昨夜炎原跟她说的话转告给欢喜。
第二十二章:代价
欢喜对于烟容的感情,一直颇为复杂。
亲姐妹同嫁给一个男子,这本不算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但偏偏,花秀和应竹这两个人,就像是冰与火,永无相容的一日。花秀费尽千方百计,终于从自家姐姐手上夺走了皇帝。她那样趾高气昂,洋洋得意地站在应竹面前,只盼着她会跪倒在自己脚下痛哭流涕,要不然就破口大骂。
但应竹却只是坐在窗台边上,安静地品着香茗。过了许久,她才抬起头,若无其事地看了花秀一眼。那一眼,却令花秀不寒而栗。她搞不懂,明明自己是胜利者,但为何姐姐应竹却一派平和,仿佛她完全不在意自己的妹妹爬上了皇帝的床似的。
“你若是来向我炫耀,大可不必。”应竹缓缓放下手中的杯盏,淡淡说道。
“姐姐,你难道不恨我吗?”花秀瞪着应竹那张因生病而显得越发憔悴可怜的面孔问道。
“恨?”应竹抿嘴一笑,不再言语,花秀站了一会儿后,便一甩袖子,忿忿离去。
欢喜记得,那时候自己怯怯弱弱地走到应竹身边,应竹吃力地抬起胳膊,捋了捋欢喜耳边的碎发说道:“欢喜,永远都别轻*贱自己,无论你是公主还是贫民。”
那时的欢喜,并不懂母亲话里的含义,她只是点点头,温驯地靠在应竹的脚边。而现在,欢喜觉得自己能慢慢体会到当年应竹的心情。因为她身边,也有了那么一个刁钻任性,自以为是的妹妹。
清晨十分,尔夏刚离开椒房前去大殿上朝,水草便焦急地冲了进来。她支走了其他下人,一把拽住欢喜的胳膊:“娘娘,昨日您让我把丞相府送来的东西都扔掉,我……”
“你打开看了?”欢喜轻轻笑了一声:“看到了什么?”
水草一怔,昨晚她拿东西朝御花园里的镜湖走去,偶遇了正在当值的炎原。她这人性子直,见到熟识的炎原,不待炎原开口询问,她便噼里啪啦说开了。
“真搞不懂娘娘这是怎么了,好端端的非让我把这些东西扔进湖里。”水草不解地说道:“白白糟蹋了这些值钱的宝贝。”
炎原皱皱眉头,他心知欢喜不会做那些无理取闹之事:“这盒子里装了什么?娘娘叫你扔掉,定有娘娘的理由。”
水草并未打开看过,听炎原这么一说,她反而有些好奇地打开了锦盒。里面整整齐齐码放着两只浅绿色的琉璃杯,这杯极为珍贵,就是在六弓国的后宫也不过只有一只而已。水草不禁忿忿说道:“这个丞相,果真如传闻中所说,不知敛取了多少民脂民膏。”
炎原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只琉璃杯,在灯笼前细细地打量着:“这杯上有毒。”
“什么?”水草不可置信地望着炎原。
“嗯。”炎原点点头,十分肯定地说道:“这并非是一般的毒,而是在制作这杯盏的时候,被烧制进去的毒。若是用手碰触它,并不会染毒,但如果倒上一杯酒,那酒香就会引出这杯中藏着的毒。只需一口,人便会昏昏然倒下去。旁人只以为他是醉了,殊不知,却是中了这琉璃之毒。这毒并不会顷刻发作,而是要整整沉上数日才会夺去人的性命,一般人决计不会怀疑到这个杯子身上。”
“啊?”水草吓得张大嘴巴:“这么说来,丞相要害娘娘,我底赶快去告诉娘娘。”
“你且慢。”炎原拽住水草的胳膊:“既然娘娘让你扔掉这锦盒,自然是猜到里面装着的东西是什么。你也不用太过着急,待明日陛下去上早朝,再向娘娘禀报也不迟。”
水草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她突然拉住炎原的袖口,郑重其事地说道:“我先代娘娘谢过你,待我明日禀告娘娘之后,定会重重地嘉奖你,提拔你做娘娘的贴身侍卫。”
“万万不可。”炎原有些慌张地说道:“我只是一个粗人,碰巧听人提起过这个杯子而已。再说,娘娘正怀着小皇子,怎可让我这种被毁了容貌且母亲已死的人去伺候呢,若是惊吓了娘娘,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就算不挑拨,那嘉奖总是要的吧。”水草说着一甩头,胡乱把杯子塞进锦盒里,蹦跳着跑开了。她一边跑,一边不忘回头对炎原说:“你就放心吧,我定求娘娘赏赐你。”
“水草?”欢喜见水草晃了神,便轻轻推推她的胳膊。
水草啊了一声,忙不好意思地傻笑了一下说道:“娘娘,这杯子有毒,那丞相想加害您。”
欢喜瞥了水草手中的锦盒一眼,冷冷说:“休要胡说,丞相大人对陛下和本宫并无二心,更不可能加害于我。你为何不听本宫的话,把这锦盒丢掉呢?”
“娘娘……”水草急得涨红了脸,她有些语无伦次地说道:“这是火儿告诉我的,他是个傻大个侍卫,绝不会骗人。娘娘若是不信,就把这杯子里倒上酒。喂给狗儿吃,看它会不会死。”
欢喜一把夺过锦盒,摔在地上,只听几声清脆的声响,琉璃杯摔成了碎片:“还不快去清扫干净?!”
水草百般委屈,她低着头,微微抽泣着去打扫地上的小碎片。她搞不懂,为何欢喜会这么固执,未加思考便认定丞相没有谋反害人之心。
看着水草那副沮丧的样子,欢喜别过头去,轻不可闻地叹了一口气。
昨日庆功宴上,她无意中瞥见妹妹烟容的唇角浮现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那笑容乍看起来,十分甜美。但若是熟悉她的人便会知道,每每她这样一笑,就意味着她想出了整人的点子。掰断自己脚趾那次,她也是这样笑着,仿佛在看一出温情的评戏一样。
因为太过熟悉这种笑容,欢喜的心瞬间缩紧了。她十分确定,烟容在打坏主意。特别是宴会散场之后,她对自己表现得太过热络,这一点都不像是她。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烟容可以成功地伪装自己的表情,装成一个好妹妹的样子,但却无法掩饰她眼神里的恨意。也就是源于此,欢喜才会一回到椒房,便吩咐水草扔掉丞相府送来的东西。
烟容和她娘亲花秀一样,见不得别人好,好妒,善用下三滥的手段对付别人。这对母女,倒还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烟容忽略掉了重要的一点,欢喜并不是应竹,她性子冷清,但却并非可以任人宰割。特别是自她怀孕之后,她觉得自己必须坚强起来,要保护未出世的孩子和性情单纯的尔夏。
下毒一事,丞相关尹定不知情,他虽然好弄权势,却没有谋反之心。眼下朝政刚刚稳定下来,若是爆出丞相企图毒害皇后一事,只恐怕又会闹得天翻地覆,为了尔夏的皇位也为了六弓国的江山社稷着想,欢喜选择瞒下此事。但这些话,她又不好讲给水草听。
“你这是在生我的气吗?”欢喜幽幽问道。
“女婢不敢。”水草一扭脸,小声回话道。
欢喜走到水草身边,伸手搂住她的肩膀:“水草,很多事,我没法解释给你听。”
“娘娘。”水草抬起头,眼里含泪望着欢喜。
“好了好了,我心里都明白。”欢喜擦擦水草眼角的泪水,温柔地说道:“不如这样,你把这锦盒连同碎了的琉璃杯送还给丞相府吧。”
欢喜一直拿捏不准,应该如何应付烟容。她们是不共戴天的仇人,亦是互取性命的敌人。欢喜曾隐隐约约期盼着,她和她不会走上自相残杀的那条路,但似乎冥冥之中自有某种安排,她们两人之间,一定要分出个胜负。
“水草,那个叫火儿的侍卫,就赏赐他十两银子吧。”欢喜像是想到什么,她慢悠悠地说道。
水草还想替炎原说上几句好话,却被欢喜一挥手打断了,只得低着头出了椒房。
欢喜并不想知道火儿是谁,更不想知道他是如何与水草相识的。应该说,她是害怕知道那个人的真实身份。自从回宫以后,她总觉得有人在暗中窥视自己,那并不是居心叵测的眼光,而是一种饱含温情的注视。欢喜的心没来由得颤动了一下,她曾有一瞬间,想要抓住那个目光,看看自己的猜测是否正确。但那种想法只在她心头盘旋了一刻,便悄然无声地消失了。
早在她骑上马的那一瞬间,便注定了他们俩不过是偶然相遇的路人。
午后,欢喜带着宫女们前往御花园赏春,不知是谁提议,宫女们玩起了投壶游戏。大家在院子中央摆了一个阔口铜壶,分成两组,以投中的多寡来判定胜负,欢喜只是坐在一边看她们兴高采烈地玩耍着。
初春的午后,阳光暖洋洋地照射在众人身上,有几株桃花早已按捺不住寂寞,纷纷张开了笑颜。皇帝尔夏和太傅子寻刚刚从御书房里出来,他们远远便看到欢喜坐在桃花树下,面容恬静美好,令人不禁痴痴地想,到底是桃花映红了人面,还是人面点缀了桃花呢?
水草所在的那一组只差一支长箭便可获胜,她们几个姑娘你推我,我推你,谁也不敢投这最后一箭。倒是欢喜笑着走到她们面前,接过长箭,她的体态十分优雅,步履从容,沉了片刻,瞄准壶心投掷出去,那箭直直地飞入了壶中,发出清脆的撞击声。
尔夏一边鼓掌,一边大步朝欢喜奔来。欢喜刚想行礼,却被尔夏一把抱住了腰:“朕都不知道,我的小娘子竟然会投壶呢,下次可要和朕比上一场。”尔夏一边说着,一边故意把欢喜按在自己的胸前,那副洋洋得意的样子,看得子寻只想翻白眼。
“陛下。”欢喜用胳膊肘暗暗捶了捶尔夏的肋骨,尔夏故意哎呦一声,他懒洋洋地靠着欢喜的肩膀,压低声音,故作暧昧地说道:“娘子刚刚投壶的动作太吸引人了。”说着他还不忘瞥子寻一眼,“为夫担心,会被不良人士看到,种下恶念。”
“恐怕是陛下不怀好意吧。”欢喜见尔夏眼里冒着小火苗,心知这家伙是随时随地都能喝上一碗老陈醋:“还有旁人在,陛下请稍微收敛一下,切莫令臣妾感到难堪。”
“娘子这是什么话。”尔夏不高兴地撅起嘴,嘟囔道:“难道为夫和娘子恩爱,有人敢质疑吗?”
子寻没忍住,噗哧一下,笑出了声来。尔夏怒视着他那张笑得堪比桃花的面孔,咬牙切齿地说道:“太傅大人可是羡慕朕与皇后情深意重?朕看太傅大人年龄也不小了,不如让朕亲自给你挑选一位夫人如何?”
“微臣不敢劳烦陛下大驾。”子寻忙俯首说道:“微臣只想伺候在陛下身边,为国为民尽一些绵薄之力。”
“陛下,既然太傅大人已经这样说了,您也就别再强人所难。”欢喜适时地插话进来。
子寻抬起头,用眼神对欢喜说,这样一个任性的皇帝,恐怕也只有你才能忍受。欢喜还给了他一个笑容,仿佛是在告诉他,偏偏我就是喜欢尔夏的任性。
“喂喂,你们俩这儿眉来眼去,当我不存在啊!”尔夏一把捂住欢喜的眼睛,恶狠狠地说道:“不许瞧他,他有什么好瞧得,又瘦又高,一阵风吹来就能刮上城楼。”
宫女们全都垂着头,死咬着嘴唇,生怕发出一丝笑声让皇帝怪罪。只有水草不明所以地望着欢喜,她觉得太傅大人和皇帝怪怪的,却说不出到底什么地方怪。
“越说越没边儿了。”欢喜嗔怪道:“太傅大人,以后还要麻烦您费心辅佐陛下。”
“臣自当竭尽全力。”子寻嫣然一笑,他施过礼,转身要走。
“你等等,朕话还没说完呢。”尔夏指着子寻的后背,大声吼道。
子寻侧过头,温柔地对欢喜说:“娘娘还是早些回宫吧,乍暖还寒之际,别冻着自己。”
欢喜点点头,没说什么。
这些天,尔夏每次和子寻争吵,都没讨到什么便宜。他见欢喜也不站在自己这边,不禁有些气结,嘟着嘴,气呼呼地跑回椒房。
水草搀着欢喜的胳膊,有说有笑地跟在皇帝身后。一进屋,尔夏便倒头躺在了床榻上,用被子蒙住脸。他本以为,欢喜会担心地过来瞧瞧自己,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