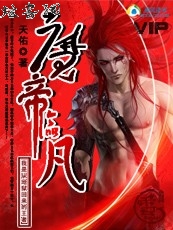网人 作者:黄孝阳-第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提,静默无声息。楚山鸟语悒,空谷回音稀。枝疏暗香袭,影清拂君衣。良辰勿叹惜,醉眼苍穹低。你的声音暗哑无力,断断续续,像一群无精打采在寒风中颤抖抖的麻雀。你已不再年轻。血液中的热量现已沉淀,除了给身体带来种种不适,已无任何益处。原来那个在酒酣时思前想后慷慨而歌的“我”应该是死掉了。这种“死”与生无关,它是血腥的,是玻璃瓶的碎碴子,是扔在屋后的鱼的内脏。它并非传说中能将一切暮气沉沉的洗涤干净的清洁剂,反而有股子腐烂味。你皱起眉。一个学生模样年轻人踩着车辘轱从小巷那头来过,瞥了你一眼,随口抛下“有病”两个字。你忍不住笑了,自己确实搞笑。
9
流星从天边一颗颗划过,漆黑的夜穹美得一塌糊涂。什么时候,自己才能变得天上的星星?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人。青石板,石板青。青石板上钉洋丁。你在夜里独自逛着。城市的深夜只有在马路边和衣而睡的乞丐、疯子,对了,还有你自己。你朝远方的光亮处慢慢走去,想去喝一杯酒。在城市里,就是这点好,不管何时,总能找到某个地方买来一瓶酒。
你慢慢走着,每个人每幢房子甚至于这街道上的每一处,都是一个个梦。在梦中行走,自己却也是个梦,这有些滑稽。拐弯处,一盏孤伶伶的灯光正默默地眨着眼睛。你心中一紧,快步走过去,店面不大,一个男子正趴在柜台上。他睡着了吗?你敲了敲柜台玻璃,男人仰起头,枯瘦面容,两眼混浊,眉间似有无数疙瘩,嘴角往下耷拉着,像在嘲讽什么,又似正苦闷至极,形容猥陋,仿佛谁都欠了他三百两银子。这种尊容能招徕生意?你脸上浮起笑容,“老板,给我拿瓶酒。”
男人打了个哈欠,“要什么牌子的?”白酒太烈,啤酒太淡,葡萄酒太甜,它们都是酒,滋味却截然不同,有的一小杯就可令人晕眩然后开始装疯卖傻;有的喝完一大瓶,还是清醒得很,只能满嘴苦涩。你的目光在琳琅满目的货架上慢慢扫过。你看见一瓶包装古朴的酒,伸手指了指,“就拿那瓶吧。”男人把酒拿下,递过来,“十八块”。这是瓶虎鞭壮阳酒,你这才看清瓶子上那几个黑字,不觉好笑,一只老虎只有一条虎鞭,这世上会有多少只老虎?前些日子你在份旧报纸上看过一份过时的报道。说一个记者乔装打扮潜入正被广告炒得沸沸扬扬某牌子鳖精的加工厂房,结果发现,整个工厂只有清水缸里趴着的几只巴掌大的王八,缸两头装有龙头,这边进水,那边出水,流出的水再添上点糖精香料就是鳖精。想来,这虎鞭酒的生产工艺,也大抵如是。你掏出十八块钱递过去,你并不奢望酒里真会有那么一星半点儿的虎鞭。十八块钱,又能买个啥?若能买来这酒名中的某种暗示,也是不错。
拧开酒瓶盖儿,店门口有把椅子,你坐下来。夜色还是在漫无目的地飘来荡去,活像一群找不到家的孩子。你仰起脖,咕咚声灌下一大口,剧烈地咳嗽,酒里有种浓重的药味,好闻,并不好喝,涩,舌头发麻,有点像泪水。你没尝过女人的泪,但也曾把某个时刻从自己脸上莫名其妙滚下的泪水用指尖拈起粒放入嘴里,你记得这种滋味。瓶子很重,沉甸甸,你翕动鼻翼,微闭上眼,仔细回味。你还是分辩不出酒里到底放了什么,便侧过头,对着光,仔细地看。瓶子上这几个黑体字写得很漂亮,不是印刷体,似某名家手笔。也许名人更需要壮阳,其实说起来谁不需要呢?软的想硬,硬的想更硬,更硬的想最好是一根铁。人心是不会知足的,所以才会有人心不足蛇吞象这话。你舔着自己的嘴唇,头晕乎乎,这酒毋论是否会壮阳,劲倒是挺大。
这是个阳痿了的社会,你嘟囔着,理理自己的头发。她现在一定是与几个男人在牌桌上兴高采烈吧。哗啦哗啦的麻将声,可能真的比这世上所有的人声、音乐声、天籁声加起来都好听些。恍惚中,你感觉肩膀被人拍了下,然后是一个沙哑似乎正在不断咽着口水的声音,“老板,要小姐吗?”
你有些疑惑,扭过头,是卖酒的那个男人,竟搬了把椅子在自己身边坐下。他的脸好像在慢慢摇晃,不过感觉已没有刚才那样丑陋不堪。你礼貌地对他点点头,没说什么,又灌下口酒,这下喝急了,酒呛入鼻子里,像有人在鼻子上重击了一拳。你的手一松,瓶子掉在地上,拍地一声,碎了。那些可以让人晕乎乎的液体泛起一堆白色泡沫。你呆呆望着,是的,它们只不过是些泡沫,又会有什么大不了?碎了也就碎了,碎了也好,日子本来就是碎的。
“老板,要小姐吗?很好的,不贵,给你打八折?”还是那个男人锲而不舍的声音。苍蝇不叮无缝蛋,自己看起来是否像个嫖客?说来也好笑,近三十岁的人哪,只有过她一个女人。不是说没机会,不是说不想别的女人,很多个夜里,独自卧在床上,你真的很想有个女人能抱着你,能让你暖和些。会有这样的女人吗?你没有去找过小姐,虽然并不觉得做小姐有什么可耻。有人说,权财悦人,美色悦人,文章悦人,三者并无高下之分,你也觉得是,再怎么说,做小姐还是要付出劳动,用某位哲学教授的话来说,她是这世上惟一靠自己挣钱的人。她靠不是商品的商品挣钱,出售服务,这种服务建立在属于她的资源上。而其他人靠的却是土地、矿藏、老板、合作伙伴、关系网挣钱,毋论他们所从事的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还是第三产业,他们出售的农产品、石油、服务等等资源并不是真正属于他们。而这总比那些不劳而获还要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好点吧。
你想自己之所以没去找小姐,只是觉得那些女人并不会给你暖和,还有,你隐隐约约也有点怕,谁敢保证小姐没有性病?性病打一针犹可没事,艾滋病呢?你不喜欢戴套子,或者它是安全的,但也是乏然无味的。做爱是与女人做,不是与套子做。几年前,你与她试过一次后,就再也不肯用了。你喜欢真正地躺在那湿润的地方。你也想找情人,但问题是能被你看上眼的女人,人家又会看上你吗?说实话,你也常纳闷,她当初看上自己哪里,为何就肯嫁给你?这应该是一个误会。你没有去问她,她也没对你说。你想也许是她晕了头,也许因为原来的那个自己还讨女人喜欢,人是会变的,自己就变得越来越不讨女人喜欢。你有些怅然,看上的找不来;看不上的,找来又有什么意思?还是不会暖和。你摇摇晃晃地站起身。你并没有醉,只是被夜风吹得有点儿头晕。你伸出手,扶着椅背,听见自己嗓子里冒出个声音,“在哪?”你吓了一跳,是自己说的吗?
男人忙伸手向店里一指,“就在里头,安全的很。”你迈步刚想往前走去,男人拦住了你,“老板,先付钱吧。”你笑起来,“没看货色就付钱?生意不是这样做的吧?敢情,你是才入行?”既然别人以为自己是个嫖客,那不妨就多一些敬业精神。你不喜欢找小姐,门道倒听了不少。男子脸上有些犹豫,这让他的丑脸又好看了些,“好吧,我与你一起进去。”一个女人仿佛刚从睡梦中被人推醒,茫然地坐在床上。里面很小,就几个平方米大,堆满各种纸箱,你皱起眉,这里怕是想伸个懒腰也会撞痛头。女人并不漂亮,也没有化妆,灯光下,脸有些柔和,看见有人进来,便忙不迭,边用手梳理略有点凌乱的头发,边打量着你。男人又伸出手,小心翼翼问道,“老板,满意吗?”你没有回答,扶着墙,在包装箱上坐下,你很倦,也不想说话。男人的声音大了些,“老板,行情你知道的,我也不多喊,八十块,一口价。”
你想笑,男人的目光勾子般紧盯着你的上衣口袋,仿佛里面有金山银山,男人没有乱喊价,这种街边的女人是这个价。你掏出伍拾元,递过去,“行情是伍拾元,就这么多,你要就要,不要就拉倒。”你听见自己粗重的呼吸声,感觉自己正一点点从身体里飘起,这个正坐在纸箱上说话掏钱的人好像并不是自己。刚喝下的酒真有点儿奇怪。男人有些犹豫,望了眼女人,女人微微地点了下头,男人脸上又堆起笑容,“先生,她刚出来做,你看能不能再多给点?保证让你舒舒服服,不舒服就退钱,行不?”你再也忍不住,哈哈笑起来,敢情这是在菜市场买菜?你有些不耐烦,又摸出伍拾,挥挥手,“不用找了,这是你说的,不舒服就退钱。”那男人可还真没想到你不仅没少给,反而多给了二十,嘴咧在后脑勺边说边往后退,“老板,你放心,包你满意,包你满意。”一不留神,脑袋在门框上狠狠一撞,扑通一声,人跌出屋外。
这下,那女人也笑起来,牙齿很白,这让她的笑容很生动。你没有继续往下笑,就与刚刚忽然没有了讨价还价的兴趣一般,你开始仔细地看女人。你付了钱,那么在这短短几个时辰内,这个女人是属于你的,这世上绝大部分的东西都可用钱买到,你想,上衣口袋里若真有座金山银山,是否就能找到令自己暖和的女人?头很痛,女人正脱着衣服,乳房上有一块淡淡的青紫,很瘦,似乎真是刚做这行不久,连女人衣服是要男人脱才更刺激这道理都不懂。你看着女人弯腰褪下最后一件衣裳,闭上眼睛,想起她,若是此刻她能推门进来,会跳起来叫吗?若是那样,那可就令人太开心了。生活如此乏味,所以大家都喜欢找些乱七八糟的事,来令这些乏味的生活看上去不那么乏味。女人说话了,“老板,不上来吗?”
你还是没有说话,也不想动,这样坐着就挺好。你睁开眼,捋捋头发,对女人招招手,那男人不是说保证满意吗?还真想看看女人会如何令自己满意法。女人咬了下嘴唇,眼睛里似乎有点害怕,她怕什么?你叹口气,站起身,朝床边走去。这上面躺过多少个男人?你没脱衣服,把自己重重地扔在床上,床板很硬,让脊梁隐隐生痛。女人的手伸入你衣服里,很冷,你哆嗦了下。冷而且干燥,你皱起眉。女人意识到什么,开始亲吻你的胸膛。舌头是柔软的,牙齿是坚硬的。你抚摸着女人光滑的脊梁。你摸着了那些硬梆梆的骨头。骨头会化作灰的,人都是要死的。女人想去关灯,你拉住她的手,她的乳房晃晃悠悠,很好看。你伸手情不自禁轻轻捏了下,仍然是冷,这里面有些什么?海绵组织,肌肉,对了,还有乳汁。女人轻轻啊了声。你是弄痛了她还是弄舒服了她?你忽然想起那块青紫,脱口而出,“你这里是怎么了?”
女人的身体似乎颤抖了下,犹豫了会,舌头更加温柔了,好像有些潮湿的花瓣在胸膛上一朵朵绽放,女人的手慢慢往你的身下摸去。“外面那男人是你什么人?”你握住女人的手,有些慌张,心脏不争气地拼命跳动,似就要跳出嗓子眼。女人的手愈发冷得厉害。“你躺下来吧”,你轻声说道,把被子拉来,盖在她身上,“别冷着了,着了凉不好。”女人显然有些诧异,没说什么,温顺地躺下,你闭上眼,搂住女人,没再问什么。你很倦,想睡觉,无论这女人是否可以给你温暖,很多时候,能有样东西抱抱也是足够。你听见女人的声音,“老板,你不满意我?”你睁开眼,女人的脸忧伤而又疲惫,你在她脸上摸了把,“不是的,我很满意。你能够让我抱抱,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你忽然感觉眼眶里已莫名其妙溢满泪水,忙闭上眼,已经来不及了,几滴清泪慢慢滚落,身体在刹那间僵硬了,自己怎么了?你扭过脸,良久,猛地觉得有几滴冰凉的东西正落在自己脸上,你回过头,看见女人泪盈盈的眼。“老板是个好人,我看得出来,老板还是第一次出来找女人吧。”你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你静静听着。泪水是莫名其妙的,人也是莫名其妙的,还会有什么不是莫名其妙的?女人慢慢地说着话,每个人都渴望说话,问题是他们能够说给谁听?所以很多人越来越不爱说话,他们已习惯了自己说给自己听。“外面那男人是我老公。”女人顿了顿,“他喝酒中毒,就成这样子。他年轻的时候长得挺帅的。”女子忽伸手用力抱住你,身子剧烈颤抖,“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活着本来也就是苦,若不觉得它是苦,那它就不苦。你还是没说话,你把头埋在女人胸前,这是个受了伤的女人。女人说道,“这个店也不是我们的,一个姐妹见我可怜,请我来帮她看店。厂里倒闭了,我和他没别的什么本事,没有文凭,学别人的样开过几家店都亏了,天天都有穿各种各样制服的人来收钱,孩子要上学要吃饭,他妈妈又病了,不晓得哪里有条活路呵。”女人的哽咽声渐渐地大起来。你静静听着,不管这故事是真是假,这与你并无关系。报纸新闻上,这样的事也太多了些。你都有点无动于衷,你只是更用力地抱紧女人,人都是自私的,不轮到自己头上,是体会不出其中三昧。“为何不找过个男人嫁了?”女人的脸已经苍白得没有一丝血色,“老板,不怕你笑,我都是出来卖的人,还有什么脸面抹不开?我也想啊,也想过找个能让我和孩子吃饱饭的男人嫁过,可谁会看得上我这种老女人?”女人幽幽说道,“还有,他怎么办?”
“你爱他?”这个问题可笑至极,但话已出口,无法收回。爱是什么?天知道,这世上本来不应该出现这个字眼,若是没有了这个字,想来大家也就没了这多稀奇古怪的梦,活着就是活着,形式往往大于内容,载体本身也就是意义。女人说道,“什么爱不爱的,那是你们有文化人说的话,我们哪晓得这么多?他是孩子的爸爸。”女人想了想,“其实,他对我挺好的。”你有些奇怪,“对你好,还让你干这个?有手有脚哪儿会饿死人?做别的不行,难道去工地上打小工挑砖也不会?”女人没言语了,好一会儿,“老板,你说对了,他现是在工地上干些零活,可那能挣多少钱?上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