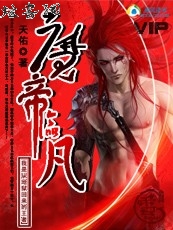网人 作者:黄孝阳-第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看着。妈妈怎么就不起身擦一下那男人滴下的口涎?这男人真脏,你看着那男人微微凸起的眼球,有些害怕,缩起头,屏声静息。似乎过了很久,又似乎才过几秒钟,妈妈与那男人终于爬起来,说着一些你听不懂的话,紧紧拥抱在一起,似乎就像不要了命。妈妈好像哭了?妈妈的眼泪为何老流不完?那男人噘起嘴在妈妈脸上啃来啃去。妈妈穿上了衣服。妈妈不穿衣服时真好看。男人也穿上衣服,男人不穿衣服时也好看。妈妈与那男人一前一后走出水房,妈妈为何忽然掩脸朝前山跑去?男人为何只追了几步就停下来扭头朝后山走去?
你把蜷曲已久的腿缓缓伸直,心中溢满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但绝对不是浆糊。阳光真冷,老天爷说翻脸就翻脸,一大朵乌云眨眼间就已从远方窜来,发出乒乓乒乓的声音。你打个寒颤,顺手捻死一只爬进脖子里的蚂蚁。蚂蚁的尸体上似乎有一股好闻的香气。你抽抽鼻子,侧过身,一点一点蠕动,出了铁管,然后仰面躺在草地上。黑云越来越多,有的像剑,有的像刀,有的像斧头,满空都是形状各异的兵器在飞。你叹口气,良久,从草丛中爬起,爬了一会儿树,又捡起石块朝山下的林子扔去,仍觉得不安,吹起口哨。口哨声在树叶上滴溜溜打着转,天渐渐黑下去了,像一个锅底严严实实地盖在山的头上。
你回了家。妈妈正在厨房把一大瓢水添入锅里。水在锅里发出咕咕的响声,一些水蒸气飘起来,妈妈的脸模糊不清。你没说话,勾着头,吃过一大碗加过红薯的稀饭,心里恍恍惚惚,屋子里原本很平常的东西都散发出一股意味深长的味道。昏黄的灯一摇一晃。爸爸蹲在厨房门口就着淡淡的月光大口大口地喝着水。水喝急了。爸爸用力咳嗽。妈妈走过去,欠下身,用手拍着爸爸的脊背。爸爸的脸上满是皱纹,没有水房里的那男人一半好看。你伸出手指沾了些口水粘起桌上的饭粒一粒一粒放入嘴里,望着墙壁上高高挂着的那杆黑乎乎的猎枪。爸爸是用它去深山里面打猎的,可爸爸从来就不肯让你碰一下它。有一次,爸爸出去了,你搬了把椅子去摸那枪,可你的指尖刚触到冰凉的枪身,椅子就歪了,你结结实实地从上面摔下来,摔得鼻青眼肿。你皱皱眉,起身去睡了。睡到半夜,醒了,心底凉凉的,就爬起来,望一眼窗外,抖落下身上的月光,扭开门,蹑手轻脚走到爸妈的窗下。屋里有爸爸呼呼的喘气声,像一个破风箱。你竖起耳朵,还是听不到妈妈的声音。你静静地发了一会儿呆,悄悄回到自己的床上。
第二天中午,你又去了水房。很快,你发现了妈妈与男人的规律,这让你很自豪。说真的,看妈妈与那个面目清秀的男人脱光衣裳在水房里打架,比逮蝴蝶有趣多了。你缩在铁管里不停地点着头,兴趣盎然,嘴里嘘嘘有声。你现在能估摸出妈妈在哪个时刻会叫出声,在哪个时刻拼命颤动然后发出啊地一声就一动也不动。这很有意思,而且很有节奏,原本无聊乏味的都因为这个而变得生机勃勃。草泛着香,风微微唱。你将手指头伸入鼻孔,觉得日子惬意无比。
忽然之间,咣当一下巨响,水房那扇破木门刹那间就已四分五裂。一个彪悍的人影闯入水房,紧接着又是一声巨响,你还来不及掩着耳朵,第三声巨响狠狠地轰入耳膜。铁管里发出嗡嗡的回音,额头蹦出汗粒。爸爸!你头一抬,头在铁管上重重一撞,金星冒起,爸爸!没人说话。巨大而又短促的响声迅速消逝,死一般的寂静,一泓鲜红的血从水房墙壁大窟窿里慢慢淌出,滋滋响着,冒出白气。你浑身僵硬,一动也不动。爸爸怎么跪了下来?那杆猎枪的枪口怎么在冒着青烟?这些血从哪里来的,又想流到哪里去?妈妈与那个男人怎么就像两只被人捻破肚皮的蚂蚁?眼前一黑,你晕了过去。一只蚱蜢跃上你肿得老高的后脑勺。
8
你是谁?我又是谁?千百万年的轮回中有什么东西不可以被重叠?两点之间,重叠最短,它让一切距离等于零,让所有参差不齐的都丧失厚度,不再拥有时间的光泽,重新回到宇宙洪荒时的那个无限大又无限小的奇点。
这是真的。有个村庄的小康之家的女孩子,生得美,有许多人家来做媒,但都没有说成。那年她不过十五六岁吧,是春天的晚上,她立在后门口,手扶着桃树。她记得她穿的是一件月白的衫子,对门住的年轻人同她见过面,是从来没有打过招呼的,他走了过来,离得不远,站定了,轻轻的说了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她没有说什么,他也再没有说什么,站了一会儿,各自走开了。就这样就完了。后来这女子被亲眷拐子,卖到他乡外县去作妾,又几次三番地被转卖,经过无数的惊险的风波,老了的时候她还记得从前那一回事,常常说起,在那春天的晚上,在后门口的桃树下,那年轻人。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
你不是很喜欢张爱玲的小说,非是嫌其从旗袍中抖落下的跳蚤,她的笔触太华美斑斓反衬得人物面目的苍白。笔调虽落寞,却只在一口不足尺余宽的井里汲水,情节琐碎,刻薄有余,从容不足,徒有井水之幽与碜骨之寒,而乏大漠孤烟日落长河,更乏了在高山巅将整个自己拎出万丈红尘时意态睥傲的悲怆。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件旗袍,里面不仅会有跳蚤,还有吃人的兽。被它包裹得紧紧的“我”,或许就是最凶猛的一只。
张爱玲的文章看过不少,独爱这篇344字的短文。文字虽淡,三起三折。文字背后是茫茫生死。时间与空间不停地重叠。没有死去活来,没有惊天地动,没有艰难苦恨,没有喜怒哀乐。这些东西已经被“重叠”这个动作一一被滤去。我们所渴望的爱,所汗流狭背追寻的幸福,不就是多年前“对门住的年轻人”么?
你把《童年》在网络上贴出后,有人在语言、视角、写作技巧上做出相应评论与批评。你很感激他们。但有一个老读者却给你写来这么一封信。她说,你的文章写到现在,我所能看到的,也只是你对肉体的追求而已。你写性,写得很好,但若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不停地将性写下去,那么你的写作生命也快要到结束的时候了。性是人生中比较重要的一部分,但是人还要靠其他的东西维持生命。相比而言,性并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一生只追求性,那就是我看错你了。你吓了一跳,自己真是一个对迷恋下半身气味的人吗?当时你回答是,很抱歉,不知道我的文章为何会给你这样的感觉。就《童年》而言,只是用一个孩子的所见试图揭示那个年代里的一些残酷与灰暗。环境描写是时代的底色,“爸爸”、“妈妈”更大程度上是作为一种象征符号存在。
还记得那个国外的广为流传带点颜色的笑话么?老师让同学回家后写一篇有关“国家”、党”、“社会”和“人民”的作文。爱莉丝不理解这些词的含义,就去问爸爸。爸爸告诉她:“国家是最大的,就像你奶奶。党是最有权利的,是一家之主,就像我。社会就是为党和国家干活,还得听党的,就像你妈妈。人民就是最小的,说什么也没人听,就像你。”晚饭后,爱莉丝想写作文,可是还不是很明白这些事,就去想问奶奶,可是奶奶已经睡了,就去找爸爸。爸爸和妈妈正忙着“床上运动”。爸爸一看她来,两个耳刮子就给打出来了。爱莉丝没有办法,只好抹抹眼泪,回房间自己写作文了。第二天,爸爸接到老师的电话:“你是爱莉丝的父亲吧。”“是啊,什么事”“关于爱莉丝的作文。”“是写的不好吗?”“不,是写的太好了,我怀疑不是他自己写的。”爱莉丝的作文是:国家已沉睡,党在玩社会,社会在呻吟,人民在流泪。
朋友默然了。你关好电脑,披了件衣服下楼闲逛。晚上大街上的人很多。这是一座陌生的城市,不大,非常精致,据说城市人口不过六十万,号称是地球上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有河从城市中央七曲八折绕过。河边有绿草、青树、竹林、嶙峋怪石、落满叶子的木椅,河里有游船、笑语、人影、桨橹水声、精美的食物。空气中有桂花的香味。灯光在水面飘动,像是一群有生命的东西。城在水中座,人在画中游。大大小小的楼房争先恐后将影子投入河里,溅起一圈圈涟漪。长堤、石桥等各色建筑上皆有一排排霓虹灯管,或红或蓝、或绿或黄,光华流转不定。远处有喷泉,水珠高高跃起。
一些碎了的玻璃在血液中流动。你在街头站住。红绿灯下有滩污迹。一个孩子几分钟前在这里跌倒。或许他的身手本来足够敏捷,事实上,他的攀援动作与一只猿猴没有多大差别,但人毕竟不是猴子,街道上的铁栅栏的锐角猛然扯住他的衣服,他在往前蹿时失去重心,头朝下重重地摔在水泥路面上,然后像一根枯树枝被滚滚车流折断、卷走。他应该是一个捡垃圾的孩子,有一些同伴,不过这些同伴在他倒在车轮底下后就都不见了。你弯着腰,默默地站在汹涌的黑色人群中。事情的前因后果都落在你眼里。他是为了抢在同伴之前捡到那个被人刚扔出来的易拉罐。他终究没有抓住它,手臂笔直地伸着,而那个易拉罐就在离他三尺处。他太急了,急得整条街道上都是救护车凄厉的喊声。
夜色继续涌动,整个城市流光溢彩,好像一个巨大无比的鸡蛋壳。可惜哥伦布已死去了很多年。这世上还有谁能把鸡蛋立在桌上?你仰起头,看着身边一块广告牌上那对更为巨大的乳房,琢磨了一会儿,觉得自己像一个要吃奶的小孩,便笑起来。许多声音与影子从身边急速掠过,一个乞丐卧倒在人行道上睁圆眼。你看他,他看你。你摇头,他叹气;你叹气,他摇头。你忍不住又笑起来,一个巡警从对面走过来,仔细地打量着你,上一眼,下一眼,目光不无厌恶,像是打量桌上一块臭肉。你只好对他笑,可他不笑,乞丐也不笑。警察刚想说什么。乞丐的臀部猛地传来一阵叽哩咕噜的脆响。警察捂紧鼻子,走远了。你没敢笑,若笑得东倒西歪那就与城市的形象不大吻合,得笑不露齿,虽然正常人都能断定你不是一个淑女,而是一个长满毛的雄性动物,但毕竟这是一座美好的城市,就算动物呆在这儿那也得有点文明素质。要知道前不久某个动物园就搞什么竞争上岗,不按规定做动作不听话的畜生们一律下岗待业。
你是在天桥上看见她的。年龄看上去,与一个四十余岁的妇人差不多。脸上有些黑斑,头发偏黄,眉眼间仍依稀得见十七八岁时的俊俏。盘着发髻,发髻上插着一根银灰色的塑料夹子。手指很长,上面全是老茧,还咧着口子。一个红扑扑的婴儿被红带子绑着捆在她肩膀上。她正帮一个女孩儿擦鞋。女孩儿头发是绿的,显然是人工绿,所以样子有点儿沮丧,嘴里骂骂咧咧不大干净。你本来也就走过去了,猛然看见她背上那个婴儿的笑容,而就在同一刻,女孩儿一脚就把她旁边的奶瓶儿给踢飞了。还好,没掉天桥下,这要砸坏什么花花草草可不大好。你走过去,捡起奶瓶,蹲下,把奶嘴儿塞入那张咿咿唔唔粉红的婴儿小嘴里。
绿发女孩儿扔下一张一元钞票与一声神经病走了。她麻利地捡起钞票,塞入左手臂的袖套里,冲你笑笑,说谢谢。你说不必,孩子真可爱。她歪过头,打量着孩子,说,那当然了。她很健谈,说话挺泼辣,呛得你脸红了好几次。她说是从附近农村来的,白天捡破烂,晚上在路灯下帮人擦鞋,一天能挣个三四十,比在家种田好多了。言谈举止间不无满足之意。你问,你老公呢?她说那个死人前年去南边打工,从脚手架上摔下来,腰椎骨就凸出来,不能再出来做重活,只好在家里歇着。她的语气中并无埋怨之色,这让你有些奇怪。你沉默下来。没过多久,一个瘸腿男人从街道那头的幽暗中,勾着头慢慢走出,一声不吭地帮她收拾东西。婴儿冲着他摇头晃脑呜呜地叫,他把手指塞入婴儿嘴里。婴儿使劲儿地吮吸,哇一声哭起来。她转过身,有些恼怒,伸手往男人手上重重一拍,说,死人头。男人憨憨地笑,弯下腰,开始拍打着女人身上的尘土。她解下背上的红带子,揉揉肩膀,将婴儿抱入怀里,松开衣襟,乳头塞入哇哇哭闹着的婴儿嘴里,起身,仰起脸,朝你摆摆手,与男人一前一后走了。那男人身上有浓重的酒味。
你发了一会愣,不晓去干什么为好。过天桥,前行约百米是一条很老的小巷,仅米余宽,从木板门房里漏出的白炽灯光劈哩叭啦打在鹅卵石铺成的路面上,溅起一片昏黄。这儿应该是城市的贫民窟,瘪着嘴,沉默地打量着你。房上生有枯草,到处都有几个大大的石灰刷成的“拆”字。一个黑黝黝的汉子捧着饭碗蹲在月牙般的门槛上大口吞咽着已经冰凉的晚饭。身后有台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屏幕上满是雪花点,人影模模糊糊。一个烟熏火燎只剩下半边脸儿的门神在他身后独目圆睁。
你穿过小巷,眼前蓦然一空,就这么刹那间城市已在身后,灯光寥落,视野所及处的夜色已浓得化不开,像有几头极为凶猛的兽正耸起脊背箕踞在夜色中。蓦然间,你想起少年时自己按乐府曲调填的一首词,心念一动,咳嗽几声,放声歌唱:吾志出青冥,狂歌上九嶷。黑岩突兀立,天高自悲啼。百川颜色齐,风云相对泣。何日拍案起,堪当雷电激。跨骥鸣飞镝,长弓挽神力。昆仑峰巅兮,圆月已危岌。我愿三十死,但为人间祈。擂鼓敲响鼙,黯然英雄气。悔未生乱世,空负好身体。偶露峥嵘意,尽在文章里。闲来不足提,静默无声息。楚山鸟语悒,空谷回音稀。枝疏暗香袭,影清拂君衣。良辰勿叹惜,醉眼苍穹低。你的声音暗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