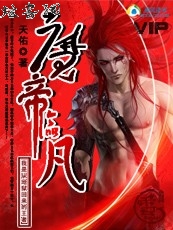网人 作者:黄孝阳-第1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记得也这么大时,大人总是说,要离陌生人远一些,他们很可能是从远方来的“拐子”,专门拿糖果或好玩的东西骗小孩子,若吃了或拿了那些玩具,就会迷迷糊糊地跟他们走,然后被卖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所以当有陌生人出现,孩子们十有八九会从地上捡石块砸过去。砸中了,哄笑一声散开,没砸中,大一点的孩子便猛地冲过去,用力往陌生人身上推一把。应该说,那时心里根本没有多少怕被拐卖的恐惧,大人的话只是为无聊的童年提供了一个恶作剧或者说一种残忍游戏的借口。毕竟看人捂头尖叫又或四脚朝天是有快感的。不过,后来还是闯祸了。一个外地公社书记的脑袋被砸破了。村里所有的孩子都被大人一起叫到晒谷场,尽管大多数孩子都扔了石块,说也不知道到底是哪块石头砸破了那个威风凛凛的脑袋,但都异口同声地将手指向平时最顽劣的那个孩子。
阳光渐渐热起来,呈颗粒状,落在地上,溅起微尘。额头已有湿湿的汗迹。身体宛若已被阳光分解,走在阳光中,微眯着眼,整个心灵似已被阳光彻底抖干净,惬意得很。村庄寂静,斜挑的屋檐、月牙状的门槛、古朴暗黄色的泥砖、满是枯叶的柴垛、衣衫褴褛的孩子、黑狗……这些东西浑似一首曲子的节拍,让人忍不住暗暗赞叹。
贫穷是干净的么?
19
你心中微微一动,想起一个朋友的话。他说,贫穷是愚昧的,是粗鲁的,很大程度上,等同于犯罪。他是江苏人,去年被派去贵州那边搞扶贫。去了三个月,回来后就骂,说,那些山民素质太低,优质杂交水稻种子被吃掉,科技书籍被撕掉擦屁股,连不远千里送去的种猪也全被宰了。那些人,当面唯唯诺诺,说什么都点头,等人一走,立刻就管不住嘴巴,只晓得吃。说他们是猪,猪们都会绝食抗议。
这话应该是真的。你见过许多愚昧的人,而且他们还为自己的愚昧沾沾自喜,并认定那是信仰、真理什么的。但自己又能好到哪儿去?小时候拿石头砸陌生人不也蠢若猪豕吗?你的喉结蠕动了下,没有反驳朋友的话。你犹豫了一会儿,小声说道,孩子不是愚昧的。请相信。穷不是原罪。愚昧也不是。十年树人,百年树木。如果我是村长,我砸锅卖钱让全村的孩子都读上书。如果我是镇长,我勒紧裤带让全镇的孩子都读上书。如果我是县长,我就在全县范围内强行推行九年制义务教育……朋友冷笑一声,打断你的话,你还是国务院总理呢。就凭着你嘴里念念叨叨的“如果”两字,你这辈子就不可能是县长、镇长乃至一村之长。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这标语煽情不?刷得到处都是,简直臭了大街小巷。事实又咋的?轰轰烈烈的教育产业化,嘿嘿。
你的话确实苍白无力。一个矫情的落魄书生对资助他盘缠参加京师会考的父老乡亲们说,等高中了状元,一定会肝脑涂地来报答这份恩情。结果,状元是中了,恩情却是用一把刀子来还了。“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一个好地方,自从出了一个朱元璋,十家倒有九家荒。”
你叹了一口气,继续往前走。很快,你走出了村庄。前面路边出现一个小亭子,已被风雨啄食得不成样子,叫“有仁亭”。你看过一个故事。说有个心善的富人在建屋时特意把屋檐盖得长长的,以方便穷人避雨,但穷人一边在他家门口避雨,一边破一大骂,在听到他家失窃后更是拍手称快。富人想不通,就去问先生。先生叫他把屋檐改回本来的模样,并在不远处盖一间亭子。结果大家又开始称赞成富人的仁慈。不过,书中并没有提到富人盖的亭子是什么名字。
亭子里很脏,满是泥土、粪便、枯草、瓦砾。一只蚯蚓在一块干裂的泥土上来回挣扎,身子发白。你往泥土上踢了一脚。泥土滚入水沟。你回过头,往来时的地方看,已见不到白塔与寺庙,只剩下那棵奇怪的树,树冠如云,墨色的一大团,天穹深蓝,似有水波在这蓝色中轻轻漾动。你有些恍惚,整个天地间好像只有着这棵树的存在,就连它脚下的山也被你有意无意地忽略掉了。这树真大。你在山上时竟然没有注意这点。也许那时的心神全为它脚下的香火、古怪的样子所吸引。也许却是因为有些东西一定得站在远方看才能咂出其中滋味。又也许是因为它足够孤独。
你这么想着。前面路口转出几个人,白衣白帽,穿着草鞋,腰扎麻绳,一身重孝。“女要俏,一身孝”。你往这几个人脸上瞅去,可惜他们皆低垂着头,不要说脸蛋,就连性别也看不出来。生,然后,死。你嗤嗤地发出轻笑,忽然伸手给了脸上一记巴掌,心里没有来由的一阵烦躁。这些日子来,自己真有些儿不知所谓,一些词语总是莫名其妙地跃出脑海,并且与眼前所见并没有多少直接联系。
记得那年,你在武汉。中午。阳光很辣,呛人。在一所区中心医院门口,你看见几张哀哀哭泣的脸。他们坐在楼房阴影里,只晓得哭,两眼红肿,头发蓬乱,声音忽高忽低,浑身散发出恶臭。人们匆匆地走来走去,没有人注意他们,尽管他们哭声很大,但就好像并不存在。
你默然。他们的眼泪也是清澈的。一个紫红色脸庞女人脸上有很多泪珠。他们哭了好几个时辰,从你来医院挂号开始,就在使劲儿地哭。人都是要死的,没钱看病所以得死,这是没法子的事。何况早死或还能少受点这阳世间的苦,没钱看病便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未尝不是件好事。医院不是慈善机构,若每天见死便救,那用不了多少天就得关门大吉。中国这么大,穷人这么多,时时刻刻分分秒秒都有看不起病的人。看多了,就习惯了,熟视无睹了,不再觉得什么了。人都是要死的,
哭吧。再哭上一会儿吧。现在流的眼泪就算是为以后自己连哭都不会时预先准备的吧。你在旁边听着,心里黯然。他们是你老家附近的,一群打工仔。他们之中的某位正在医院里死去。他们还得把他烧成灰,放入盒子里,托人带回给他的父母妻儿。只能这样委屈他。虽然他们那的风俗讲究入土为安,再穷,街坊邻居们还是会凑出一副薄杉木做的白板棺材。但在这里,他们买不起棺材,况且带副棺材回家总比带个盒子麻烦得多。
人生下来的时候就不一样,死了睡的地方那当然也不一样。你瞅着摊开四肢躺在滚烫水泥路面上低低干嚎的女人出了神。她旁边那个黑瘦汉子正急切地分辨着什么。女人不答话,就是哭,眼角都有血丝了。
你的日子也并不好过。刚打完针,口袋里只剩五百块钱,那是全部家当。离发薪日还有十天,每天伙食及必不可少的开销大约要十五元钱。你仔细默算了下,掏出三百块钱,放入黑瘦汉子手上,扭头朝外面走去。你不想看见诧异的目光,更不需要那些感谢,也不想被人当作傻瓜或白痴。你在医院门口快步走着。你是自私的,求的只是份心安,谁叫自己遇上了?至于这三百块钱他们拿去办什么,那就不关自己什么事。
天底下的穷人是一家。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你无声地笑了。你是穷人,却并不仇富,尽管你相信每一笔巨大的财富后面皆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罪恶,也相信金钱的每一个毛孔都是血腥的,但这相对于兵灾过后的满目疮荑要好一些,何况因为技术进步,这种罪恶也戴上了温情的面纱。当然,战争不可缺乏,必须存在其可能性,否则罪恶将肆无忌惮地吞噬一切。妥协比反对更困难。建设比破坏更艰苦。珍惜人类胼手砥足辛苦创造的财富,不轻易将它摔碎,更不因为羡慕别人的花瓶,便叫嚷着革命冲过去,将其占为己有。以审美的态度面对所有的人、事、物。
你又点燃一根烟。得把这些天真的想法驱赶掉。你咳嗽着,眼眶有些涩。穿孝服的人消失在路的那头。他们是穷人。所以亲人也死得悄无声息。穷人、富人。你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你曾在一个城市亲眼目睹过一个衣着艳丽的女人不停地将手中的钢蹦儿扔向路两边的乞丐。她是富人,很为这种施舍的感觉陶醉。但几分钟后你又走回此处后就听见几个乞丐正用最恶毒的语言肆意侮辱她,并做出种种下流的手势。可惜她没听见。若听见了,她还会施舍吗?估计是不会了。记得一个知名作家说她再也不向街边的乞丐施舍了。据说其中大多数是骗子。所以她要施舍也只施舍给专门的慈善机构。因为她没有一双火星金睛去分辨。
这话听起来挺对的。如果这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说的,可以理解。但作为一个阅尽世情洞悉人性的作家嘴里说出来,就令人心里犯堵。中国的慈善事业发达吗?那些善款又有多少落入真正需要它的人手里?别说善款,就算抗灾救命的钱,王八蛋们也敢往自己口袋装。而那些真正需要它的人,很多人从来就没听说过“慈善”这回事,更不知道这两个字如何一个写法。他们只是凭着本能离乡背井,在街上跪下,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跪下,然后颤抖着伸出手。
你曾亲眼见过一个小姑娘将一个乞丐被人踩翻的饭盆里散落出来的钢币一枚枚捡起,放回原处。她没施舍钱物,乞丐却一直说着谢谢。施舍本无所求,不在意施舍了什么,不在意施舍给谁,更不在意施舍的方式。人们讽笑“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若因为乞丐中的骗子停止施舍,这种行为又与其何异?骗子得到越多,身上罪孽就越重。头顶三尺自有神明。这不是自我安慰,因为你所施舍的本来就是一颗悲悯的心。只要你有,你就不妨去给,弯下腰去给;若没有,大可问心无愧地从他们身边走过,而不去寻找任何借口。
自己还真是一个现代版的阿Q。你摇摇头,苦笑起来。阳光从天上跌落,石头一样,尘埃溅起,到处都是耀眼的光芒,白茫茫的。田野上撒满横七竖八枯黄的稻杆。一些鸟儿便在这上面茫然地此起彼伏。可供填饱肚子的还会有什么?被洒落于地的稻谷多也是空瘪无物。你从口袋里摸出皱巴巴的香烟,微眯起眼,皱皱眉,里面只剩下最后两根烟,皆已略为弯曲,上面竟然还有些许汗渍。它们陪着你走了不短的一段路。
你小心翼翼地抽出一根,弄直。汗渍在灼热空气中很快就消逝不见。你再把烟叼入嘴里,又点燃了,青烟缭绕。它们就像天上正飘过的那些快活的云朵。你深深地吸了一口,惬意的感觉便随着烟雾一起涌入肺部,在里面慢慢兜个圈,一丝一缕从鼻子眼里冒出,这让你的脸看起来有些恍惚。
浅浅的水流正从脚边沟渠里缓缓流过,亭子旁边一棵苦楝树往你脚下投下一片影子。你出了亭子,在草坡上躺下,伸长四肢,懒懒洋洋地仰视天空。这些阳光应该能把心底那些已经发了霉的东西晒干净吧。一些已泛黄的草正努力地从你耳边脑后探出头。有些痒,你翻过身,从脸上匆匆滚下一只山蚂蚁,个头挺大,却不知为何要惊慌失措到处乱走,倒是那些小蚂蚁看起来从容许多。当然,这只是人眼里的从容或惊慌。在蚂蚁眼里,这种从容或许等同于游手好闲,而惊慌却等同于干劲冲天。
你嘿嘿地笑,猛力吸了口烟,烟头明亮,鲜红的一点,记得某本书上说,烟头燃烧时温度会有近千摄氏度,也不知是真是假。你把烟头凑近蚂蚁,四周的草迅速枯萎,叶沿卷起。山蚂蚁浑身一抖,似乎意识到危险,疯狂地跑。跑得掉吗?孙猴子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还不是逃不脱如来佛的五指山?蚂蚁跑得很快,眼看就要溜入草丛深处,你伸出手,两指头轻轻一摁,把它拈起。佛拈花,伽叶不语,笑意盈盈。主角、配角,一个也不能少。这不,一个莫名其妙的笑容里面就藏有无数玄机,敢情还流转千古,让大伙全为之晕头转向。你手指稍一用力,听见啪地一声。这个动作又能说明什么?蚂蚁死了,一些黑色汗液从指缝间渗出,这是它的血还是它的泪?你拍拍手,蚂蚁本来就是粉尘。你也是粉尘。只是捻死你的会是谁呢?
烟抽完了。四周还是静得像一整块玻璃。田野里没有什么在蠕动,不管它们是否在蠕动,因为你看不见,所以它们就是没有动。不是旗动,不是风动,只是心动。慧能和尚确实了不起,难怪能将衣钵发扬光大。你歪下头,吐出口唾沫。唾沫星子沉甸甸落在草尖,草尖一颤。你的视线落向远处。一头公牛晃晃悠悠从山那边走出,哞哞地叫,走下田埂,牛角一摇,尾巴扬起,身子趴入水沟,不再动弹。你闭上眼,眼帘处一片通红。这就是命运的诅咒吗?
20
你厌倦身边所有的一切。你嘲笑生活。因为你深深知道,不管你是承受、忍耐、奋斗抑或是嘲笑,结果都得被生活嘲笑。人都是被打入地狱受惩罚的西绪福斯。清晨,人们将巨石从平地推向山顶;黄昏,石头沿着山坡滚下去。这个过程周而复始,一直到死。个人的意志与努力不会带来丝毫改变。惟一的区别仅在于有些人意识到这点,而更多的人没有意识到罢了。
那天的阳光打在你脸上,让你都睁不开眼。你拉着她的手,她也紧拉着你的手。你以为幸福就在自己手里。从天艺路出去左行三百米,有一家影楼。影楼老板是你的朋友,这些年,你发了一点小财,肉嘟嘟的脸快把眼睛挤没了。她说你像熊猫盼盼。她抿嘴乐着,指甲掐入你的手腕。她喜欢掐你,你也喜欢让她掐。那时,你并不知道这些月牙状的伤疤,竟是她留给你惟一的东西,如果你知道,你一定会跪下来求她在你的每一寸皮肤上都掐下这种疤痕。
她不喜欢照相,说相片上那个人并不是她自己,她按按自己脑门,说这里的她才是她。她真是一个孩子,还没有学会自己骗自己,虽然她比你大了五六岁。她浅笑嫣然。影楼门楣上那串风铃叮叮当当响起来。玻璃橱窗内美女相片的颜色顿时黯然。整个天空忽然亮堂了。你说老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