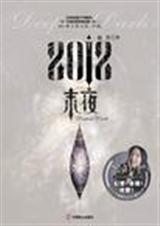014黑暗的左手 作者:[美] 厄休拉·勒奎恩-第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写信给昔日的克母恋人阿西,告诉他如何从一些贵重东西中获得收益,来供养我们的儿子们,但叫他别寄钱给我,因为蒂帕会派人监视边境的。
我不敢在信上签名字,我也不敢打电话,否则的话,受话人准会被送进监狱。
我往西穿过城市。在一个十字路口停下来,思忖:我为什么不朝东走,翻过高山,穿过平原,回到克尔姆地区呢?我,一个徒步行走的落难人儿,为什么不回到我的故园埃斯特,那座荒山上的石头房子呢?为什么不回老家呢?
路上我停下来三四次,回首顾盼,每次都好像在街上冷漠的面孔中间看见一名探子,是派来监视我离开艾尔亨朗的,想回老家的念头真愚蠢,无异于自杀。看来,过流亡生活是我命中注定的,因此我的回家之路就是死亡之路。于是我继续西行,不再回头张望了。
在三天的宽限期内,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我最远可以到达距海湾边有85英里之遥的科斯本。
船长们不敢搭我,他们都认识我,因为港口是我为国王建设的。
水陆两栖船也不让我坐。我别无选择,只有徒步前往科斯本。
我发现,叫自己卖国贼是挺难的,难得出奇。这个罪名安在另一个人身上倒很容易令人信服,可是我对自己却半信半疑。
第三天黄昏时分,我风尘仆仆地赶到科斯本,累得腰酸背痛的,因为这些年来在艾尔亨朗,我过惯了荣华富贵、养尊处优的生活,连走路的力气都消蚀掉了。
阿西早已在这座小镇的城门等候我了。
我和阿西克母恋了七年,养育了两个儿子。孩子们都是他生下来的,因此都取他的名字福雷斯·雷姆·伊尔·奥斯勃斯,并且在他的部落抚养。三年前他去了奥格雷隐士村,如今他脖子上戴着“预言家禁欲主义者”的金项链。
三年来我们彼此都没有见过面,然而,此刻我在石头拱门的暮色里一看见他的脸,昔日的恋情就立刻涌上心头,仿佛我们在昨天才分手似的,而且明白是他的忠贞不渝驱使他来分担我的厄运的。感到那根徒劳无益的纽带又将重新系住我,我很生气,因为阿西的爱情总是迫使我违背自己的意愿。
我从他身旁走过去。如果我必须绝情,我就不必掩饰,假装和善。
“埃斯文!”他边叫我边跟在后面。
我急忙走下科斯本陡峭的街道,向码头奔去。
从海上刮来一阵南风,吹得花园里的黑色树枝沙沙作响,我乘着温暖而又大风怒号的夏天黄昏暮色,像躲避杀人犯似的匆匆地离开他。可是,无奈我脚底疼痛,走不快。
他追上了我,说道:“埃斯文,我要和你同行。”
我没有吭声。
“十年前的这个月,咱俩在图瓦发过誓——”
“可是三年前你毁了誓言,离开了我,这倒是个明智的选择。”
“我从来没有毁过咱们的誓言,埃斯文。”
“是呀,本来就没有什么誓言可毁的。你我两人谁也不欠谁的情。让我走吧。”
他眼里噙着泪花,说:“你收下这个吗,埃斯文?是的,我并不欠你什么,但我爱你。”说着,他向我伸出一个小钱包。
“不要,我有钱。让我走吧,我必须一个人走。”
于是,我继续往前走,他不再跟随了。然而,我兄弟的影子却跟着我。我刚才谈起他,糟透了。我做的一切事情,都糟透了。
我赶到码头时,霉运正等待着我。
我准备搭一艘驶往奥格雷纳的船,于半夜离开卡尔海德领土,半夜是我的最后期限了,可是没有一艘奥格雷纳的船停泊在港口。码头上只有寥寥数人,正行色匆匆地回家。
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正在修船的渔民,他瞧了我一眼,赶忙转过身去,一声不吭。准是有人预先通知了他,否则他不会认出我的。蒂帕显然雇人抢先到达码头,想把我困在卡尔海德,让我的宽限期过去。
我没有料到流放令并不仅仅是个借口,目的是要把我处死。一旦六点的钟声敲响,我就会沦为蒂帕手下的瓮中之鳖,干掉我就不再是谋杀,而是就地正法了。
港口海风劲吹,天色若明若暗,我坐在一袋压舱沙上。
有些人在危险关头会急中生智,但我却没有这个本事。我的本事是具有先见之明,而一旦危险近在咫尺,我就不知所措。
从这儿到奥戈塔海岸有150英里之遥。我不会游泳。随后,我的目光从大海移开,往回瞧科斯本的街道,这时我发现自己在寻觅阿西,希望他仍在跟随我。到了这个地步,我才因羞愧而从恍恍惚惚中回过神来,能够思索了。
那位渔民还在船坞里面修船,我可以向他行贿,也可以用暴力迫使他就范,但那台破引擎不值得我冒此风险。
那么,偷船吧,可是那些渔船的引擎都锁上了。我从来没有驾驶过机动船,要想凭着凸码头上的灯光,绕过去启动引擎,将船驶出船坞,开往奥格雷纳,那简直是玩命,太鲁莽了。碰巧有一只划艇拴在两只汽艇之间的外船坞里。事不宜迟,偷。
我跑过灯光照耀下的码头,跃身跳进划艇,解开系缆,摆好划桨,朝向浪涛涌动的码头水域划去,那儿灯光滑向黑沉沉的浪涛,划出一道道炫目的光芒。
我划出码头相当远了,抬起头来,只见码头的尽头有两个人影,在远方探照海面的强烈的电光下犹如两个跳跃的树枝,我一下子瘫倒了,不是因为恐惧,而是中了远方射来的枪弹。
他们用的是一支声波枪。我不知道声波枪设置的致命点范围有多大,但我离它的射程并不远。
剧痛使得我弯着身子,好像肚子绞痛的婴孩似的。我感到呼吸困难,看来致人虚弱的声波场攫住了我的胸部。他们很快就要乘快艇来结果我了,情况紧急,我不能再蜷伏在桨上喘粗气了。于是我挥动虚弱的双臂划呀划,双手已经麻木了,只好睁大眼睛,看着手握紧桨。就这样,我划进了惊涛骇浪,划进了黑茫茫的海湾。每划一次,我的手臂就更麻木了。我的心狂跳不已,我的肺忘记了呼吸。我竭力划桨,但手臂却不听使唤。我竭力把桨拖进船里,但拖不动。
随后,一艘巡逻艇的探照灯光犹如雪花落在煤烟上,在黑夜里发现了我,这时候我的眼睛甚至无法从那耀眼的光束移开。
他们掰开我那握紧桨的手,把我从划艇拖上去,摊在巡逻艇甲板上,就像一条剖了腹的裸首隆头鱼。
我感觉到他们低头望着我,但不大听得懂他们说的是什么,只听清楚其中一人的话,听他的口气是船长。
“还不到第六个小时呢。”接着他又回答另一人,“这与我有什么关系?既然是国王流放了他,我就执行国王的命令,不执行别人的。”
于是,尽管蒂帕的人从岸上通过无线电台三令五申,大副害怕遭到报复而一再反对,科斯本巡逻艇艇长还是不予理睬,把我运过查里索尼海湾,安全到达奥格雷纳的谢尔特港口。
艇长救我是坚持信誉原则,反对蒂帕的人杀害一个手无寸铁的人呢,还是出于好心?我不知道,也无从知道。
透过晨雾,奥格雷纳海岸隐约可见,灰蒙蒙一片。这时候我站起来,拖着双腿,离开船向谢尔特市濒临海边的街道走去,可是走不多远,又倒在地上,昏迷过去了。
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医院叫做森利斯克第24社区谢尔特市第四沿海区公共医院。
我肯定无疑,因为床头上、床边灯架上、床头柜上的金属杯上、床头柜上、护士的白大褂上、床单上以及我穿的睡衣上面,到处都以奥格雷纳的书写体刻着或锈着这个名字。
一位医生走过来,问我:“你为什么能抵抗迷幻剂呢?”
“我并没有受到迷幻作用,”我回答,“我是受到了声波场的损害。”
“可是你的症状表明你抵抗了迷幻剂的张弛阶段。”
他是一位老医生,盛气凌人,终于迫使我承认,我在划船时可能服用过抗迷幻剂药,以防止瘫痪,只是当时我自己并不清楚;到了今天清晨,我处于假死阶段,本来必须静躺不动,但却爬起来行走,结果险些把命送了。
他对我的回答感到完全满意后,便告诉我一二天后就可以出院了,接着他去查下一个病床了。在他身后出现了督察员。
在奥格雷纳,每一个人的身后都会出现督察员。
“叫什么名字?”
我没有问他的姓名。我必须入乡随俗,学会像奥格雷纳人一样,在没有保护的环境里生活;学会克制;学会不要无谓地冒犯人。不过我没有告诉他我的本名,这与奥格雷纳的任何人都无关。
“瑟尔瑞姆·哈尔斯吗?这可不是奥格雷纳人的名字。从哪里来的?”
“卡尔海德。”
“这可不是奥格雷纳的一个社区。入境证和身份证呢?”
“我的证件在哪儿?”
先前我在谢尔特市街上昏迷了好一会,方有人把我送到医院来,所以我的证件、随身物品、大衣、鞋子以及现金,全丢失了。我一听,憋了满肚子的气,顿时发泄出来,哈哈大笑起来,其实在我的内心深处并不生气。我的笑声激怒了督察员。
“你明白你是一个穷汉、一个非法入境的外国佬吗?你打算怎么回到卡尔海德呢?”
“我是从卡尔海德被放逐出来的。”
医生刚才一听见我的名字就从旁边病床转过身来。这时候他把督察员拉在一旁,交头接耳谈了一阵。
督察员脸色变得阴晦,好像酸啤酒。他回到我面前,慢腾腾地说:“那么,我想你要向我宣布,你打算申请在奥格雷纳的社区永久性居住权,作为社区或城市的一员找一份工作,是吧?”
我回答:“是的。”
五天后,我获得了永久性居住权,登记为米西洛瑞镇的一个居民(根据我的申请),并且领到到该镇旅行的临时身份证。
多亏那位老医生让我呆在医院里,否则这五天我准会挨饿的。他喜欢卡尔海德的一位首相住在他的医院里,而且这位首相还感恩戴德呢。
我在一支从西尔特开来的运输鲜鱼的车队里当一名水陆两栖船的装卸工,打工来到米西洛瑞。旅程短暂,充满腥味,终点在南米西洛瑞的大集市,我很快就在那儿的冷冻库找到了活干。夏天那些地方总是有活干,譬如装卸包装储藏运输死鱼。
我主要处理鱼,同我那位冷藏库的伙计一块住在一座岛上,当地人称之为“鱼岛”,岛上弥漫着鱼腥味。但我喜欢这工作,因为我可以成天呆在冷藏库里。米西洛瑞夏天热得像火炉。在奥格瑞月有十天不分昼夜气候不低于华氏60度,有一天竟高达88度。干完一天活后,我只好离开冰冷的、带鱼腥味的庇护所走进火炉,走几英里路,来到昆德里河堤,那儿有树木遮荫,还可以眺望大河,尽管不能下水游泳。我总要在河堤上徜徉到很晚,最后才穿过酷热、沉闷的夜晚,回到鱼岛。在米西洛瑞我住的那一隅,人们砸坏街灯,好在黑暗里干自己的事。可是督察员的小车老是在搜寻,车灯照亮那些漆黑的街道,夺走穷人的隐私,也夺走了他们的黑夜。
作为与卡尔海德冷战的一大举措,卡斯月26实施了新的“外国人登记法”。根据新法律,我的注册登记失效,从而把饭碗丢了。我花了半个月在一个又一个督察员的接待室里坐冷板凳,多亏我工作时的伙计们借钱给我花,偷鱼给我充饥,我才不至于饿着肚子去重新登记。我喜欢那些侠义心肠的大老粗,但他们却生活在陷阱里,永无出头之日,所以我不得不在我不大喜欢的人中间工作。于是我打了我拖延了三个月之久的电话。
第二天,我正在鱼岛庭院洗衣房里洗衬衫,一起还有几个伙计,大伙有的赤条条地光着身子,有的半裸着身子,房子里蒸气腾腾,污垢臭味鱼腥味熏人,水声哗哗。
这时候,我听见有人叫我的本名,一看,是叶基总督,他看上去就和数月前在艾尔亨朗王宫礼仪大厅欢迎列岛大使招待会上时毫无二致。
“快离开这儿吧,埃斯文,”他俨然以米西洛瑞富翁的口吻说,鼻音浓厚,声音又高又大,“哟,把这件烂衬衫扔掉吧。”
“我只有这一件。”
“那就快起来,咱们走吧。这儿太热了。”
在场的人又冷漠又好奇地凝视着他,他们知道他是个富翁,却对他还是个总督一无所知。
我还了债,付了帐,身上揣着证件,没有穿衬衫就离开了位于大集市的这座小岛,跟着叶基回到高官显贵的府邸里。
我当上了叶基的“秘书”,在奥格雷纳的花名册上重新登记为一名随从,而不是一个符号。
光有姓名不行,还得贴上标签,那儿的人是先分类别,后见具体东西的。不过这种标签对我恰如其分,我是个寄食者,很快就开始诅咒驱使我到这里寄人篱下的目的,因为整整一个月过去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事情比我在列岛时有丝毫进展,目的的实现依然遥遥无期。
眼看夏季将尽,最后一个雨夜叶基才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去。
一到那里,我遇上他正在和埃塞克务区总督奥布梭谈话。我认识总督,当年他曾率领奥格雷纳贸易代表团访问过艾尔亨朗。他身材矮小,胸部凹陷,一张扁平脸上长着一双三角形小眼睛,同线条纤细,瘦骨嶙峋的叶基相映成趣。他俩看上去一个像花花公子,一个像老古董,但却是大有来头的。他们俩都属于统治奥格雷纳的32人集团,而且,还不止这一点。
奥布梭叹了口气,对我说:“埃斯文,告诉我吧,你在萨斯洛斯的所作所为目的何在?因为我认为如果有谁办事出差错的话,那么这个人只能是你了。”
“我的恐惧压到了谨慎,总督。”
“究竟恐惧什么?你怕什么,埃斯文?”
“害怕目前发生的一切。在西洛斯追求名声的斗争在继续,卡尔海德受到了屈辱,屈辱导致了愤怒,卡尔海德政府正在利用这种愤怒情绪。”
“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