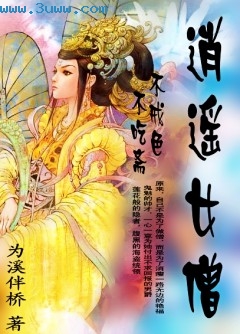新聊斋-第5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哼,什么青苗大会,没听说过一年收成要靠女人相貌好坏来定的……反正此地也没人见过我……清月,便是你吧!”
这样,卑微的婢女清月便改妆换容,作为仪容高贵的臬台夫人,在青苗会上接受了百姓的参贺。不过说也怪,尽管其实是假冒的西贝货,这一年全省的收成却是好得出奇,直喜得百姓们都合不拢嘴来,本地乡绅还特地到臬台府送了一块“洪福齐天”的篇额以示谢意。
臬台夫人倒是毫不客气地把这份功劳揽到了自己身上:“容貌虽然是清月的,不过总还是沾了我的福气,你说是不是啊?”
“是是是!”在一旁连连点头的,是臬台大人,因为妻子出身名门,自己的仕途很得她娘家助力,所以臬台大人向来对这位夫人千依百顺,没有半点违拗。不过趁着妻子转身,臬台大人还是忍不住将目光扫向了侍立在旁的清月,从心底微微地叹了一口气——如果清月真是臬台夫人,那该有多好啊!
的确,自从那次青苗大会之后,臬台大人一下子注意到了这个平时不起眼的婢女:美貌、温柔、精通文墨,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都是十分理想的伴侣人选,由不得令他怦然心动,然而事实摆在眼前:自己不但已经娶妻,而且在成亲之前,为了攀上这门对仕途大有裨益的婚事,还曾主动提出了绝不另纳侍妾的保证……真是可惜……
当清月第三次现身青苗大会的时候,真正的臬台夫人病倒了,而且这一病再也没有痊愈,短短几个月光景就离开了人世。中年丧偶,臬台大人倒也着实伤心了一阵,等忙完丧事,才发现眼看着又快到一年一度的青苗大会了。因为深信这几年省里的风调雨顺完全归功于“臬台夫人”的出色容貌,那些宦室乡绅都十分热心地争着要替臬台大人作媒,务求让他再续娶上一位美貌妻子,以保四方平安。
尽管臬台大人心中早已属意清月,但考虑到对方出身低微,对于自己的仕途毫无助力之处,最后还是迎娶了一位告老还乡的京官之女,当然,对于清月他也有自认为两全其美的打算——在成婚之前,先纳她为妾!
然而出乎意料之外,当得到授意的管家婆喜孜孜前去传口信时,清月却断然回绝了臬台大人的美意,让众人错愕不已。
“小妮子,大约想我娶她做正室吧!”得到回报的臬台大人倒是并未动怒,微微一晒后便就此作罢:“要论人材,确属上上之选,可惜出身……嘿……”
不久新夫人张氏就过了门,当她听说前任臬台夫人居然让一个丫鬟代替出席青苗会,不由大笑起来:“哪能让一个下人代自己出头,真正乱了体统。”很快又有人多嘴说出了臬台大人曾向清月提婚的旧事,张氏不由格外对她上起心来。
事有凑巧,这日臬台的旧日同窗金衡调任观察使路过此地,闲谈间偶然提及自己妻子早逝中馈乏人,臬台夫人便有意无意地将清月指给了对方看,本来只不过是准备将她当作一份礼物转赠对方,以去除这个心头之刺,没想到良缘天定,那位金观察却对清月一见钟情,甚至提出愿意明媒正娶将其聘为正室夫人。清月见对方不过三十出头,面貌清俊,谈吐温雅,也就自然首肯。两个人当下便在臬台府成了婚。在金衡清月这方是佳偶天成,臬台夫人那方则是去了心病,三方皆大欢喜,唯有那位臬台大人,在金衡夫妻辞行之后,犹在暗中怅惋良久,不能自已。
转眼正月廿四已至,新任的臬台夫人盛妆打扮,兴兴头头地赶赴青苗大会展露芳姿,然而尽管她对自己的容貌有着无比的自信,这一年却是全省大旱,颗粒无收。
寻芳记
说起来也许没人能相信,事情的起由,其实只是因为一只手。
那是辆没有记识的马车,车夫似乎有些盹着了,斜倚在车辕侧旁,一顶草帽几乎落到了脸上,任由驾车的马匹停停走走胡乱行进,车中的乘客倒也好耐心,始终没有出声叫醒车夫——幸好道路开阔,小小一辆单骑马车不算太过妨碍,才没有引起其它行路者的不满。这样行三退二,马车慢慢地停滞在了薛记银楼的店铺前面。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老板薛子矜看到了那只手。
五根洁白修长的手指,轻轻搭在车窗绊上,精心修葺过的指甲圆润光洁,如同淡淡的粉色花苞,更衬显出了肌肤的柔腻丰腴——与时下那些动不动就涂擦着满满艳丽丹蔻的手相比,这只纤纤素手显然更能吸引有心人的目光。
从第一眼看到这只手起,薛子矜就再也不能把目光移开。当然,作为一名猎艳老手,他也立刻便推断出,这只玉手的主人,必然是个出色的美女。可惜车厢内光线黯淡,隔着低垂的帘幕,只能隐约看到一个婀娜的身影,然而愈是这样,薛子矜愈是心痒难搔,眼看着马车慢慢前行,薛子矜忙不迭转身向一旁的伙计李平示意。
李平在柜上已久,自然对老板的眼色心领神会,立刻扯开了嗓子:“时令新款,钗钿环镯,十文一个,十文一个……”
这种几乎等同于白送的价格果然马上就吸引了车中人,帘幕被掀开了,不过令薛子矜失望的是,探出头来的却是一个青衣小婢,而那只玉手只在车内遥遥指点,稍作挑选,便捡中了一只镂金镯,由婢女点出十文钱,接过了镯子。
虽然对于家大业大的薛子矜来说,小小一只镯子无关痛痒,但无法见到车中人的真面,可着实令他气馁,正觉无计可施,那个青衣婢女却又探出头来,笑嘻嘻地向他招了招手。薛子矜心中一动,忙起身离柜,大踏步地走到了马车旁。
“多谢先生盛情……”车厢中响起的,是柔媚宛转的女声:“此处人多不便相邀……我住在金光门桂花巷第三家,门口有一对石狮子的便是,先生如果得空,尽可今夜来访。”
老半天薛子矜才回过神来,没想到仅用一只金镯便获得佳人青睐,亲口许订下密会幽期,这可远远胜过了他的初衷!相较于平日里偷香窃玉,总免不了要兜兜转转试探上三五个回合才能得手,这一次真是格外来得爽利。看着远去的马车,薛子矜不由喜形于色,几乎就在大街上手舞足蹈起来。
佳人有约,自然不可太过马虎,薛子矜也无心再打理生意,匆匆交待了李平几句,便往家中赶去。到家后先舒舒服服地泡了个澡,又换过一套时款新衣,修饰齐整,薛子矜便安安稳稳地静候太阳落山。家中的仆佣熟识主人脾性,早已见怪不怪,都静静地退开不去打挠。
“嘿嘿,这就是不娶亲的好了……”靠在躺椅上闭起双眼养着神,一丝得意慢慢浮上了心头——自从三十岁那年妻子病逝,薛子矜就没有再娶,在他看来,老话说得再好也没有,所谓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偷,家中妻子纵然是天仙下凡,日久相对也觉生厌,哪里比得上外间的姹紫嫣红野趣多多?因此平日里除了花街柳巷时有涉足之外,薛子矜最喜打探城内哪家有文君新寡,哪户有怨妇怀春,仗着自己相貌英俊,又肯撒漫使钱,倒也结下了不少露水姻缘。虽然如今已然年过四旬,不过薛子矜自己却丝毫不觉老之将至,仍是整日价修饰得油头粉面,极尽风流之能事。
象今晚这样的幽会,无非也就是在他的寻芳史中再添多一页罢了,想来车中的那个女子,多半便是名单身独居的孀妇,芳心寂寞,亟需待人打救……
桂花巷离薛家不算太远,看看已经入夜,薛子矜也没带仆从,一个人自行踱了过去。因为是初次上门,薛子矜不敢太过造次,先站在巷口树荫里观察了片刻,只见巷内第三户人家的门口,果然有一对威风凛凛的石狮子,尽管时近初更,两扇红漆大门却没有合拢,半敞半闭——看来正是有所待的样子!
当下薛子矜再无迟疑,踏上台阶刚要推门,白天见过的那个青衣小婢忽然从石狮子背后转了出来,不等薛子矜开口,就竖起中指轻轻“嘘”了一声,随即转身前行,薛子矜本是个中老手,便不作声地跟着一起进了门。
感觉上这是一间极大的宅院,跟着婢女在微寒的春夜里静默前行,回廊曲折,星光明灭,薛子矜忽然觉得自己仿佛又回到了十七八岁的少年时代,很久都没有过这样急切想得到一样东西的心情了呢,如果告诉别人,竟然只是因为一只美丽的手,也许谁也不会相信吧……直到被延入一间小小的厢房,薛子矜才收回了辽远的暇思。
“我家娘子正在梳妆,请先生稍待一会儿。”婢女交待过后便向内室行去,将薛子矜一个人留在了外间。然而枯候半晌,却始终也没有出现美人环佩叮咚香风四溢出迎的场景,薛子矜久坐无聊,又觉得脚下的青砖地寒意渐生,不由立起身子,将手凑到了蜡烛上取暖。
惨白澹青的烛火跳了一下,几乎烧着了薛子矜的手指,然而在感觉上却并没有烧灼的热度,反而有一缕刺骨的寒意渗入了肌肤。
到底是有些阅历的中年人了,薛子矜立刻就觉出了其中的不妥,下意识地打量四周,这才发现整间屋子异常狭小,四壁都围着青布幔帐,而他进来时的那扇门,已经不见了。
此刻的薛子矜再也没了寻花问柳的旖旎心境,在确定欲出无门,又不甘心坐以待毙的情形之下,唯一的去向便只有通往内室的路了。一边战战兢兢地向前迈步,一边在心里狂念着“观音大士”、“皇天菩萨”等所有能想到的神佛名号,薛子矜的冷汗涔涔而下,几乎湿透了外衣。
也许是听到了薛子矜的脚步声,本来暗黑的内室忽然亮了起来,妆台旁,一个女子慢慢转过身来。
那的确是一张十分美丽的脸,柳叶眉、琼瑶鼻,丰满的樱唇——几乎挑剔不出任何缺点。然而美人当前,薛子矜却半点儿也没有欢喜之意,因为尽管女子的五官秀美异常,但整张脸却丝毫没有生气可言,就连肌肤也已经呈现出了一种可怕的靛青色,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能很快地得出结论:这是一个死人,或者说,是一具僵尸。
见薛子矜哆哆嗦嗦地挤在门口欲进不进,女子裂嘴一笑,向他伸出了手:“本来是舍不得这世间繁华,所以才最后在城内走一遭,没想到竟然还能得到先生的垂爱……这下可好了,再也不必怕泉下寂寞……春宵一刻值千金(薛子矜:这、这不是我常用的台词吗?),您可千万不要辜负了呀……”
绝望地看着那只曾令自己心神震荡的美丽玉手伸到面前,薛子矜来不及转任何念头,便已“咕咚”一声昏厥在地,幸运地避开了被骇吓至死的结局。
一直到两天后,薛子矜才被人救了出来,不过还没等他道谢,对方已经一拥而上拳脚相加,差点重新将他打回了鬼门关。
“妈的,竟然连死人也不放过……”
“要不是伙计发现棺材重得不对劲打开来看,大概你是要和死人双宿双飞到地下了罢?”
“我家清白门风,全被你这个畜牲给毁了……”
在无数的怒责声中,薛子矜总算搞清了大概事实:自己是从正要出殡的棺材里被拖出来的,而棺内的死者恰恰是个年轻的女子,难怪这群人气得什么似的,看来如果不做出合理的解释,恐怕自己是很难完整地走出这个地方了。
但是要怎么说才能令人信服呢?虽然透过人群缝隙,薛子矜清楚地看到,棺材内素白绫下露出的一截手腕上带着的,正是那只以十文钱卖出去的镂金镯,甚至还认出了在灵堂一侧大堆的纸人纸马中,有一个婢女的脸容十分熟悉,但是,难道真能告诉他们,主动与自己相约前来幽会的,正是棺材中的这个女死鬼吗?何况薛子矜也不认为自己还有勇气,再去掀开棺材中死人脸上的那幅白绫。眼 看着几个年青人一边痛挥老拳一边连声詈骂:“敢败坏我老婆/姐姐/妹妹/弟媳的名节,打死你打死你……”,薛子矜除了双手抱头连声求饶之外,实在也说不出别的话来了。
最后还是有老成的人怕闹出命案,做好做歹地拉开死者家属,薛子矜又央人去挽了自己相熟的亲友来做保,答应重金陪罪,才带着满身青紫回了家。
这件事过后不到一个月,薛子矜便重新娶了房妻子,转过年妻子又替他生下了一对孪生子。现在的薛子矜不仅身形日渐发福,衣着也不再象以前那样精洁讲究,因为一对儿子实在顽皮的缘故,薛子矜往往带着满襟污渍便出门会客,奇怪的是,这种生活却并没有象他预想中那般沉闷无趣,有时候薛子矜甚至还觉得颇有滋味——也许确是该多过过这样平淡安稳的日子了罢?人到中年,香艳刺激的寻芳生涯,真的有点不太适合了。
异宝
“阿采,快去打壶酒,再到刘屠户家切两斤猪头肉,要是有下水,也捎上一副……”还没有跨进院门,徐四便已提高嗓子嚷了起来。
“啐!”回答他的,是妻子阿采的一记白眼,家里大堆的活计从早忙到晚不说,还要照看阿大阿二两个淘气包,简直没有片刻的停歇,阿采自然不会有什么好气性:“油蒙心啦?不年不节的吃什么酒肉,再说哪来的闲钱!”
对于妻子的唠叨,徐四并不着恼,而是笑嘻嘻地从腰间取下褡裢,故意慢条斯理地解了半天,才露出里面光华灿灿的一锭银子来:“你看,这是什么?”
有道是:有钱好使鬼推磨,前一刻还满脸不痛快的阿采脸上立刻艳阳高照,嗔笑着抢过银锭:“死鬼,这么多钱……这是哪弄来的呀?你不会是做了什么坏事罢……”
“嗐,瞎说什么呀!”徐四取回银锭用褡裢布仔细包好,才凑到阿采耳边,轻声道出了缘由。
原来前两天徐四在耕地的时候曾无意中掘出一把铁剑来,当时看这把剑虽然锈迹斑斑,不过入手倒是甚为沉重,便想试着将它当作旧铁去换卖些日常用品回来,没想到正在集市转悠,却有一个西域胡贾拉住了他,说是有意收售这把铁剑。
“那、那把破剑?能卖这么多银子?”阿采的下巴差点跌落在地:“是不是遇上傻子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