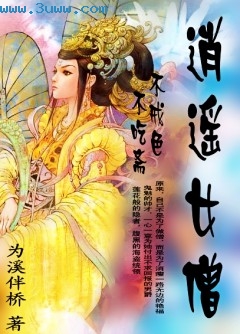新聊斋-第3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看呆眼的村人们老半天才回过神来,定睛细瞧,那个念出神奇的击退毛怪符咒的人,是村上昨天才请来教读私塾的先生朱秀才,真没想到这文弱书生居然有这样的能耐,仅凭几个字就驱走了毛怪。
感激、惊奇、庆幸……当然除此之外大家还有止不住的好奇,围住了朱秀才纷纷询问——方才他念出的倒底是什么样的咒语,竟有如此大的神威?
“呵呵,不是什么神咒。”朱秀才笑了起来:“我早就听说这一带有毛怪出没,想不到是真的。幸好我来以前查阅过一些典籍,书上说这些毛怪都是秦朝时的孑遗,因为躲避修筑长城的苦役而逃入山中,后来岁久不死渐渐变为此种怪物……他们最怕的就是被捉住去修建长城,所以只要听到‘筑长城’三字,就吓得屁滚尿流逃之唯恐不及了……看起来秦朝时的法度一定异常森严,才会历经千年犹有余威……”
原来如此——村人们恍然大悟,看来这读过书的秀才就是不一样啊,困挠村庄许久的麻烦,轻而易举地就被人家解决掉了!所以当朱秀才引经据典滔滔不绝的时候,那些做父母的也不失时机地拉住自己的儿女,给他们做起了“知识就是力量”的现场教育。据说这个小山村日后很是出了几位学问人,大约都是经此一役之后意识到了知识的重要性吧……
冷灶
“大人,前面就是淮县了。”
“噢——”策住马匹,张之华翻身下马,风尘仆仆地赶了一天路,饶是他正当壮年,也难免显露出疲惫的神色来。何况只要想到自己目下的处境,便由不得张之华双眉深锁胸中抑郁。
他本是江西巡抚,因为生性梗直,不知无意中开罪了哪路神仙,几道参奏他“结党营私,舞弊弄权”的本章便悄无声息地递到了朝堂上,皇帝虽然不甚深信,但还是很快就下旨将他拿问进京——尽管因为圣旨未曾革去张之华的官职,所以无须象普通犯人一般套板上枷,勉强保住了那份尊贵体面,但官场世态最是炎凉分明,两年前张之华离京上任的时候,一路行来,各省各府的官员不知有多巴结趋奉。如今路还是这条路,人也还是那些人,但张之华却已经从香饽饽变成了瘟神。仿佛是怕沾上他的晦气一般,行经之处再也无人搭理。即便是张之华自己的门生亲信,也往往避而不见。能派人来传话说 “因病不能亲见”、象征性敷衍一下的,就已经算是给了天大的面子。
想来在这淮县,等待着自己的,必定又是驿站的冷茶冷饭吧?张之华无声地苦笑了一下,牵马走进了城门。
不过世事可真是难以预测,刚踏进淮县城门,就有一个长随满面堆欢地迎了上来,持着淮宁令华雍的手本,恭恭敬敬地将张之华迎入了某处公馆。馆内张灯结彩,不仅牲牢夫役置办齐全,更有一桌精美的酒菜齐崭崭地摆在了正厅,旁边尚有丝竹雅乐轻奏,这可真让张之华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华雍即非自己属员,又素未谋面,如何会有这样的重礼相待?
对于张之华的疑惑,这个自称名叫华寿的长随并不曾解释,只是殷勤布菜,饭后又服侍着他到内室歇息,床帐被衾自然也极为精美考究,仔细嗅去,柔软的丝绸上居然还有细微的熏香余芳……一路尝尽冷落滋味的张之华这份感动可想而知,第二天启程之前特地手书一封托华寿转交,信中不但向华雍称谢再三,同时表示日后定会寻机相报对方的这份盛情。
呼——看着张之华等人远去的身影,华寿抹抹头上的冷汗,长出了一口气。他确是准宁令华雍的亲信长随,不过昨晚对于张之华的盛情款待可不是出自上官本意。事实上几天前华雍将他指派来这淮县边界,本是为了迎接据说即将从此处过境的钦差大人,所以华寿极尽奉承之能事,将一座小公馆打点得异常舒适雅致。谁知刚刚料理齐全,驿站却得报——钦差大人奉旨改行他处,不再过来。
这下可坏菜了,接待钦差用的乃是官银例份,算一算为了替钦差大人接风洗尘,备置公馆,花费不下百金,如今钦差大人改道别行,这笔花销让华寿如何落帐?正急得团团转,驿卒无意间说起江西巡抚张之华因为被罪拿问进京,正从此处经过,华寿灵机一动,才起了这个移花接木的主意。所以说穿了,张之华其实只是在阴差阳错之下,才得以享受了一番本该属于钦差大人的待遇罢了。
对于华寿的自作主张,华雍起初也颇有些不快,不过想想除此之外的确别无销帐之法,稍稍责备了华寿几句,这件事也便放过一边。
意外的是,两年之后张之华重获圣眷,被启用为山西巡抚,而华雍恰恰调职到他的治下,到行辕禀谒那天,张之华一见华雍的名贴,简直如获至宝,不但从中门亲自出迎,而且还硬是摁着他落了上座,起初华雍不明就里,吓得拼命推辞,后来才渐渐听出事情端倪,原来自己今日的这一番荣遇,竟然是两年前华寿无心插柳之举种下的因果。
此后华雍在张之华的治下不断升迁,由通判而同知再知府,仕途一番风顺。当然他也没有忘了华寿之恩,先是陆续打赏了不少金银,又替他选了门好亲事,最后索性资助华寿开了两家商铺,做起了小老板。
——世间趋炎附势,本是人之常情不足为怪,而华雍之贵与华寿之富却偏偏从烧冷灶而来,倒也甚为出奇。当然古人也有云:不可有意,有意即差,大概正因为华雍华寿当日善待张之华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无意之举,才收到了如此不可思议的效果吧?
湖变
几滴鲜血溅入了碧波之中,转瞬之间就在水里消散得无影无踪。
“啊呀!怎么又出鼻血了!”看到丈夫满面痛苦之色,妻子柳氏心疼地抽出手巾,递了过去:“是不是天时太燥,内火虚旺啊……看来得叫厨子多煮几味清淡润肺的小菜,给你去去火……唉,在北方呆惯了,现在调到熙州任职,恐怕难免会水土不服呢……等会上了岸,到官衙安置好之后,可要叫医生仔细瞧瞧……”
“嗯……嗯……”因为正仰头用手巾捂住鼻子,所以李辰典并不搭话,不过听着妻子一边唠唠叨叨,一边又小步跑到后舱催促下人替自己准备净面用的热水,那份多年夫妻间才有的关爱与体贴让他心里十分受用,甚至连鼻子里的刺痛仿佛也减轻了许多。
不过,头似乎有些晕……是阳光太刺眼了吗?下意识地闭上眼,李辰典仍然觉得头晕脑眩,阵阵酥麻的感觉袭遍全身,手……脚……象是被什么缚住了一般,无法动弹。
一条柔软滑腻的东西慢慢卷住李辰典,悄无声息地将他拖入了湖中。
正午的阳光照得船梢几个舵工昏昏欲睡,谁也没有察觉到船身轻微地侧了一下,湖水散开的涟漪在日光下变幻了几道金光,便自消失不见,几只鹭鸟从水面低低掠过,间或从轻波里啄出一条鱼来。
依然是平安静好的夏日午后,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是这样啊——”紫衣的道士点点头,若有所思。
也许是太过全神贯注倾听的缘故,道士丝毫也没有发现来往的行人都在用怪异的眼神看着他——大热的天,穿着厚厚的道服不说,还独自站在临湖的岩礁上,低着头不住“唔唔”连声,现在又对住湖面喃喃自语:“你放心好了,这件事包在我身上!”
难道是来太湖寻死的疯子?虽然近日因为连续大旱,太湖干得将近见底,不过要淹死个把人还是绰绰有余的。几个热心肠的甚至已经做好了一俟这道士跳入水中,便立刻下去救人的准备。
幸好这道士对着湖面指手划脚一番后倒是转身走下了岩礁。不过还没等人们松口气,道士却作出了更古怪的动作:只见他俯身托起了一块巨石,在上面指指戳戳不知画了些什么,接着跃上石头一声大喝:“疾!”——巨石随之腾空而起,载着那道士向天际直飞而去,剩下目瞪口呆的众人站在原地,老半天才回过神来。
“快追上去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有反应快的人见那块巨石尚在目力可及的范围,好奇心大盛,呼喝着追了上去。
于是太湖边出现了奇怪的一幕:大群的人抬头看着天边拔足狂奔,而一路行来,被他们的举动所吸引、加入进来的闲人也越来越多,当飞天巨石来到城中的时候,后面尾随的大队人马差不多已经有近千人之多了。
最后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石头落在了熙州刺史的官厅内。
此时正是早晨开衙的时候,刺史大人刚刚坐上正堂,没想到巨变突起,总算衙役们本来就分站在两边,有足够的空间躲避,倒是个个安然无恙。可刺史大人就没有这份幸运了,因为身上的官服长袍大袖牵手缚脚,又前有公案后有座椅进退无路,在一片惊叫声中,顿时被硬生生地压在了石头底下。
吓傻了眼的衙役们片刻之后才回过神来,纷纷扑到巨石底下察看大人的安危(衙役T_T:肯定压死了,可怜的大人啊,上任才不到一百天),随即这些人就发出了比刚才石头落下时更为惊天动地的喊声。
——虽然绝大部分的躯体被石头压住了,但露出来的一小截手脚趾端,却分明都长有尖尖的黑色指爪,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也不象是人类的手脚。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刺史大人被压得连手脚也变形变色了不成?
“哈哈,压中了……看你往哪儿逃!”紫衣的道士大笑着从石头上跳了下来(衙役:刚才吓昏了,居然没发现石头上还有人),低声念了几句符咒,巨石便轻轻巧巧地滚到了一边,露出已经压到扁得不能再扁的刺史大人……咦,好象有点不对劲呢……经过再三辩认,大家终于确定在官服里裹着的确实不是人类的肉身,而是一只异常肥壮的龟/鼍/鳖?? (因为压成了一大坨,体貌特征实在难以确认)原本坚硬的外壳已经被压得四分五裂,不过它并没有断气,乌溜溜的小眼睛此刻正可怜巴巴地看着道士,嘴吻一张一合,仿佛在乞求什么。
“啊——相公,你怎么了——”惊叫着扑过来的,是刺史夫人柳氏,刚才得到衙门里发生剧变的消息,急得三两步就从内室赶了过来,正好赶上巨石被掀开的一刻。本来以为会见到丈夫血肉模糊尸身的柳氏看到石下的异变也愣在了当场:“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相公……”
“夫人莫急,你的相公在这里呢!”道士走到柳氏身边,轻轻抖了抖袍袖,只见一道光华闪过,一个人影出现在了大堂上。
“相……相公……”站在那里的,正是柳氏的丈夫李辰典,惊喜交集的柳氏扑上去搂住丈夫呜呜咽咽地哭了几声,忽然象是想起了什么,又急忙忙地倒退了几步,上下打量起来——虽然面貌身形的确是自己的丈夫李辰典不错,可对方不仅神情委顿,满面胡须,与平日里意气风发的丈夫迥然不同,而且身上那件衣服也不是今天早晨自己亲手替丈夫穿上的官袍——这倒底是不是丈夫?刚才石头下压着的又是什么?究竟哪个才是真的柳辰典呢……
旁观的衙役们也握紧了手中的家伙——今天是什么日子呀,先是刺史大人莫名其妙地变成了甲鱼,这边又跑来一个和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还有这个来路不明的道士,现在也搞不清对方是人是妖,是鬼是怪了,看样子还是先把他们一锅端好了。
总算道士及时地掏出一面朝廷钦赐的金牌,表明了自己御封天师的身份,才平息了这场一触即发的乱斗,随即这位叶姓法师便道出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那天李辰典在船舷边闲坐之际,因为一时不慎,无意中流了几滴鼻血到太湖里,恰恰湖中正有一只修炼经年的江鼍,得到这几滴人血后顿时成了气候,复生出叶辰典的形貌,冒名顶替做了熙州刺史。而真正的叶辰典则被它拖入水中,禁制在湖底无法逃脱。
“如果不是我正好有事路过太湖,又逢上天旱太湖水干见底,一时之间我也未必能发现此事呢!”叶道人走到江鼍面前,毫不留情地挥动拂尘,将它击为为尘齑。
妖怪得到了应有的下场,叶辰典夫妻团娶,法师飘然远行……一时之间这桩奇事在太湖流域传得沸沸扬扬,听的人紧张莫名追问连连,说的人则不免添油加醋越传越玄,虽然后来因为年代久远,故事真相渐渐湮灭在岁月的长河里,不过至今太湖一带的渔民们们还会互相告诫,如果在船上意外受伤,可无论如何不能有一滴血落到湖水之中,谁知道呢,或许还有什么甲鱼妖怪正在水波下,伸长脖子等着这样的机会呢!
狐媒
一大清早,激烈的争吵声就从周府的内宅里传了出来,进进出出的下人们都吓得缩手缩脚,生怕遭到池鱼之殃。当然心底的好奇还是免不了的——向来畏妻如畏虎的老爷今天是吃错了什么药,竟敢对着夫人大吼大叫起来?
“都是你教出来的好女儿!真是慈母多败儿!”对着妻子孙氏发作了一通,周守诚气呼呼地坐倒在了椅子上。
“你胡说什么呀!”对于丈夫的大发雷霆,孙氏满头雾水:“女儿每晚与我同睡,哪里可能半夜里和雄儿私会?我又不是死人,难道女儿从我身边溜出去我会不知道吗?”
听到妻子信誓旦旦地力证女儿清白,周守诚一把拽来了侄儿周德:“阿德,你来说!”
本是偷着向叔叔打小报告的周德没想到一下子就被推到了明处,看着婶婶不善的眼神,不由期期艾艾地口吃起来:“……我……我也吃不太准……不过听声音分明是杨雄和晓芙妹子在房内亲……亲热……”
“放屁!”孙氏可不是那种性情软糯、只会唯丈夫之命是从的柔弱女子,随着她的一声断喝,周德的脸上已经被火辣辣地抽了一记巴掌:“我的女儿我自己知道,谁要是再传这种捕风捉影的话,看我怎么收拾他!”
看着孙氏拂袖而去的背影,周德捂着脸向周守诚苦道:“叔叔,我这可是为了堂妹好!”
“算了算了,这事也没有真凭实据……阿德,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