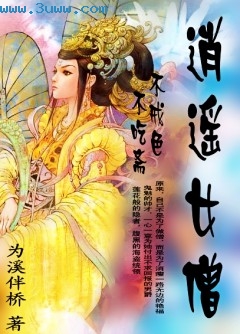新聊斋-第3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见势头不妙,那汉子一边躲避着王老头的花锄,一边飞速地往院外退去。
院门口的青石本就长满了苔藓,吸饱雨水后滑不溜丢,挑粪的汉子急于趋退崴到了脚,一个收势不住仰天直直摔下,后脑勺顿时砸在了阶沿上。那汉子连一个字都没有哼出来,便僵僵地不动了。
被吓呆了的王老头半天才回过神来,见此刻天时尚早,四周并无其他人发现到这一场意外,忙定定心神,将死尸拖到了巷口东侧的小河浜旁,又将他的扁担、粪桶一股脑儿地搬了过去。慌慌张张地清理干净现场之后,王老头掩上门,抖索索地念起了佛号:“……阿弥佗佛……我可不是故意的……日后我一定多烧纸钱给你,莫要再来找我……”
他没有注意到,在他对门的一扇窗子里,有双明亮的眼睛正在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事态的发展正如王老头所希望的那样,官府在例行勘察后按失足跌死的说法草草结了案。因为是外乡人,又没有尸亲,挑粪汉子最后由官府出资埋入了城外的公冢。
尽管逃脱了法律的制裁,但对方毕竟是一条人命,王老头仍然难免心中惴惴,不仅初一十五都会在花圃里烧上两份纸钱,甚至当挑粪汉子亡故周年的那天半夜,他还大着胆子溜到河浜旁边烧了几刀纸箔。
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王老头终于成功地将这件不愉快的往事从记忆里驱赶了出去,年节的烧纸敬香渐渐取消,也不再稍有风吹草动就心惊肉跳彻夜难眠。
如今在这个世界上,还记得这幕惨剧发生的人,大概只有当时唯一的目击者郭雪文了。
他是王老头邻居郭家的独子,两家隔着一条窄巷对门而居,那天清晨郭雪文意外早醒,在二楼卧室里隔窗看到了事情发生的全部过程。
由于害怕、惊恐……以及小孩子对官府莫名的畏惧,郭雪文选择了沉默。当然,即使是他当时出来指证,官府大概也未必会采信一个六岁稚儿的证言。
现在郭雪文已经十一岁了,少年老成的他更加守口如瓶,没有把这件事告诉过任何人,只是下意识地、默默地注意着王老头。
连郭雪文自己也说不出为什么会这样做,或许在他的潜意识里,早已预料到了还会发生什么吧?
这一天又是初春时节,早起坐在窗边温习功课的郭雪文忽然想到,那个倒霉的挑粪汉子正是死于五年前的今天,从二楼窗口居高临下望去,王老头的花圃里姹紫嫣红,就连五年前折断的那枝菊花在王老头的精心呵护下,也重新获得了生机,长得枝繁叶茂。
自从出了那件事以后,王老头不但筑高了花园的外墙,对这些花木也更加呵护倍至。
“可惜人不能象花草一样枯木逢春,那个汉子大概已经连骨头都沤烂了吧!”刚刚想到这里,郭雪文目光及处,差点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花圃门口,正有一个粗壮的汉子在探头张望,看他身形背影、肩头的扁担以及扁担两头摇来晃去的粪桶,不正是那个在郭雪文的印象中应该“连骨头都沤烂了”的挑粪人吗?
郭雪文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对方来寻仇了,但出乎他的意料,那个汉子在王老头的花圃门前只停顿了不到小半柱香的功夫,就挑着担子轻飘飘地走进了与王老头相隔仅有两户之遥的李府。
那是一家绸缎商人,家境殷实,唯一稍嫌美中不足的是李家娘子只生了两个女儿,听说最近她又身怀六甲临盆在即,李员外为此四处烧香拜佛,希望菩萨能保佑这胎一举得男。
眼看着这挑粪汉子前脚刚走入李家,后脚李府就传来了阵阵儿啼之声——事态的发展如此诡谲,让郭雪文只觉心头怔忡,老半天才渐渐醒悟过来——一定是那个汉子托生到李府去了,想不到这一世他竟有如此好命,难道上天怜他前生无故横死,今世补偿于他不成?
从这天起,郭雪文更是象着了魔一样,不仅时时刻刻地留心着王老头的动静,也关注着李家的情形。为此他甚至不顾父母的强烈反对,放弃了到省里进学的机会,执拗地要求留在家里自行攻读。弄得父亲大发雷霆几乎把他赶出家门,而母亲则哭哭啼啼地猜测他定是和这巷子里哪家的姑娘相好上了,才无心上进……总算在郭雪文的努力之下,不到五年光景,他就已经在乡试中一举夺魁,成了县里最年轻的举人,父母的脸上这才重新露出了笑容。
眨眼功夫,李家儿子虚龄已经六岁了,一提起这个小家伙,远近邻居无不皱眉。说起来李员外是一个慢性子的老好人,这个孩子却一点也没有继承到他的好脾气,打从会下地走路开始就没有消停过,最高曾创下过一个月内更换五个奶妈子的纪录。每个奶妈子无一例外,都是带着惊怕的神情从李府连滚带爬消失掉的——与进府时的整洁干净不同,她们出府的时候,不是头发被烧焦就是在鞋底沾满了狗屎,不然便是惨叫着从袖子里抖出了十七八条毛毛虫来。以至于后来牙婆们一听说李府要招奶妈子就止不住连连摇头,声称即使是搬一座金山来也没人肯干了。
何况李员外也不可能真的搬出一座金山来。
刚庆幸李家后继有人的李员外陷入了新的烦恼之中,可不管怎么说,这是他唯一的香火,又是正房嫡子,再怎么淘气不听话,总是李家的宝贝疙瘩。好在小家伙已经断了奶,没有奶妈子就没有吧,多派两个下人照看着就是了。
于是李家下人的噩梦就开始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位小少爷迷上了养鸟,整个李家大院里挂满了各色各样的鸟笼子,从画眉到鹦哥到百灵……应有尽有,不过这些鸟儿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身上的羽毛七零八落——因为它们的小主人最喜欢做的事,就是从它们身上拔毛!
于是附近的居民每天一大清早就可以听到从李府传来的鸟儿们尖利的叫声和李家小少爷口齿不清的嚷嚷声:
“……别灰(飞)……”
“……我要划(拔)……”
“……灰(回)来……”
这天早晨惊醒郭雪文的正是这热闹的声音,隔着二楼窗子看去,可以看见李家的小少爷正满院子地追着一只八哥,从庭院一直追到了三楼的画阁窗口。李家的那些下人们大约早就习惯了小主人的这种晨运方式,此刻正在屋檐下笼起袖子或倚或蹲地抓紧时间闭目养神,没有人发现小孩子已经跑到了他们够不着的地方。
漆黑的八哥被追急了眼,虽然在买来伊始就已经剪掉了它的大羽,但鸟儿飞翔的本能还是在的,此刻见小恶魔带着满脸天真的欢笑一步步地凑过来,嘴里还叫的“……划(拔)……划(拔)……”八哥很熟悉这种声音,知道随之而来的就是无比糟糕的事情,所以用足力气振翅一飞,斜斜地掠过几条屋脊,最后落到了王老头家的花院里。
“……灰(回)来……”心爱的玩具逃走了,刘家小少爷的眼泪顿时喷涌而出,而那只逃离魔爪的八哥显然并没有重入虎穴的打算,站在一根粗壮的花枝上,得意地鸣叫了起来,惹得刚起床的王老头也走到院子里出神地听了起来。
那块拳头大小的石块就是在这个时候飞过来的,被娇纵惯了的李府小少爷见自己的眼泪、恐吓、尖叫对八哥都没有起到慑服的作用,随手捡起阳台上不知从何而来的石块,远远地掷了过去。
石块不偏不倚地砸中了王老头的太阳穴。
虽然这小小的石块其实并不能造成什么致命伤害,但突如其来的砸击让王老头惊跳了起来,落地时一个重心不稳,顿时摔下了台阶,头狠狠地砸在了石板上。
就如同十二年前的那个挑粪汉子,王老头也是连一声都没有来得及哼出来,就倒在血泊中停止了呼吸。
虽然年幼,但李家小少爷也约略知道自己闯了大祸,他很快就抹干眼泪,一言不发地溜下了画楼。
因为事情发生在清晨,唯一有可能作为人证的那些李府仆佣们又在偷懒打盹,所以当官府来查勘的时候,并没有任何人能说清王老头跌倒致死的原因,官府少不得还是以“失足”二字作了这件案件的定论。
和十二年前一样,这次郭雪文依然下意识地选择了沉默。
因为王老头没有子女,最后由他的一个远房侄子出资,将他葬入了城外的公冢里。
王老头的那套住房便由这个侄子承继了下来,不过这位新主人似乎因为忙于生计的缘故,并没有什么莳花弄草的闲情雅致。而失去了主人的精心照顾,王老头花圃里那些名种花木很快就焦枯而死,昔日动人的美丽情景再也不复存在。
“郭兄,好了没有……大家都到齐啦!”
“这就下来!”听到窗外同学们的叫声,郭雪文手忙脚乱地捆扎起了包袱——大比之期将近,一班同窗好友相约共同进京赴考,彼此也好有个照应。
本来父母还担心他还会象几年前那样,无缘无故地犟着性子不肯出门,可出乎意料之外,这次郭雪文却出奇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我的使命到此就结束了罢?——提起行囊,郭雪文最后看了一眼对巷的王家,虽然他从来都不怎么相信怪力乱神的东西,但作为唯一的知情者,每当郭雪文想起十二年来发生的种种情事,仍然止不住感到遍体生寒。
也许上天就是要在这有意无意之间,让世间凡人充分领略到因果循环、报应不爽的天道吧?
被莫名挑中作为旁观者的自己,真不知道算是幸运呢还是倒霉?
见郭雪文下楼,一群少年人说说笑笑地走出了巷子,间或你捶我一拳我推你一把,追逐嬉闹间将巷口几乎堵得水泄不通,也难怪,这些十七八岁的举子们其实还都是些大孩子,平时在学堂里和父母面前少不得要做出循规蹈矩的模样,现在出门远行,脱离出师长们的视线之外,顿时都显露出活泼好动的天性来。
在巷口打打闹闹了老半天,才有人发现一辆马车已经在他们身后等了半晌,车夫正不耐烦地斜眼看着他们,这些少年人才不好意思地吐了吐舌头,让开了一条道。
“老爷坐稳当了!”扬起鞭子,车夫忍不住咕咕哝哝:“差点被你们担搁了正事……也亏我家老爷耐性子,要换了我,哼……
“没关系的!”车厢里传出来的,是老好人李员外的声音:“反正是烧香还
还愿而已,不急不急……呵呵说起来真是菩萨显灵,让我这个宝贝儿子一下变得这么听话懂事,昨天还吵着要上学堂念书呢……这次我定要好好多烧几柱高香……”
最后几句话随风飘到了郭雪文耳中,微微一怔间,他的脸上露出了由衷笑容——本来还担心李家少爷小小年纪就行凶伤人,只怕长大后另有他患,现在看来,自己是真正可以放下这条心了——紧紧肩上的包袱带子,郭雪文轻松地向前迈开了大步……
毛怪
初冬的暖阳懒洋洋地悬挂在天空,一大群鸡鸭在田头里东刨西啄,寻食秋收后余下的碎谷子。农人们则趁着这难得的农闲时节,三三两两散坐在背风的墙角里,或闲唠家常,或拢起袖子闭目养神。就连平时满世界乱跑的猫狗们此刻也是难得的安份,慢条斯理地梳舔着自家的毛发,间或轻轻叫上几声——整个山村都沉浸在了一片宁静闲适的氛围里。
忽然象是受到了什么惊吓似的,田头的鸡鸭们同时尖叫了起来,眨眼间便如同炸开的马蜂窝般四散奔逃开去。
一条黑影出现在了村口。
“可恶,又来了!”看到鸡鸭受惊逃逸,男人们纷纷站起身来,四处寻找着趁手的家伙:“索性和它拼了罢。”可还不等取到器具,他们身后已经围上了一群妇孺和老人,哭哭啼啼地扯手拉脚:
“小栓子啊,别上去送死……”
“孩子他爹,你们打不过他的……”
“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抛下我们两个老的可怎么活呀……”
……
男人们奋起的一股勇气立时就在这哭泣哀告声中消散得无影无踪,不过也不能怪这些拖后腿的女人或是老人们,无论谁看清了奔到眼前的这个巨大怪物,都止不住会在心中打起突来——那是一个遍体毛发披拂的怪物,仔细看去,其实五官口鼻和普通人也没有太多差异,但那高达丈余的身材和粗壮强健的四肢,都在在彰显着这绝非是寻常人能够对付得了的怪物。
更何况还有活生生的例子摆在那儿呢——这毛怪不但力大无穷,而且动作灵活异常,往往十多人围攻还讨不了好去,上个月同村的阿牛就是被它一脚踢伤腑脏断送了性命,剩下孤儿寡妇艰难度日,凄惨异常。
毛怪的势子来得极快,那些来不及逃远的鸡鸭们被他的长臂轻轻一捞,便凌空抛进了那张阔口里。几只鸡鸭生吞下肚,那毛怪仰天张开大口,将满嘴的毛羽喷了出来,一股浓浓的鲜血顺着嘴角流下,看上去说不出的狰狞可怖。
这样吞食了十多只鸡鸭,大约是觉得还不够过瘾,那毛怪索性跨入了农家的院墙,搜捕起猪圈里的猪仔来了。百多斤的肥猪在巨大的毛怪面前简直如同小猫一般软弱无力,同样是轻轻一抛就被扔进了毛怪嘴里,不过两柱香时间,毛怪的肚皮便已经吃得鼓胀溜圆。总算不幸中的万幸,这毛怪似乎并无伤人之意,目光始终只在那些家畜身上逡巡。吃罢了肥猪,毛怪又开始打量起牛栏来……
农家贫苦,这些肥猪、耕牛都是每家每户极为重要的经济来源,那些农人急红了眼,正要挣脱身边羁绊上前拼命,忽然有一个人从人群中大踏步地走近毛怪,仰头向着毛怪高声叫了起来:“筑长城!筑长城!筑长城!……”
说也怪,本来正在专心研究先吃水牛还是黄牛的毛怪,在听到这几个字之后,身子顿时簌簌发起抖来,随即怪叫一声拔腿飞奔而去,瞬间就消失在茫茫的山峦之中。
看呆眼的村人们老半天才回过神来,定睛细瞧,那个念出神奇的击退毛怪符咒的人,是村上昨天才请来教读私塾的先生朱秀才,真没想到这文弱书生居然有这样的能耐,仅凭几个字就驱走了毛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