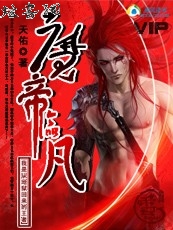布谷 作者:亚莱克斯-第1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比利?对付别人我还有更厉害的招儿呢!”莫伊拉回答。
电话铃声响了,莫伊拉拿起话筒:“说你在,还是不在?”
她觉得瓦莱丽已经被折腾够了:“谢谢,我来接。”
她拿起电话:“瓦莱丽!”
“不,我是帕特里克·汤姆林森。《大英百科全书》,记得吗?”
“哦,你好,汤姆林森先生。”
“我这儿有你想要的消息,关于现金买书的事儿。”
“请说吧。”
“想和你一块儿去喝几杯,怎么样?是不是没门儿?”
“那还用问?”凯茨回答得非常坚决。
“你会后悔的。”
“知道,你昨天已经说过这话了。”
“好吧,说正经的。我这儿有三个人:住在霍夫的布雷尔·哈维、布赖顿的亚瑟·邓恩,还有皮斯的丁·斯摩尔先生。”
“谢谢。”
“他们去年差不多在同一时候买了书,留了电话,我以后每年都要给会员送几本书,让他们的藏书赶上最新的出版趋势。”
“会员?”
“是啊,买了百科全书,就成了我们的会员。”
“他们的年龄有多大?”
“谁?”
“哈维·邓恩还有斯摩尔。”
“不知道,不过我可以查。”
“那,帕特里克,你能不能……”她尽量把声音放柔和些。
“没问题。”那边的回答很爽快,“不过,可能得再等一两天时间。”
“太谢谢你了,帕特里克。”
“没什么别的事了吧?”
“对。”话刚出口,一个念头问进了她的脑海,赶紧补充道:“我是想说,还有事儿。”
“你能不能安排下星期访问用户?这样我可以假装实习生跟着去。”
“是和我一起去吗?”
“谁访问用户,我跟谁去。”
“是我。”
“那就和你一块儿去。”
凯茨再次对汤姆林森表达了谢意。放下话筒,她还是觉得有点不自在。想到晚上和汤姆林森一起加班,她一点儿也不感到兴奋,相反要瞒着探长和布莱克赛去做这件事倒着实让她伤脑筋。最后,她想通了,去它的,既然上班时间被拴在电脑机房里,那还可以利用下班时间干点什么。就把它权当作和男朋友共度良宵,那又怎么样呢?
和汤姆林森通话固然称不上是件快事,但至少让她从中获取了活力。六点了,她的心情也好多了。她给瓦莱丽打了个电话,两人决定七点在运通公司见面。
凯茨马不停蹄地往数据库里输入着挨户调查的笔录。她输入的速度很快,内容都是些连资料都称不上的东西。即使称得上资料,也离情报差着老远。出色的侦探只收集那些有助于破案的情报资料。不具破案价值的事实材料,只能把破案工作带人云雾里。“福尔摩斯”软件有长处也有短处。它能查找某人的犯罪记录,从档案局调出指纹记录,列出各事实间的可能联系。可是这些联系中绝大部分是毫无价值的偶然巧合。“福尔摩斯”的问题在于,它让人陷入事实材料的汪洋大海,无从得知哪些是关键材料,哪些人是真正的涉嫌人员。
凯茨眼前闪现出瓦莱丽和他的“东芝”手提电脑。他可以往里面输入材料,再把它们加以整理,贮存。可是材料终究是材料。有了它,固然我找材料的时候可以快一些,它还可以帮人设计,索引目录等等。但是最后把材料和结论联系起来的还是掌握信息的人。
要是哪一天电脑能把贮存的信息资料变成思想,那人类就真的失去了第六感觉。凯茨读到过一些有关直觉根本不存在的资料。这是一个无意识的过程。所谓警察凭直觉破案,其实还是指他们凭借丰富的经验和已知情况作出结论。有时连他们自己都不敢相信得出的结论竟会如此正确,可有的时候结论又是错误的。不能仅仅因为人们无法确切地表达出其中的原因,就下结论说他们的做法是毫无道理的。
凯茨的手在键盘上灵活地运作着,连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输人的是什么内容。这种感觉就好像开车到了某个地方,却不知从何而来,身在何处。她打印了一张信息清单,在上面写着:“男性,身穿类似淡黄褐色的外套”,“浅色外套”,“浅色雨衣”。刚才输入的时候,她根本没注意到这些内容。她打算进一步查询一下。
屏幕闪了几下,过了一小会儿,打印机“哧哧”地响起来。五个目击者中包括拉尔夫夫人。其中三位认为目击对象是男性,一位认为是女性,一位不能肯定是男是女。五个人都看见了身穿浅色外套的人,其中三个人说,目击时间是10点左右,一人说是9点,还有一人认为是在九点半至10点之间。其中一位还提到了金色长发。至于吉姆·格林的案子,至今还没有来自霍歇姆的消息。
已经7点15分了,机房里就剩下凯茨一人。外间的办公室里黑漆漆的,只有她的办公桌上亮着黄色的灯光。她抬头看看钟,又低头看看打印出来的材料,轻声诅咒了几句。
瓦莱丽的车停在运通公司大楼旁边,车身笼罩在昏黄的街灯下。车已经发动起来,凯茨走到驾驶座一端的车窗旁,说了声“对不起”,透过深色的车窗玻璃朝车里望去。她隐约看见有人在挥手,便又道了声“抱歉”奔到车身另一侧。车门锁着,她敲了敲窗。门开了,她钻进车里。
“我睡着了……”瓦莱丽慢吞吞地说。
“我来晚了。”
“我可没觉出你迟到了。”这显然不是实话。她吻了他一下。
车驶上斯坦尼时,凯茨说想走得远一些,“你觉得这主意怎么样?”她显得温顺。
“只要你下命令,怎么都行。”
“那么,去霍斯梅,你觉得远吗?”
“我根本就不知道它在哪儿。”他说。
“在格乐德和彼得斯之间。”说完,她补充道:“就35英里远,我们可以听听音乐,说说话,多好。”
“是吗?也许还可以去格里格斯喝一杯。”
“离得很近吗?”凯茨问。天下起了毛毛雨,车窗蒙上了一层水珠。
“见你的鬼,你知道得比我还清楚呢!”
“我真的很想坐坐长途车,瓦莱丽。”她边说边抚弄着他的手臂。
“没问题,我其实就想听你说这句话。”
他们出了城,驶出A27号公路,上了A283公路。瓦莱丽决计不再追问这次旅行的缘由,只是告诉凯茨自己刚读完那本《自私基因》。
“这本书不错。看来我不是我,只是一堆早已排列好的基因,对吗?”
“这只是看待遗传的方式之一,瓦莱丽。如果说人类做事是出于某种动机,那么那些猪啊、狗啊、其他生物不都是一样吗?”
“当然。”瓦莱丽说,“或许苍蝇、跳蚤,甚至细菌和病毒都有它们各自的目的。但是基因……”
“为什么基因就不能有动机呢?”
“因为它们不会思考!”他让车速保持在50迈,享受着驾车的愉悦。他认为书里关于行为解释的那一部分更有意思,凯茨追问理由。“哦,我也说不上来。比如说关于献殷勤,膜拜仪式等都很有意思,还有关于妒嫉。”这时,车旁闪过一块路标,上面写着:“珀尔伯夫,5英里。”
“哦,是的,”凯茨说,“妒嫉倒是一种比较容易解释的行为。”
“你说说。”
“比如说,有两个人,就拿你和我做例子吧。假如咱俩住到一起,并且有了个孩子,这其中什么事只有我知道而你却永远不会知道?”
“我在开车,”他说,“还是你说吧。”
“好吧。换个说法,假如你和一个女人上床,她有了孩子,那么孩子是谁的?”
“我的,当然是我的!”
“你怎么知道肯定是你的?也许她还和别人有过性关系。所以,在这一点上你无法肯定,但孩子的母亲可以肯定自己作为母亲的身份。我们得忍受十月怀胎带来的种种不适。可是做父亲就容易多了,随便哪个男人都应付得来。”
“你说什么?”
“瞧你,瓦莱丽!你的偏见暴露出来了吧。”
“往下说,继续。”
“拐弯,走通往米德赫斯特的A272公路。”她停顿了一下,“好吧。雌性哺乳动物知道自己是孩子的母亲。为了把孩子抚养成人,她得找个帮手。孩子身上有自己的基因,她心里就有了底。现在真正失落的该是那个把精力投在别人的孩子身上的那个所谓‘父亲。’”
“这跟妒嫉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不要相信人们说的什么‘妒嫉使人失去理智,’什么‘她要是爱你,总会回到你身边’一类的鬼话。好好想想,如果一个男人牢牢看住自己的妻子,他就不会戴绿帽子。而那些思想解放的家伙都在照看别人的孩子。虽然也许他爱那个女人,很乐意这么干,可是那终究不是他的孩子,这后者就是缺少妒嫉带来的后果。”
“哦,”瓦莱丽恍然大悟道,“我要是没理解错的话,你是说,男人最好把老婆牢牢拴住,不要让别的男人有任何可乘之机。”
“完全正确!”凯茨说,“但是男人不会简单地把女人锁在家里,他们会要些小伎俩去达到同样的目的。”
“既然女人明确了做母亲的身份,为什么还要妒嫉呢?”
“这妒嫉跟男人的妒嫉是两码事儿。女人只想有个人照顾孩子,最让她牵肠挂肚的就是孩子不能失去父爱。毕竟,男人在外面稍微拈拈花,惹惹草,还不算太严重,而女人就不一样了。”
“这么说,我也可以去和女孩子搭讪搭讪了?”
“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们只是假设而已。如果哪一天这个大众情人往家带回一打孩子,她妻子不疯了才怪呢。”
“我还是不太明白……”
“男人在外面拈花惹草,给女人带来不安全感。”
“这儿肯定离格里格斯不远了。”瓦莱丽插嘴道。
“是吧。”凯茨正说得兴起:“在这件事情上,男人一不小心就会戴绿帽子。所以他们对女人的占有欲要强而又强。可见,对男人来说‘妒嫉’倒是件好事。”
“好吧,老实说,今天晚上为什么迟到?你到底上哪儿去了?”
“嗬,你倒是学得真快。”车放慢了速度。
19
路边的告示牌上写着:“车过小镇,请小心驾驶”。这里有明确的限速规定,他们俩摇下车窗把车速放慢到了每小时25英里。
“这地方太差了!”凯茨叫了起来。
“感觉就像是别人的宠物一样。”瓦莱丽接着道。
“你说什么?”
“这个地方,就像别人养的宠物一样。它很可爱,把玩够了还可以还给人家。住在这么偏僻的地方,可没有想像的那么好:失业率高,工资低,各种服务设施也不健全……不过,光是看看风景倒还不错。”
“那就太惨了。”凯茨说。
“对现实主义者来说,的确是有点惨。”他说。
他们驶过一排红色的公用电话亭,只见前面是个屋檐低矮的酒吧,门口挂着块黄绿相间的大招牌“醉鬼”。“太好了!”瓦莱丽一眼看见了这个招牌,车拐进停车场。
周五傍晚,停车场里也是高朋满座。他们好不容易才把车停在了一辆黑色富豪车和一辆白色卡车之间。还没下车,就听屋里一片嗡嗡的说话声,叮叮当当的碰杯声,赌场里间还传来吆喝声。
“太棒了!”凯茨叫了起来。瓦莱丽看着她兴奋的样子,朝她做了个鬼脸。
酒吧里人头攒动,黑漆漆的矮桌上放满了啤酒瓶和玻璃杯。靠墙的四周,人们三三两两围着吧台坐着。昏黄的灯光笼罩着整个屋子,吧台后的侍者一个个心力交瘁,脸色苍白。屋子的一角飘过来一股甜丝丝的烟草味儿,有个人正在那边讲笑话,周围至少有10个人围着听故事的结局。这个人留一头式样难看的棕黄色头发,长着一双炯炯有神的蓝眼睛,红脸蛋鼓鼓的。故事总算收场了,他心满意足地拍了拍一名“听众”的肩。“嘿,乔治老兄!”有人喊道,“又在吹牛吧!”
“吹牛我自己知道。”乔治回答。
瓦莱丽凑到凯茨耳边问要什么饮料,她要了杯干白。他的气息热热地吹在耳边,快乐在凯茨的心里荡漾开来。瓦莱丽很快消失在一片桌椅之间。
一对夫妇站起身来,离开了座位。凯茨很快占据了那两个座位。说实话,坐了一整天,她倒很想站一会儿。过了不久,瓦莱丽回来了。他两手端着饮料,腋下夹着菜单,看上去像个招待。看凯茨不在原来的地方了,他有点茫然。凯茨突然觉得他简直像个小男孩一样。她朝他挥了挥手,瓦莱丽的眼睛一亮,快步走过来:“我想,你可能饿极了。”瓦莱丽说着,用手拍着写在塑料板上的菜单,“反正我是饿了。”
菜单上的字显然是用老式打字机打的,整张单子看上去乱糟糟的。在不该空格的地方有许多空格;所有的“e”都漏打了;所有的“r”字母都比别的字母高出一头。凯茨点了一份鸡和薯条,瓦莱而要了份食虫虾。
女招待在人丛中来回穿梭,动作很麻利,胸前的牌子上写着她叫“安妮”。她不是那种羞答答的小女孩,已经三十好几了。看起来,她活得很开心。
“请稍等五分钟,小姐!”她说着,往桌上放了张“17”的牌子。吧台那边传来一阵阵哄笑声,乔治还在讲笑话。“知道那个讲笑话的家伙是谁吗?”瓦莱丽凑近了问。
“那是乔治吧……嗯,好像很有性格。”
她呷了口酒,那是一种廉价酒,凉凉的,不过还说得过去。瓦莱丽把酒和可乐掺在一起,据说这种饮料喝多了,不知不觉就会大醉。凯茨尝了尝,觉得味道就像咳嗽药水一样。
瓦莱丽说自己喝得高兴是常有的事,不过倒是难得喝得酩酊大醉。“除了失恋的时候。”他变得一本正经起来,“那种时候,我会关了灯听着埃尔顿·约翰的爱情歌曲,来个一醉方休。”
“你可不像那种借酒浇愁的人。”她说。
“那是你还不了解我。”他不客气地说,“没准哪一天,我会听着埃尔顿的《蓝眼睛》自杀,而且会发现沙发上还有个空酒瓶。”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