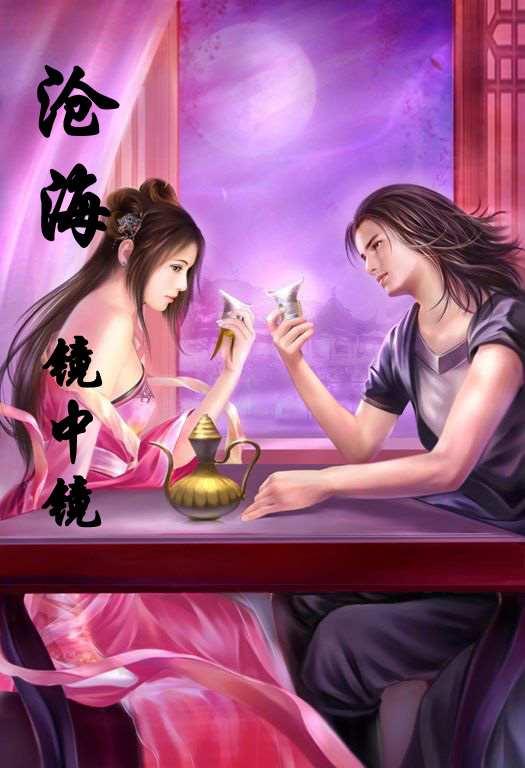哪怕沧海变成桑田-第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字真言?
唵嘛呢……?
俺叭呢……?
唵嘛呢叭哞吽!
终于想起来了!冷凝如释重负,顿时在心里狂念起来:唵嘛呢叭哞吽!唵嘛
呢叭哞吽!唵嘛呢叭哞吽!
果然佛祖是慈航普渡的。三遍还没念完,背后的脚步声嘎然而止。冷凝对于
自己的聪明才智,一时不得不深表敬佩,当下还恐效力不够,努着劲又补念几声。
却听身后一个怪样的声音道:“凝儿!”
冷凝吓得一颤。答不答应呢?还在奶奶的故事中紧张地思索着——好象有一
种鬼,专门叫人的名字勾魂?身后那人已经冲了上来,又叫一声道:“这么巧呀,
凝儿!”
冷凝扭头一看,鼻子险些儿没给气歪。原来却是个剑馆的同窗。就是昨天在
演武大厅里站在她旁边,给她翻《暗器打穴大法》还没翻出个结果的那男弟子,
小名叫做阿明的。老天丫!这家伙在她屁股后面跟了这半天,差一点没有吓破她
的胆,还好意思说“这么巧”?
阿明笑道:“这么晚一个人往哪去呢?还拿着把剑,不是又去打虎吧?
冷凝本来就生气,让他这一说,更不高兴了:“我跟阿闲约好了到锥子山上
练剑。”
“是么?”阿明一边说,一边环顾四周,好象是看阿闲在不在,然后就忽然
递过一样东西来:“这个给你。”
冷凝接过来,夜色下认得是个竹筒,不晓得里面装了什么。在手上摇一摇,
好多小东西滚动着滴滴答答地撞在筒壁上,终于明白过来:“炒黄豆?”
阿明一怔:“呃……是呀,我妈炒的。”
冷凝道:“那谢了。那你这么晚,在这里又做什么?不会是一边吃黄豆,一
边散步吧?”
阿明道:“呃……只是随便走走。”
“那你继续走吧,”冷凝道:“我要上山去了,说不定阿闲已经在等我了呢。
再见!”
“再见!”
冷凝听到这一声,已经向前走出两步路。心里只觉得阿明奇怪。一个大男人
家,吃什么炒黄豆呢!不过这一层奇怪,也没怎么放在心里,过桥上山,到了塔
底,阿闲果然已经到了,月亮头下,正把剑使得花团锦簇呢。见她过来,不由分
说,刺过一剑。
冷凝跳开,以一个优美的姿态反手拔剑,迎将上去。两人遂剑来剑往,各自
亮开前无古人的俊逸势子,迎战对方后无来者的臭滥剑法。当然,再臭的剑法,
对于锻炼身体总无坏处。尤其摆势子比较累人,两个人如此这般风情万种、风姿
摇曳的交上手,不要多久,额上也都见汗。阿闲先跳出战圈:“歇会儿吧。”
“好的,”冷凝巴不得这一声,早把剑往鞘里一插,拿出竹筒:“来,吃炒
黄豆。刚才正巧碰见阿明,给的。”一边说,一边把竹筒盖子一揭,倒出两把豆
子,跟阿闲一人一把,信步往塔内走去。
“这是什么豆子?”阿闲走在前面,道:“可不象黄豆呀?”
冷凝往掌心一看,那豆子果然不是黄豆。黄豆圆鼓鼓的,这些豆子却生得煞
是苗条。看来阿明也是个五谷不分的家伙,只知吃,混不知吃的什么。好在无论
他知道与否,只要是豆,总是尽可以吃之不妨。冷凝伸指一弹,一粒豆子比打镖
还准确,百步穿杨,落入口中。那边阿闲也跟着吃进去一粒。
两个人嘎嘣一嚼,表情忽然都异怪起来,一个面面相觑,忽地一起弯腰低头,
张嘴大吐。阿闲对着墙脚连连“呸呸”上几口,直叫道:“呸!这简直是什么世
道?连阿明这种人,也都学会耍弄人了!”
冷凝跟着吐完,抹抹嘴,苦巴巴地没有说话。阿闲愤然道:“且看看是什么
东西!”噔噔噔冲上二层,凑到塔眼边仔细一张,月光下那豆子黑乎乎地,还是
看不出个所以然。好在她是刚刚发奋向上,虽没正式练好武功行走江湖,那行走
江湖的诸多物事倒带得齐全,信手摸出火折子,一下吹亮,便往手掌心里一照—
—不照则已,这一照,顿时“咯咯咯”止不住直笑起来。
冷凝凑上去看,却见那豆子不止是身材苗条,连脸蛋都漂亮得从所未见,一
半红来一半黑,在阿闲手里聚成一堆,被火光照耀着,粒粒饱满,灿灿发光。阿
闲笑得肩膀直抖,怕把豆子抖出来,连忙把手握成拳头,笑道:“这个真是阿明
给你的?”
冷凝情知有什么不对:“怎么了?这到底是什么豆子?”
阿闲要说,忽又笑得止不住,弯下腰去直揉肚子。冷凝大急,抓着她又推又
搡,连连道:“笑什么嘛!笑什么嘛!快说快说,笑什么嘛!”
阿闲笑了半天,等到好不容易平静下来,却不忙着回答。先是一肃衣襟,清
清喉咙,从塔眼里无限深情地了望明月,忽然拉长声音,吟起诗来:“红豆生南
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笨丫头!这是红豆呀!恭喜你啦!
这下可终于被人家看上啦!”
冷凝将信将疑:“这就是红豆?你怎么知道?”
“切!”阿闲不屑道:“长了这么大年纪的人,都没见过红豆的,恐怕就只
有你了吧?看你这模样,其实也不是特别对不住大家的眼睛——算了,既然是红
豆,两馋嘴猫也只好歇一歇了,来,再把它装回去。”
冷凝机械地把两把红豆又装回竹筒。坚硬的豆粒洒落筒底,响得圆润而清脆,
可又说不上来有些空荡荡的。冷凝心里也空荡荡地,有些发慌,没有着落,整个
人虚飘飘地好象浮在了什么地方。阿闲一口吹灭火折子,道:“倒看不出阿明…
…这么闷的一个人,也有这心思!”
冷凝不答,只又机械地合上筒盖。抬眼看明月,那月亮飘在天空中,很远很
远。恍惚之间,仿佛有什么东西也象月亮一样的飘远了。只那是什么呢?难道是
岁月?是没有认识红豆之前的那段岁月?
飘得远远的月亮仍旧在清灵灵地照着人间。不远的山路上,缓缓走来一对情
侣。二月里的春风温柔地从山坡上拂过来,又从塔眼里钻进去,一股馨香的气息
便不知从什么地方泛出来,倏忽间渗透这个轻暖的春夜。
一片温馨的寂静中,山坡上的那对情侣渐渐走近。春风中隐约传来一串轻咳。
这轻咳有些似曾相识,冷凝微微一怔,仔细一瞅,果然认出个熟悉的身影来。可
是,那熟悉身影身边的那个女人,却又是谁?又是谁以那样粘腻的姿势,走在一
贯孤家寡人的乱草丛身侧?
再走近些,还是阿闲见过几面,认出来了。这女人谁能想到,竟就是昨天的
新娘子月影如花?月影如花挂在杞成舟的胳膊上,两个人依依偎偎地,在串串病
态的咳嗽声中,一直走到塔下站住。几乎是在同时,剑馆先生低头看看身边的女
人,月影如花也在抬头,两张嘴唇便没有任何前兆地,互相凑了过去。
这样的春夜未免有些迷乱。隐在塔里的两个人大气也不敢透一声,只有心跳
不听使唤,怦怦如鼓般跳。而塔外,正有一场激情在燃烧。吞噬与快乐,渴望与
疯狂。男人女人的喘息混在一起,也不知是被春夜点燃了,还是他们点燃了春夜?
这样的春夜呵,总是让人有些不能忘怀。
葬花公子两骑快马一前一后紧擦着镖车,爆豆也似的蹄声中,夹着一声轻笑,
飞一般去远。从早晨到现在,自翠云廊蜀道这样追过来的西南堂快马,已经是第
十八对。马上的三十六个人,清一色的太阴教天青色服饰,在翠云廊森森古柏的
掩映下,便留给大家一串黑幽幽的印象,以及嵌在黑幽幽的袍子上,在奔驰中翻
滚飞扬、晃人眼目的三十六弯冷月。
插着西川镖局镖旗的这一行镖客,从成都府出镖,四五天走下来,也已经走
了一半的路程,眼看着过了前面素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绝险剑门,便是
往汉中去的栈道,却偏偏在这个要紧关头,撞见这伙惹不起的祖宗。别的不说,
负责押这趟镖的镖头凌风尘单是听到这声笑,便知道今儿这趟镖,可算是遇到麻
烦了。
在肚子里揣摩一阵,凌风尘便转头去问这一次跟镖而来的青城派师兄。她所
属的这个西川镖局名气不大,在川中一向受青城派荫庇,因而每次出镖都由青城
弟子跟镖,已成一种沿袭已久的惯例。一者,可以借青城派的名头,保一保路途
平安;二来,也是利益均沾的意思。今儿这次,跟镖来的便是掌门人无缺道长的
得意弟子东方佳木。凌风尘身为东方佳木七师叔无心的记名弟子,论起辈份来,
是他的师妹。这当儿,便向他探过头去,低声道:“东方师兄,情形可有些不对
呢。”
东方佳木道:“是么?”
凌风尘道:“这些人身上并无包袱,不是走长路的模样。而且前面就是剑门
关,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魔教的魔崽子们偏偏在这个时候,先我们一步过
去,我看不只是一种巧合。”
东方佳木道:“是么?”
凌风尘道:“大家几个月前才起冲突。虽说江风楼协定中,他们已经占了很
大便宜,可这些人又哪有个餍足的时候?要重起争端,那也是可以想象的事。”
东方佳木道:“是么?”
凌风尘道:“只是要重起争端,总得找个理由。就象上次明月楼的大厨,指
不定是他们自己杀了,却混赖在我们身上。不过在市廛里找理由,总难免破绽,
现在这边荒野地的,哪怕他随便栽个什么赃过来,我们如何分辩?所以我的意思,
这一路往前,大家可得千万小心了。无论看见什么可疑迹象,都不要上去插手。
不知东方师兄意下如何?”
东方佳木道:“是么?”
四个“是么”说下来,凌风尘终于明白,跟这位师兄商量事情,是白费精神
的。无奈之下,也只能自顾着把这层意思吩咐下去。一边肚子里暗暗抱怨,却不
知这一次,青城派给她派了个什么样的师兄来?从成都府走到现在,也好有几百
里的路程,这人倒好,一共说了可有十句话,加起来总计不超过二十个字。看来
派里的纷纷传言倒是确的了,说是山脚下玲珑斋里出了事故的那位姑娘,却是跟
他有了私情,偏又被他始乱终弃,这才终于闹出上吊自杀、一尸两命的事情来,
哼!
凌风尘想到这事,便在心里痛骂一声。一时不免又为那位不幸的姑娘,使劲
儿捏一把拳头。不用说,若在平时,碰见这样的不平事,她早是一拳头打过去了。
偏偏今儿犯事的人却是师兄,这一把拳头,因此,也就只能是在心里捏一捏而已。
而如果同样的事情,犯在师兄身上,拳头就捏在心里,犯在别人那里,拳头就打
出去,那这种打出去的拳头,其抱不平的公正成分,不管怎么说,总是打了很大
的折扣吧?但是有什么办法呢,这就叫人在江湖,身不由已。
既然人在江湖,身不由已,凌风尘也就不再去管她师兄的风流韵事,自管留
心着这一溜镖车,迤逦顺着山路,一直走到剑门关下。
时间已是酉时,只夏季日长,天色还是大明的。一行人走到关下,那剑门关
却出人意料,两扇朱红色的大门早已关闭。凌风尘一马上前,看着天下第一雄关
夹在大小剑山的峭壁狭谷之间,被两扇铜钉森森的大门封得严实,不祥的感觉愈
加浓郁。虽说是年轻,可十八岁走镖至现在,剑门这条道也算跑了无数次,这还
是第一次见识关门昼闭。而不久前越过镖车的三十六骑,这里却又没有见到,也
就是说,剑门关放了他们过去,却独独将镖行挡在关外。这其中,又有什么奥妙
呢?
“军爷!”凌风尘在关下大叫:“麻烦开个关,借一借路!”
关上守军从箭楼里探出半个身子,却是慢条斯理的:“大姑娘,你也忒不明
理了,若是还能开关,军爷我闭它作甚?”
凌风尘叫道:“可关门昼启夜闭,现在光景还早呢!”
“早是还早,”那守军道:“可是上头有令,今夜圣教总坛里有人入关,为
安全计,那边已经遮断栈道,这边自然也不准放人进来。所以大姑娘呵,你们也
只能委屈委屈,在狭谷里安顿一夜了。好在圣教使者明天就走,你们明日过关,
可也不迟呵。”
说话的守军是个熟面孔。从答话的口气上看,也不象是欺哄。凌风尘再无话
说,只觉绷紧在心里的那一根弦,蓦地里倒松弛下来。老天保佑!原来她还猜想
错了。西南堂的那三十六骑,照此看来,是为了迎接总坛来客,却不是冲镖队而
来。只不晓得魔教总坛这个时候有人来川,又是为了什么?会不会跟他们青城派
又有什么牵扯?不过这个问题,也就不是她这个青城派的小角色所能操心的事情
了。
入关既然无望,镖行这一众人马都惯走江湖,当即就地扎营,生火做饭。只
有凌风尘做事把细,不免趁此机会查看查看地势。虽说剑门是熟路,每当再看,
那种险恶情形,还是令人坐不安席。单只看这巍巍两山紧夹一谷,前有剑门,而
后面再若有追兵呢?更有甚者,连左右对峙的大小剑山上,万一还伏得有敌人呢?
一时施展轻功,沿着小剑山的侧脊奔上去,还好并未发现想象中的敌踪。在
山顶舒一口气,暮蔼四合中举目四看,却见那对面的大剑山上,俨然有人。
山顶的大青石上,白衣飘动,有人危坐。凌风尘先吓一跳,再仔细一看,那
人影却眼熟得很,原来却是跟镖过来的同门师兄东方佳木。一袭白衣被山风吹得
猎猎飞舞,在渐黑下去的天色中,浅淡的颜色透着股沉埋不掉的孤凉,从一片昏
暗中寂寞地挣扎出来。凌风尘心中一动,想要招呼一声,不知为什么,却又没有。
忽然想着,经历过这种事情的人,合该比别人多些心事?只是早知如此,何必当
初?
夜,瞬间就吞没掉所有心事,以及那浸满心事的一袭白衣。这实在是个黑得
伸手不见五指的夜。凌风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