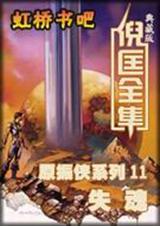111 四月深呼吸-第3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第二部 第三十四章
当大笔资金最终注入公司帐号以后,公司里善良的人们几乎想去打造一座十几个九的全金神台把我供上去,但是我却实再愧对那些倾慕的眼神拷打我的良知,心虚得想逃跑。可是更紧急的是,我必须尽快找出公司里的那黑手来,然而这种情况下我是又想打着耗子又怕碰了满屋的瓷器,除了自己一点点找证据加小心防备之外真的是一点办法也没有。最难受的是,这种情况下,我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一时间愁肠满结,仿佛任何一个下一分钟都有可能长出长长的胡子来。
有人敲门的时候我正看资金计划,头也不抬地说:“进来!”
奇怪的是却没有听脚步声。我抬起头,却看到单杰站在门口。
“要进就进,要退就退,你站那儿干嘛?”我有点没好气。
单杰仿佛下了很大决心,终于走了进来,却放了一份辞职报告在我桌面上。我吃了一惊,望住他,他的眼神倒是一点没有要回避我的意思,但是这一来却突然让我明白了,多日来苦思不得其解的答案就在眼前。
我不想让自己有任何失态的表现,但是内心的冲击却让我真的有点无法自恃。本以为真相大白以后,可以放下这块心头大石,谁知道事实却更让我难以承受。
“不光是他,还有我们。”柳一鸣和Fiona结伴而至,桌面上又多了两封辞职信。
我有点儿头晕,恍惚间感觉叛变的那个人应该是我不是他们吧?三比一,没有人知道这一刻的打击对我而言是如何的沉重。
“对不起。”我站起来,向他们九十度鞠躬,“我想让大家做出被叛公司的选择一定不是一个快乐的过程。能让大家一起去做这么痛苦的事,做为终极原因的我实再是罪大恶极,所以,再没有资格坐在这儿的那个人应该是我,应该离开的人也是我。让大家困挠了,很报歉。”
我站起来想走,却被三双手一齐拉住:“请你听我们说完。”柳一鸣有点激动地说,“没错,我们接受了一份协议,就是这份,”柳一鸣放下几张纸,继续说,“而且是三个人商量以后接受的。因为我们收到的信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唯一可以挽救‘怒放’的机会就是签下这份协议,而且在这份协议里面我们写下了除了让‘怒放’继续营运下去的之外唯一的一个条件就是,你继续担任公司的执行总经理,掌舵公司的营运。而且对方也答应了这个条件。但是最后,因为我们全票支持你做最后一次的资金努力,违反了协议的规定,所以我们也失去了挽救‘怒放’的最后机会,好在,我们终于投资正确了一次,你不旦解决了资金源,而且重组了资金链,‘怒放’开始了良性循环,所以,我们这帮坏人也是时候要谢幕了。应该说报歉的人是我们。”
我傻子一样看着他们。
我一直以为自己不是最优秀的,但一定是最勤劳的,不是最聪明的,但一定是最坚强的。可是现在,这一切却完全颠覆了!我一直以自己的方式在保护他们,包括耍小心眼儿,没想到真正被保护的人却是我自己。如果这一次没有朱嘉华近似神迹的帮助,我的最后一搏导致的结果是多么可怕和严重?!
“我很羞愧。”良久以后,我才艰难地重新开口,“我真诚地希望,你们能给我一个机会,让我与你们能够继续与怒放一起盛开。”
在FIONA的眼泪中,几双肥瘦不均的手握在一处,单杰小声嘀咕了一句:“头儿,下次能不能别这么印刷体了?俺受不了你突然变得这么肉麻啊。”
神清气爽了几天之后,朱嘉华女士突然出现在我的办公室。虽然很意外,但是我还是非常热情地接待了她。对于她的帮助,我除了之前的感激之外,还有了后来的暗自庆幸,因此,我的热情百分之百发自心底。
谁知道朱女士的第一句话说是:“说实话,从一开始我就不喜欢你,现在还是不喜欢你。”
我楞了一下,奇怪道:“你为什么要喜欢我?”
“倒也是。”朱嘉华点点头表示同意。突然又说:“你最近失恋了吧?”
“女人失恋不要紧,关键是不要失业。”我心平气和地说。经历了最近的大起大落以后,爱不爱的事对于我真的不那么重要了。
“我是个失婚女人。”朱嘉华的口气理所当然。对于这个性情古怪的女人,我唯一能回报的就是做个处变不惊的好听众。于是朱嘉华女士继续,“我的前一段婚姻经历了一年臭名昭著的家庭暴力以后结束了,当时我的心里怀有一个愿望,这是没有人知道的:我希望每个身体都有一张床,每一个心灵都有温暖,我想擦干每个人的眼泪,不再让任何人拉掉别人的一根头发。就这样,我努力地工作,然后在这儿,在广州,一年前,我遇到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这个男人。我们同病相恋,他在我心目中拥有一切男人应该有的东西:力量,自信,决断……他唯一的缺点就是,他不爱我。因为他告诉我,他爱的人是一个叫李好的女人,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我不喜欢你了吧?”这真是个奇怪的女人,居然可以在别人的办公室里刚刚冷漠地表达了自己对办公室主人的憎恶,马上就可以理直气壮地用诗一般的语言来阐诉憎恶的理由。
我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可是这个男人是谁呢?同病相怜?一年时间,也是失婚男人……WILLSON!我恍然,但是旋又不解:“那你为什么还要帮我?”
“你以为拿钱出来的真的是孙总?”朱嘉华的语气非常不满,“因为他不想让你知道是他在暗中出力,所以才兜了那么大一个圈子,至于我,不过是个临时演员。帮你?如果可以,我情愿你被打下十八层地狱。”WILLSON居然为了我肯改变公私绝不混为一谈的原则,说不感动那就是在骗人了。
“那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对于眼前这个女人我还是吃不透。
“我只是来告诉你,你的债主不是我,如此而已。被不喜欢的人感恩戴德会让我消化不良。”说完,朱嘉华站起来拍拍衣服:“好了,话说完了,我要走了。”
“那我就不说谢谢了,免得影响你的好胃口。”我殷勤地为这位捉摸不透的女士拉开办公室的门。
在位子上坐了好一会儿我才说服自己拿起电话。Willson的是个大人情,我没想好怎么还,但是应该多谢的我不能不说。
“你好,willson,是我。你在忙吗?如果忙我等会儿再打过来。”我听到那边的背景声音有些复杂,习惯性地赶紧想收线。
“李好?!不,我不忙!什么事?”
“哦,我想说,谢谢你。”
“谢谢我?不,要说谢谢的是我。你不知道能给接到你的电话我有多高兴。”
这个世界真是奇怪,想当初,打一次电话给他我总要思想斗争半天,生怕打过去的时候他不方便,甚或给他带来什么麻烦。如果电话那边的回答尚算温柔,揪着的心方才放下来,如果对面有一丝不耐烦,赶紧自觉收线并且担惊受怕,不知道这个电话是否会给对方造成困挠。这样战战兢兢的心情相信每一个自诩被爱情击中心脏的第三者都是颇有体会的。可是现在心平如镜地打了电话过去,对方的兴奋却从电话线里都听得出来。爱情里的男女关系好象总是翘翘板的关系,平衡是永远无法祈及的理想。
正说着,手机趁热闹似的,也响起来。一看,是家里的电话,我只好对WILLSON说:“你HOLD住线等等我,我听个电话。”接通手机,是老哥。说了几句话,我的脑袋“嗡”的一声,后面的话就再也听不清楚了,来来去去只有几个词纠缠在一起,却没办法组成一句完整话:老爸,胃癌,晚期……
我用最快的速度订了机票,跟公司的同事交接了公事,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我把所有的积蓄全部分别转到两张卡上,以防万一其中一张卡失磁还有另外一张可以后备使用。我很清楚当疾病袭来的时候,最有效的治疗手段只有一个,那就是钱。
做这一切的时候,我冷静得象在安排一场商务谈判。这样的时刻我不能混乱,我是老爸嘴里那个让他骄傲的女儿,所以,我只能做让他一直骄傲下去的事。
第二部 第三十五章
不知道为什么,一路上我的心里一点悲伤的感觉都没有,只是在心里谋算着有没有什么关系可以搭到,以便帮老爸询问更详尽的病情或者安排转院,还有,带的钱够用到什么时候。
所以下飞机,见到嫂子红肿着眼睛在秋风里等我时,不由得心生愧意。但是,仔细想想我真的没有办法难过起来。老爸此刻又没到无药可治的地步,我为什么要悲伤?不如出力去找最佳的治疗方案。
可是当我推开病房门的时候,我才知道嫂子难过的原因,身高一米七三的老爸瘦得皮包骨头,躺在白色的病床上连脸颊都窝出骨头的形状,头发因为做化疗的原因全部剃光了,样子变得好怪,脸色是一种没见过的灰黄色,只是那对眼睛仍然亮晶晶的。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居然能够笑着叫了老爸一声,甚至声音里一点些微的不稳都没有。嫂子看了我一眼,眼神颇为复杂。我没管,走了过去,抓住老爸的手,很暖,我放下些心来。
“妹妹也回来了?好,好,好。”老爸连说了三个好,抓住我的手使劲儿捏了捏,但是只一下,就没有力气再握紧了。
看床头的输液架上一大袋乳白色的东西,我扭头看了看嫂子,嫂子解释说:“老爸做了胃全切以后,很多营养靠这个营养液。”
“哟,输上营养液了?您可够腐败的哈。入党的时候一口咬死自己的成分是小职员,人家以前的地主病了也就最多吃两口莲子汤而已,您这小职员一点儿病连营养液都吊上了。”我忿忿不平。
“滚一边儿去。见不得穷人吃口饱饭。”老爸一边叫我滚,一边全把我的手拉得紧紧的。我赶紧使劲儿望了望窗户外面,法国梧桐的叶子全黄了。
半小时以后,老妈做好了汤送到了医院,在走廊里一见到我,双肩一耸“依依依——”地就哭了起来。我忙忙抱住老妈的背,轻轻拍着,忽然觉得老妈又瘦又小,忍不住小声埋怨:“都说我长得矮是你遗传的了,你还一直自己号称一米六二,死赖活赖非赖说是我爷爷隔代遗传,现在好比我还低小半个头!”嫂子红着眼睛跑一边搂着腰乐去了。在我刚想动作之前老妈的手掌“啪”一声准确无误地落在我脑袋瓜儿上,掌风凌利依旧。
等哥也到了医院,我们去了见主治医师。据那位传说中的国手大夫介绍,老爸手术中未见转移,但胃底见弥漫性肿瘤,为了保险起鉴,做了胃全切,现在刚刚做了一期的化疗。现在关键是要看病人术后恢复能力和抗化疗情况。如果一切理想的话,五年存活率是百分之八十。
我每一个字,每一个字都听得非常清楚仔细,生怕漏掉一个字会影响到老爸的生命长度。最后听到百分之八十的存活率的时候,我粗粗地透出一口气这就好办了。对于我来说,多过百分之五十的机率,那就是百分之百的胜利。
然后,事实上,真正面对化疗的时候,我才开始知道什么叫力不从心。老爸的化疗反应很大,吃什么吐什么,而且一化疗就开始高烧,连手指关节都是黑黑的颜色。偏偏他又是胃全切,饮食上诸多限制,短短十天时间就又瘦了三斤。对于正常人来说体重骤减三斤可能不算什么,可是对于已经只剩一把骨头的老爸来讲,这三斤却是让人胆战心惊的。而且,最要命的是,老爸开始表现出对化疗强烈的抵触和厌世的情绪。第三次化疗的时间就快到了,可是不管怎么劝,老爸就是吵着要出院。
因为公司那边事情很多,我也开始着急起来。如果不能安抚好这头,我根本没办法在那边安心工作。姑无论对公司的责任感,至少一点,如果我不工作根本就没有钱来维持老爸庞大的住院和治疗费用。这天,我坐在病床前,正跟老爸深刻剖析如果他不化疗就活不下去,如果他活不下去,老妈迟早一定会改嫁,如果改嫁我跟老哥就变成拖油瓶了的逻辑因果关系,谁知道老头子精神萎靡地闭着眼听了半天,最后咬牙切齿地抛出一句:“那我这两天就把我小金库里的钱先分给你们兄妹俩,免得你妈以后拿去贴小白脸!”
“哐!”没法坐稳,我一家伙撞床框上。
有人敲门,我站起来打开门,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只见WILLSON拎着一大袋子标着“东方红”LOGO的东西走了进来。
“伯父,您好!”他径直走到老爸床前,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老爸这一辈子大约没给人这么待遇过,一时之前显得有点儿蒙了,等反应过来,忙支起上半身:“好,好,你是……”
“我是李好的……好朋友。”WILLSON依然毕恭毕敬地站着回答,印忆中,无论见到怎样的客户他都从不曾这么低声下气过,错愕兼具有些不忍心,我忙递过去一张椅子:“坐下来说吧。”
谁知道WILLSON看都没看一眼我递过去的椅子,依然那样微微前倾地站着。只是眼睛往我的左手腕上注意地看了一眼,我下意识地把有疤痕的手缩了缩。老爸也说:“不要站着说话,坐着说,坐着说。”WILLSON这才向老爸点点头,欠身浅浅地坐下去。
我突然发现,老爸讲这几句话的时候,好象很精神的样子,之前要分钱给我们的时候声音也只是比平时嘀咕的音量大一点而已,现在讲了两句话,都能让三米以外的人听得清清楚楚!嘿,奇了怪了。我孤疑地望了望老爸,居然发现他双目炯炯地看着WILLSON,WILLSON则依然恭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