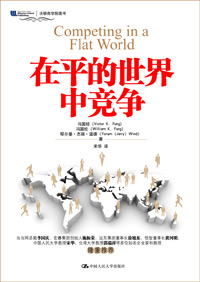亚森·罗平的巨大财富-第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她十分慌乱地挂上电话,给酒吧台的人扔了几个小钱后便逃了出来。水手来到了:她躲闪着他,在酒馆外面拼命地跑着。幸亏她看到了一辆空的出租车,她跳了上去。她已经头昏脑胀了,本应该把弗雷德里克·弗尔德家的地址或者是报社的地址告诉司机的,结果却下意识地把她自己的地址说了出来,就像是一只受了伤的动物,要本能地逃回自己的窝一样。
她突然感到自己特别地疲乏,好像都快要累死了。她想躺下,睡上一觉……忘掉她预感到的这幕惨剧。现在,这出戏已经演完了,她对此已经束手无策了。动荡的事件已经把她压垮了。
她睡得很差,好几次被可怕的幻觉惊醒。在半夜里,她失眠了。这次的冒险令她越来越害怕。关于隐秘的皮公文包这一插曲更增加了她的担心。可是,她经过思索,无法找出合乎逻辑的推理。也就是说,如果公文包从马克·阿莱米那里被盗走,那就只能是强行夺走的。不,她完全相信弗雷德里克·弗尔德已经成了野人的牺牲品,可是,还不到一秒钟,她又为马克·阿莱米担心了。她什么也不去猜想,也不愿意预料任何东西。
第二天,她来到报社,看到办公室里人声鼎沸、编辑室里一片混乱。当她得知老板就在自由广场上的一个商店里被人在心脏上刺了一刀时,她的惊讶是难以言表的。在自由广场!就是那儿,带拱廊的广场!
为了不倒下去,为了保持沉默,她极力坚持着。这一事件令她心绪不宁,她感到自己悔恨不已。她不是可以救马克·阿莱米的吗?她不是可以采取行动的吗?……她只是想着这些,想着在这已发生的罪行中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其余的,就是稍后警方被通知的方式,警探们如何能知道这间商店,店主在那里召集的会议,以及所有的细节,这是大家知道了的。可是对她来说,在此悲惨时刻,这些已经无足轻重了,因为此时,她正像个女犯人一样在责怪自己没有采取行动!
她还是读了所有的晚报,它们以各种资料详尽地描述了凶杀案。她读了各类的评论文章和关于死者的一篇往往是错误百出的生平介绍。一个知名人物的悲惨、神秘的死亡,在读者中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在这些报中,同时还叙述了另一件引起轰动的凶杀案,但是这并没有使帕特里希娅感到意外;不正是她第一个打电话通报的吗?而且就是在凶杀发生之时。这是一桩涉及弗雷德里克·弗尔德律师的凶杀案。他这个人,本应该很快去欧洲的,结果却在自己家中被杀了。就在动身的前一天晚上,被一位来看他的陌生人给了他心脏一刀——与《警探报》总经理挨的那一刀一样。这两起凶杀案是否有某种关联呢?报界都这么揣测着。两个死者关系很好,而且有共同的事业。是一群强盗团伙杀害了他们吗?是否在同一时间杀掉他们的呢?
但是,在弗尔德家,一个保险柜被强行砸开了。一笔五万美元的现金被盗走……难道这是单枪匹马一人干的凶杀?
帕特里希哑无庸置疑地知道是同一只罪恶的手杀害了这两位老人。但是确切的目的是什么?为了什么了不起的暗帐吗?野人是大型犯罪团伙的代表呢?还是仅仅是一个杀人的工具?她很想知道这一点……为达此目的,只有一个办法……
在双重罪行发生的第二天下午,帕特里希娘被亨利·阿莱米召到了《警探报》的总经理室。做为吉姆·马克·阿莱米的儿子和继承人,他接了班。
年轻女人看上去没有一点激动,她应邀赴约了。亨利·马克·阿莱米,三十岁。帕特里希娅已经有好几年没见他的面了,她发现他已经完全成熟了。同时她还认出了她过去早已熟悉的面庞。但是,所有的激情在她的身上都已经死掉了,就像在他的身上一样。他们像两个陌生人一样地交谈着。
“小姐,”年轻的经理说,“我的父亲的私人记事本上的最后一句话是与您有关的:‘帕特里希娅……有个性、激情和组织能力。副经理的位置完全适合于她。’”
他没有看年轻女人,继续说:
“我将尽一切所能来完成我父亲对您的安排意见……只要,当然啦,这要与您的意愿相符合……”
帕特里希娅同样有保留地回答道:
“我以为,先生,我为报社效力的最好方式是,全身心地去为您父亲报仇雪恨。几个小时后,我就要去法国了。我已经在‘法兰西岛’号船上订了位。”
亨利·马克·阿莱米做了一个感到惊讶的动作。
“您要去法国?”他大声问道。
“是的。根据您父亲所说的某些话,我可以断定他曾打算在近期内自己去法国一趟。”
“那又怎么样?”
“那么,我以为这次法国之行是与马克·阿莱米先生之死一案有关联的。”
“您有证据吗?”
“没有确凿的证据。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想法。”
“而就在报社最需要您的时候,您却做出了如此重大的决定,就凭一个简单的想法吗?”亨利·阿莱米有点嘲讽地强调着。
“为了行动,人们往往不得不顺从自己的直觉。”帕特里希娅十分平静地解释道。
“可是您要和警方取得一致意见呀。”
“我不认为有此必要。我不可能为警方提供任何有用的情况……”
沉默了一会儿功夫。
“您有钱吗?”亨利·马克·阿莱米继续说着。不管他愿意与否,年轻女人的决定还是感人至深的。
“预支的两千美元。是您父亲拨到我在出纳处的帐上的,做为我今后工作的预支。”
“这不够的。”
“如果为了取得成果我需要一大笔钱的话,您将会被通知到的,先生。”
“我相信。再见,小姐。”
帕特里希娅刚退出来,一个未经通报的年轻女人就跑进了总经理室。她漂亮、浓妆艳饰,穿着丧服仍显出了雅致,她像一阵风似地从帕特里希娅身边擦过,连看都不看她一眼,然后喊叫着投进了亨利的怀中:
“我的新大衣,亲爱的!你觉得怎么样?现在是服丧期,对吧?”
这是亨利·阿莱米的妻子。
时间到了。帕特里希姬登上了“法兰西岛”号船。她独自一人。一位女友将在两三周后,把她的儿子小罗多尔夫再带给她。
这次航行马上为这位年轻女人提供了很好的休息机会。她孤独地呆在陌生的旅客之中,船上的恬静生活在她身上产生了无可抗拒的良好效果。人的一生中的某些时候,只有当闭上眼睛时才能看得清楚。大海带给您的这种泰然从容,正是人们在某些心绪不宁和犹豫难决时所特别需要的。
头两天,帕特里希娅没有离开她的包舱。她的包舱在走廊的尽头,左边没有一点声响,右边也没有一点响声。“隔壁的旅客从来不出舱门,总是躺在床上。”客轮服务员这样告诉帕特里希娅。
可是,在第三天,她在从甲板上散步回来后,发现她的旅行袋和所有的抽屉都是乱糟糟的,有人到她这里来翻东西了……谁来翻的呢?要找什么呢?
帕特里希娅让人检查了一下扁插销,这扇舱门的两边都闩住了。它们没被碰过,锁也是转了双圈的……不可能有人来过。可实际上确实有人来过了。
转过天来,同样的闯入,同样的乱翻又发生在帕特里希娅的包舱里。她不能再犹豫了。有人趁她不在时进来过。谁呢?又一次地,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了找到线索,她加入到船上的活动之中,以便观察旅客们。她中、晚餐都去餐厅吃饭。她到甲板上去散步,出入于沙龙……听着……观察着……不,她不认识任何一个人……
可是对她包舱的搜查和翻动仍在继续。帕特里希娘向船长投诉了,后者告诉了负责搜寻工作的船上警长,让他安排人进行监视。
监视和搜寻工作一无所获。但是她本人通过调查,发现船上一只大米粉罐子漏出的粉末上留下了脚印。这个迹象向帕特里希娅揭示出:闯进她包舱的人是从隔壁过来的。这间包舱是由一个名叫安德莱伍·福伯的人占用的。安德莱伍·福伯?……帕特里希娅根本就不认识他。可是在十分担心、万分惶惶不安之中,她认为这个名字的背后隐藏着“野人”这个家伙……或许是那个在《警探报》社的楼梯平台上把“野人”打翻的人呢……谁又说得准?是他把帕特里希姬救出来的。
怎么才能摸准情况呢?既然隔壁的旅客从来不出他的包舱。步。
她决心要弄清楚令她不安的这一疑团,她让警长陪同着一起去拜访隔壁包舱的旅客。警长敲了门,进行交涉,最后利用他的权力,把帕特里希娘带了进去。
帕特里希哑看到了神秘的旅客,惊讶得叫了起来。
“怎么,是您?亨利……”
她请警长让她独自一人跟这间舱里的客人呆一会儿。
亨利·马克·阿莱米,在警长在场时,还控制着自己,可是,当他独自和年轻女人呆着时,自他们在报社见面时就戴着的无所谓的面具掉了下来。他面色惨白,慌乱无主。他跪在了帕特里希娅的脚下,供认了一切。
他爱她。他从来都没中断过对她的爱。他哀求她对他那不负责任的抛弃给予原谅。没有她,他无法再活下去。
“我很嫉妒。”他气喘吁吁地结束道,“我很痛苦。这次动身是什么意思?为我父亲报仇雪恨?这只不过是个借口!这是在撒谎。您不是一个人走的,帕特里希娅!您跟一个您爱的男人一块走的!他是谁?我一无所知?但我会知道的!我要从他手里把您夺回来!没有比您更重要的了。我的婚姻是一次疯狂。我爱您!我忍受不了看着您跟别人走!我应该杀掉您!我无法忍受您的背叛!”
在这些不公正的指责下,帕特里希娅惊呆了,她感到愤慨:
“至于背叛,这是您干的事,亨利!我是委身于您的!我把自己全部的爱都给了您!我只是为了您和我们的孩子在活着!可是您把这一切都毁掉了!所有这一切都毁于一旦,没有理由,没有任何解释。在一张小纸条上只有一句话:‘永别了!’您说要杀掉我?……可是,如果没有罗多尔夫,我早就死了!原谅您?休想吧。不过,我可以对再也不放在心上的残酷的过去给予原谅!也可以对一个已经从头脑中抹掉的和根本就不再把他放在心上的、冷漠的人给予原谅!”
她非常地坚决,又很倔傲和毫不留情。亨利·马克·阿莱米极力保持着冷静。他站了起来,答应她当天就换客舱,而且不再打搅她,还说一到了欧洲,他就马上再返回纽约。
“您应该去管理您的报社和照看您的妻子。”帕特里希娅近乎命令地说。
他耸了耸肩。
“不,报社让我厌倦。这是超过我的能力的。编辑们集中在一起,他们会干得比我好。我已经在出发前交出了权力。我已经把所有的善后工作都解决好了……”
“那么您的妻子呢?”
“当我真正了解了她之后,我讨厌她。她非要把我从您的身边夺走。这是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自私、浅薄,而且非常任性!”
“您的位置是在她的身边!因为您已经娶了她!您应该让她幸福!这是您的职责!”
他辩驳着、哭泣着,重又开始恳求她。当看到她无动于衷后,他最终答应了她向他提出的一切。
“一个懦夫,一个没有主见和三心二意的人。”帕特里希娅回到自己包舱后,这么想着,“我当初怎么会上当受骗到这种程度呢?怎么会把他这么一个人看成是一个正直的和值得爱的人呢?……”
亨利·马克·阿莱米并不使她害怕。她这一夜睡得很安稳。
可是第二天早上,她得知夜间在甲板上有两个人在相骂打架。其中一个人把另外一个人扔到了海里。
那位名叫安德莱伍·福伯的旅客从那时候起就不见了。人们都相信他成了牺牲品。但是无人知道是谁把他从船上扔下去的。没有人是这次相骂打架的直接见证人。打斗者之一被扔进了大海,另外一个又隐匿了起来。人们在船员和旅客中徒劳地寻找着。这神秘人物未被揭露出来。
可是帕特里希娅断定——尽管没有证据——这个凶犯是“野人”。是他在杀害了父亲之后,又干掉了儿子的。她猜想“野人”一定混在了旅客之中。她认真地研究所有的面孔……可是怎么能够认出只是匆匆一见,而且是在特别危机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仔细看的人呢?
年轻女人尽管胆子很大,但她知道这是危险时刻,因为她的看法是经过认真推理的,和令人鼓舞的:有人在监视她。是的,那个曾经救过她一次的人,在必要时,还会再救她的,那么他也在这条“法兰西岛”号船上了?为什么不呢?他不是曾许诺要救她,要保护她吗?他不是最强大的吗?想到她要面对一切可能的攻击,为了保护好自己,她像对待有用的护身符一样,在脖子上挂上了他给她的那只小银口哨。只要一有情况,她就叫他,他也就会来的,她对此坚信不移……
现在,她心里非常踏实,她可以在宁静中度过剩下的旅行时光了。没有任何事发生。像野人一样,她的拯救者就躲在她看不透的阴影里。
到达后,在登岸的栈桥上,她就站在他们的迎面,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让她能够在离船登岸的旅客中辨认出这两个人中的任何一位,可是他们却在她的记忆中占据了如此重要的位置。一个是险恶、粗俗,令人生畏、并且有着执拗的、粗暴的和胆大妄为的激情的人;另一个则是果敢、友好和强大的人。她信任他,有他在,她就再也没有恐惧感了,因为他答应救助她并保护她。
帕特里希哑的方案是建立在以下的推理上的:
吉姆·马克·阿莱米的伟大而神秘的事业决定了他要做这次到法国的旅行。那么,野人,杀害他的这个人——就是他,这一点不容置疑——也要到法国去,这样做既可以躲避纽约警方的追捕,也可以继续他已经开始了的想要得到好处的行动。肯定地,在英格兰秘密地离船之后,他想走另外一条路到法国来。于是帕特里希娘在勒阿弗尔租了一部汽车,开到布洛涅,然后到加来,为的是监视从大不列颠来的旅客在此登岸。
傍晚时分,在加来,一个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