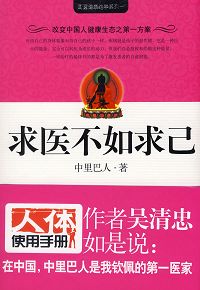不如安心做鸳鸯-第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侍?”
秦渠眉哑然失笑,挟了一箸烩鸡丝送进口中,再目不转睛瞧她一会,眼见着她由羞窘而怒,倒全没了平日的愁绪,心下也是极为高兴,不禁瞧了又瞧,将谢描描倒的那碗酒喝的涓滴不盛。
谢描描在他未进来之前已经偷喝了半坛酒,此时已有醺然之态,大脑一时里没有管住嘴巴,讽道:“不过喝了一碗酒,姐夫怎么像八百年没喝过酒似的?!”
本有讥诮之意,岂料那人满面笑意又斟了一碗酒,点头道:“酒逢知已千杯少,为夫虽一介武夫,哪有整日吃的醺然欲醉的道理?说起来,为夫还是半年前与君老弟畅饮过一回,只是这小子听说回家向意中人提亲去了,这半年没有他的消息,不知道是不是跟我一样娶妻生子去了?”
谢描描哪管他口中君老弟是哪个?只是瞪了他一眼,但难得见他哪如此兴致,且近来瘦的可怜,不知为何,心下一软,那恶狠狠的调子不由软了些,反驳道:“姐夫说笑了!你这哪里是娶妻啊?老婆都跑了,也不去追,还想着生子呢?!不是喝醉了酒说糊话吧?”
秦渠眉笑意盈盈又喝尽了一碗酒,只盯着她笑,缓慢的搛了块鹿肉喂进口中,慢吞吞道:“老婆跑了,总还是有人生的!”那目光毫不客气在谢描描身上扫来扫去,笃定而霸道。
谢描描只觉一阵头晕,猛然站了起来,怒道:“反正不是我!”说完了几乎要懊恼的咬掉自己的舌头——瞧瞧我,都说了些什么呀?
她双手捂着自己热辣辣的脸庞,不用想也知道红的很彻底,偏偏屋内再无旁人,她只觉浑身燥热,摇摇晃晃挪过去将窗子打开,呼啦啦一股冷风吹进来,只吹的靠窗的案上纸张哗啦啦响,也不知将秦渠眉刚拿进来的什么东西给吹下去了两本,她倒不曾费力去捡,只看窗外浅月如钩,月华成霜,有溯风侵骨,可是背上似乎有道视线要将她炙穿,含意不明,令她不敢一想再想。她只好借机蹲下身去,将桌上刮下去的两本书拿上桌来,凑近了细看,才发现是两本帐簿,为了急于将自己从这种窘境中解救出来,她随意翻了翻,微讽道:“这种帐目也要庄主您老人家过目吗?莫非贵庄的帐房都是吃闲饭不干活的?不如你雇了我来替你管帐?”
秦渠眉这下大大惊异了一番,不成想她居然还有这份本事。后知后觉想起来今晚自己尚有一大堆帐目要核,苦笑着揉揉眉心,道:“帐房王先生老母亲去世,他去奔丧了。近日外间事务急需要一笔银子,我这才准备看看帐,看从哪里挤一笔现银出来?!”这确是实话,谢描描每日足不出户,自然不知山庄外早已设了粥棚,几乎涌来了几千灾民,庄中闲散人员,除了回暖园与紫竹园两处侍侯的下人,别处的下人多数已去了庄外帮忙安置灾民,更有庄中护卫带了银钱去别县购置草药。现在虽天气寒冷,积雪未融,也不容易发生瘟疫,但若天气眨眼转暖,便防不胜防了。因此秦渠眉总觉得早作准备,有备无患的好。
他略微点点头,道:“那书案左手下面的格子里放着算盘,桌上有纸笔,若要我雇你,且先算一本帐来试试?”
谢描描敏感的从这话中嗅出了一丝怀疑与宠溺,更激起了她的好强之心,立时扶着桌案坐了下来,摸到了算盘,将帐本凑近了琉璃灯盏旁,立时噼叭啦碰珠如雨,手势竟是极为娴熟,虽眉眼饧酥,但大脑无比清楚,教一旁秦渠眉目瞪口呆,不能置信。
谢描描见得他居然真正呆住,更是得意一笑,算珠拨的飞快,酒意醺然,便如同金算盘老爷子坐在谢家帐房之内一般,心无旁鹜,专心致志算了下去。
恨无休
ˇ恨无休ˇ
回暖园内,秦母一早起床,便得到小僮来报,说是庄主已将帐房之事交予少夫人打理,现如今少夫人坐镇帐房,凡银钱支使,皆有少夫人作主。秦母当时听了,不过唇角露出来一点笑罢了,待得那小僮出去以后,一把便将榻几上的一套团花斗彩茶具给推了下去,茶水四溅,哗啦啦碎了一地。
苏宁过来请安,见得姑母发了大火,吓得一跳,上前连连拍着她的背,替她缓气,边柔声劝慰:“一大早的,姑母作什么发大火?水米未进,也得小心身子,凭是谁,也不值得为那起小人气坏了身子吧?”
秦母气怨难平,手指着紫竹院,颤声道:“我这是做了什么孽?自小养大的儿子,翅膀硬了就要想着掌权,我不过是想着他尚未成亲,替他管个几年,到头来两眼一闭,这家业还不是他的吗?既是他非要管,我便给了他!好!这还未过几年,新娶的媳妇还未满一个月,便将掌家大权给了那女人。从来温柔乡是英雄冢,我倒要看看她能将这家掌成什么样?”
苏宁闻听此言,嘴里发苦,还得柔声哄劝:“姑母且消消气。看那位的样子,除了会一点子武功,也是个毛毛燥燥的人物,针线女红就不肖说,这些都是细致活,最宜修身养性的,她竟一样也不耐烦学,这帐房之事从来得精细之人来执掌,不过三五日,我看她就得撂挑子不干。表哥这不是新娶吗?自然宠着她,等厌了她,还怕没机会让她灰头土脸?”她五岁上家道败落,父亲将她送进了紫竹山庄寄养,苏氏一门也多年依附这位姑母过活。她这位姑母秉性素刚,与过世的老庄主常常针尖对麦芒,不欢而散。
秦渠眉自小被父亲带在身边贴身教导,与这位母亲素不亲近。他敬父亲若天人,偶然与母亲呆在一处,母亲对于父亲,也是颇有恶言,他虽不曾反驳过母亲,但过后学武只有更用心,更为忙碌,十来天都难见母亲一面。便是他的亲事上头,双亲也是吵的颇为激烈,秦母一意要儿子娶了侄女儿苏宁,说是这丫头自小在自己身边长大,嫁得远了也舍不得,且是个温柔体贴之人,与眉儿也算得青梅竹马,结为夫妇定是美满良缘。秦父虽嘴上未说,但自苏氏败落,他这位妻舅不但不思上进,反而酗酒赌博,这些也就罢了。但秦氏一味的宠着弟弟,早些年秦父醉心武学,紫竹山庄皆是她当家,银钱土地店铺给了其弟不知多少,皆被这位妻舅给败的精光。老庄主眼见再要妻子管下去,连紫竹山庄祖宗基业也要给这位妻舅败光了,方才收回了妻子的掌家之权,自己管起了帐务。他一生夫妻情份之上始终不曾圆满,连带着对苏宁也无甚好感,总怕着有一日儿子重蹈自己覆辙,一生抑郁。所以无论如何,儿子的妻室得外聘,决不再与苏氏有任何瓜葛,这才有了秦顾联姻。
老庄主过世之后,秦氏自为儿子年少,这家业还要自己来掌,老庄主还未下葬,她便重新坐镇帐房,核算家业。秦渠眉痛失亲父,消沉月余,秦氏掌家之余,每日亦遣了苏宁前往紫竹园为秦渠眉炖一些汤汤水水,照顾他的身子。她与老庄主结缡几十载,成亲第一年在一次争吵过后,便赌气搬出了紫竹园,几十年再未踏足。如今见着儿子并未推拒苏宁的刻意亲近,心下甚慰,暗道:你这老不死的!一辈子有多长?儿子还不是我生的?能越过我去?只等守孝期满,我必退了顾家的亲事,宁儿进了门,一家三口和和乐乐的过!
可惜事与愿违,三个月以后,秦渠眉便极为生疏客气道:“父亲已经去了,还请母亲节哀顺便!都是儿子不孝,要母亲一把年纪还要来操劳庄中事务,如今儿子已经成年,若再让母亲累出好歹来,让儿子如何向九泉之下的父亲交待?——宁儿,还不快扶母亲去回暖园歇着?”
苏宁近日与表哥秦渠眉还算相处愉快,无论她做了什么膳食,他皆入腹,虽面上仍是冷冷的,但今日这声“宁儿”可谓亲昵。她十几年来蜗居紫竹山庄,对这位表面冷淡的表哥早已情根深种,且姑母的盘算她也清楚,近日常想终身有靠,目中柔情蜜意,时时凝注在秦渠眉身上,此刻唯秦渠眉马首是瞻,听了他的话急忙上前劝导秦氏:“姑父刚刚过世,表哥伤心消沉,姑母强撑着掌管山庄事务,如今表哥欲重振家声,正是姑母歇息之时,孩儿这就扶姑母回房歇息。姑母这些时日伤心劳累,可不能再操劳下去了!”她这话却正是暗示秦氏,老庄主初逝,连作儿子的都伤心悲痛,无力掌管家事,而她骤失鸳侣,合该比儿子更为悲痛才是,怎么能在此时掌管庄中事务?这不是给有心人猜度么?
秦氏想想,也有道理,只得随苏宁回房。
她不过想着,等这段时日过去,再作道理。儿子总归是自己的,应了解自己的苦心才是。哪知道秦渠眉虽是个言语寡少的性子,继任庄主以后,凡事再容不得她插嘴,便是苏宁之父常常来打秋风,也再比不得往日老庄主在世,虽厌烦这位妻舅,但总还有一两百银子好打发。这位外甥却比其父吝啬十倍,每次最多十两,少则五两也是有的。苏宁之父每次出了山庄门必是指天骂地,将秦家祖宗十八代问候个遍,连过世的姐夫亦不放过。下次走投无路之时,还是腆着脸前来。
自秦渠眉掌家,秦氏亦是有心无力,再不能随意贴补弟弟。有时候其弟怀揣她房中古董出来,还未出得山庄,便被庄内暗卫截留,秦渠眉必带了古董亲自送回母亲房中,末了淡淡道:“舅父好赌成性,苏氏百年家业被他败个精光,母亲若是一意接济,他必定食髓知味。莫非母亲也要眼见着舅父将我秦家家业败个精光方才罢手?这古董虽值不了几个钱,但天长日久,也不是一件两件的事情!”
秦母自此知道这位儿子虽寡言,可比自已那过世的老伴还要难缠。老庄主是火爆性子,凡事发完了火总还顾忌她三分,儿子却不同。这些年她极少尽心照顾过她,眼见着他已由那娇软咿咿呀呀的小小婴孩长成了八尺男儿,挺拨如松,沉默如山,然而凡事他总自有主张,容不得她置喙。
三年守孝期满,她正准备着他成亲的一应物事,总还是人心难死,指望着与他商议一番,将顾家婚事退了,娶苏宁进门。苏宁年已十七,那段时日面笼红云,娇如春花,得了姑母暗示,早将嫁衣缝制妥当。那日她闻得表哥前来回暖园给母亲请安,她描眉画唇,打扮的极为精致前往姑母房内,还未进到门口便见福玉悄悄朝她摆手,示意她别闯进去。她好奇心起,暗暗贴在窗上听这母子二人说些什么。入耳的正是姑母的声音,“眉儿,母亲近日为你准备了大婚之物,眼见着你孝期已满,也该择日成婚了!”
“多劳母亲烦心了!只是不知,母亲将婚期定到了哪一日?”饶是秦渠眉那淡淡的声音里听不出一丝喜意,苏宁也只觉手足酥软,全身被巨大的喜悦笼罩,一颗心在腔子里跳的极快,几乎要从口里跳出来似的。
“眉儿啊,为娘想着,过几日你派人将宁儿送回苏家待嫁,嫁期就定在一个月之后。她虽自小生长在山庄之内,但出门子还是得从娘家出来,你舅父日子艰难,宁儿的聘礼你一定得办的隆重一点。到时候,宁儿就算是堂堂正正的进了秦家门,娘也再无遗憾之事了!”姑母难得慈音软语,她话音方落,却听得椅子“吱呀”一声,似乎是有人重重的站了起来,耳边却听得表哥道:“母亲莫非睡糊涂了不成?儿与威武城主的女儿早有婚约,顾家女儿为了儿的孝期,年已十八还未成亲,要娶也是娶顾家女儿。儿的记性一向很好,倒是不知道自己何时与表妹还有婚约?”
仿如兜头一盆冰水,将苏宁泼得全身冰寒,她忍不住全身哆嗦,差点就地扑倒。福玉忙上前,将她扶了一把,她全身倚在福玉身上,居然还能发出声音来,颤声道:“扶我回房!”指甲死命的掐在手心里,在福玉的扶持之下一步步挪回了房,两眼一黑便倒了下去。
那时候秦母在房内张口结舌,半日说不出一句话来,只久久盯着儿子,目光说不上是绝望还是痛楚还是恨意,她的儿子,从来不曾大声对她吼过一句的儿子,客气礼貌,此时也不过温温淡淡道:“既是婚期已定,儿这就派人往威武城送聘礼,将顾姑娘娶了进门,一切还要劳母亲操劳了!”
转眼至今,顾氏是娶进了门,虽有貌而无品,她那昏了头的儿子居然让顾氏掌家?!秦氏气得早饭都吃不下去,末了吩咐苏宁:“宁儿了,一会你去帐房领五百两银子来,我倒要看看这丫头给还是不给?你亲自去看看,她是坐在一旁当少奶奶呢还是亲自核算帐目?哼,我料定她也没这等本事!”
苏宁柔声应答,摊开双手来,手心各有四个白色弯月的印子,却是那日听闻表哥要娶顾氏,她激愤之下攥紧了拳头,过后才发现,指甲深深扎进了掌心,皮破血流,伤口虽已愈合,但疤痕经久不褪。
怎堪怜
ˇ怎堪怜ˇ
苏宁来到帐房外的时候,已经过午。但见门外立着两三位管事的婆子,正屏神凝息,见得她来,不冷不热行了礼,便立在了原处。只因其父的缘故,她虽得老夫人眷顾,山庄里略有些头脸的仆妇们原先还以为她会成为庄主夫人,也曾跑来巴结过一阵子,眼见着顾无华进了门,她掌管山庄之事成了黄粱一梦,拜高踩低原是这些人擅长的,那些人再见她眼神里未免就有了轻视之色。她心内苦涩,却也不能同这些愚顽之辈争论些什么,自跌身份,只得在帐房外扬声道:“表嫂可在里面?”
有人掀帘而出,正是表哥房内的丫头敏儿,忙忙道:“表小姐快请进来吧,少夫人有请!这大冷的天,有什么需要,传个话让奴婢们跑一趟就得了,表小姐巴巴的来,万一冻坏了身子?”言语恳切,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苏宁也堆了笑容道:“怎敢劳烦姐姐?听说表嫂坐镇掌房,以后掌管偌大家业定是不得闲,我也整日闲着无事,还不如有时间自己走动走动。”一弯身从敏儿掀的帘子里钻了进去,举目去望,帐房之内偌大的书案之上码着高高两摞帐本,只听得算珠噼哩叭啦直响,却不见后面有人,再细看时,方见着帐本之上冒出来一点墨发,上面簪着只白玉雕梅花的簪子,别的五官,一概不知,唯有脆亮的声音从那两摞高高厚厚的帐本之后传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