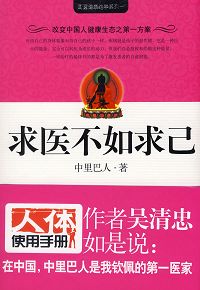不如安心做鸳鸯-第3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掌柜的吓的扑嗵一声跪倒在地,几乎要痛哭流涕,大呼冤枉:“谷主,并不是小人要拿了次货来充门面,而是谷中皆是珍奇之物,这些个寻常富贵人家瞧着是极好的东西,到了谷主那里也觉得是瑕疵品……”
叶初尘冷冷一笑,不为所动,“啪”的一声将盘中东西尽数摔在了地下,指着掌柜的鼻子骂道:“个个以为我年轻可欺,随意的将些旁枝末节的东西拿来糊弄人,指望着小爷就信了你等不成?闻蝶谷的规矩难道是拿来写着玩的吗?”
掌柜的吓得瑟瑟发抖,偏谢描描不知死活,趴在一摞帐本后面算盘照旧打得山响,间或长长的打个呵欠,只当叶初尘在替自己唱催眠歌曲,更兼着恨极那掌柜的诌媚之语,他那句:“夫人……”之语令她颇为刺心,只暗暗发誓非要在帐目间置他于死地,也就不再计较口舌之利了。
她哪成想自己那个呵欠被叶初尘瞧了去,那人忽尔转了脸色,朝她笑道:“媳妇儿可是对这事可还有异议?”
谢描描一路走来,无数次领教了此人的可厌可憎,知道自己越反驳的厉害,他定然越是开心,更要拗着她叫下去,莫如由得他去,等他厌烦了,自然不会再胡乱叫下去。当下摇了摇头,又埋头下去算帐了。
叶初尘这才转头回来,对着那掌柜的极是淡漠的一笑,似恼似恨,指着掌柜的厉声道:“你们这些人,不忠心办事也就罢了,只紧盯着上面的一举一动,专想了法子来加意诌媚。别告诉我你与伍仁政的客栈掌柜并无联系!我不妨告诉你,他亏空的厉害,拿了公中的银子去中饱私囊,已被我革了职在厨房作杂役,莫非你还想去伍仁镇与他在厨房里作伴?”
那掌柜的早吓得汗流浃背,不敢多语,目光只一遍遍往谢描描处而去,盼着这位“夫人”能看在他好意殷勤的孝敬之下,救自己于水火。
他哪里又料得到,谢描描正恨极了他,正在寻思置他于死地呢?
因此后来,当这掌柜的亏空公中的银两被查了出来,谢描描见得这得云楼的生意多是此间的富贵女客,只觉颇为有趣,更想起自己极是年幼之时,姬无凤每日打扮得花枝招展,亦与人谈生意到好晚,那时候她便极是艳羡其母能够随心所欲,如今放了大好的机会在眼前,岂肯轻易错过,苦苦求了叶初尘赏她半月假期,在这得云楼充任一回掌柜的。
叶初尘见得谢描描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虽然打扮很是古怪,道姑与首饰店简直全无交集之处,也由得她去胡闹,谢描描这位掌柜的,第二日便走马上任了。
她这日从自己包裹里挑了件簇新的长衫,将道姑头挽得一丝不乱,坐镇店内。这姿态被楼上关斐瞧了去,直笑得打跌,偷偷指着她一副全神戒备的样子给叶初尘看,捂着肚子道:“这丫头哪里像个掌柜的了?简直是银楼请来的打手嘛,腰上还带着把长剑,一副要杀人的样子!”
叶初尘刚刚起床,慵懒的目光朝楼下的谢描描扫了一眼,漫不经心道:“苗子倒是个好苗子,只是胆子太小,全无杀气,要不然岂能让那刀客沾了便宜去?”摸下巴沉思一回:“什么时候杀一回人胆子便会大了。”漫不经心回房去了。
只留关斐在原处替谢描描暗暗捏了把冷汗。
簪红萼
ˇ簪红萼ˇ
彼时,谢描描做掌柜正做得满心喜悦,一个早晨接待了两位女客,也谈了一笔小生意,哪里知道她又被人算计了去。
午饭是与叶初尘关斐同席,菜色颇为丰富,她心情愉悦,也顾不得这二人一阴一阳的目光,多添了一碗饭,略微回房歇了歇,便又尽职尽责下楼去作掌柜的。
叶初尘全然无法理解她这喜悦从何而来,拨着碗中米粒,颇为疑惑:“关斐,这银楼的掌柜当起来真的很有趣么?”
关斐侧头想上一回,也是大奇:“按理说,这前来银楼的应该全是女子才对吧……”后面的话他含了半截,生生忍了下去。
可惜叶初尘听话听音,已教他听出了弦外之意,立时扒尽了碗中的米饭,含含糊糊道:“我听着也很是有趣,不如我们一起下去看看?”也不管关斐的意愿,拖着他便下了楼。
二人殊不知,此时待在二楼雅间的谢描描正接待了一对年轻的夫妇,苦不堪言。
得云楼高三层,一层大堂只摆些普通货色或者稍贵一些的首饰,另有伙计若干打理。二楼环境却是幽密绝雅,另设几处包间,专门接待贵客。
这日谢描描吃过午饭休息之时,便有伙计上楼来敲门,只道楼下来了一对年轻夫妇,那男子要为妇人挑一些贵重的首饰,请掌柜的下去接待。
谢描描略微收拾一番便去了二楼,方推开包间的门,便呆立在了门口。只见门内女子坐着,男子正立在她身旁,侧着头不知道软语说些什么,许是听到了动静,此时恰抬起头来,竟然是一对熟人,顿时教她进也不是不进也不是。
房内的男女见得她这打扮,也是一愣。那女子揉了揉眼睛,再看,似不能置信般道:“谢描描?……夫君,莫非我认错人了?”
她身旁的男子也是张口结舌,求证似的去瞧她,点头道:“我也瞧着像!”
谢描描当即有拨腿即逃的冲动,心里似被什么东西大力撒扯了一般,一瞬间摇摇欲坠。过去的时光已然不可追回,但却无时无刻不令她倍加珍惜思念,只盼着某一日能再次知道那人的讯息,只是,却决不是这两个人。
眼前的人,正是苏宁与海非川。
她果断的正欲拨即逃走,身后响起得云楼那负责任的小伙计的声音:“掌柜的,你怎么不进去了?里面的这位海爷正要帮他的如夫人挑一些首饰。”
如夫人?
谢描描一怔,唇边缓缓绽了一抹笑意,也知今日不可能逃得开,便大步走了进去,摆出一副生意人的面孔来,道:“还请两位稍待,伙计,去将楼里最好的饰品端了来,让两位贵客挑选。”
苏宁自离了紫竹山庄,便发誓此生不再与山庄内的人有任何瓜葛。只是江湖之中早有消息灵通人士,紫竹山庄少夫人在镇江丢失,已是奇闻一桩,如今已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只是打死她都想不明白,这失踪的谢描描为何会出现在东海之境?不但作了银楼掌柜,且打扮的不伦不类,简直匪夷所思。
只是当初她离开山庄之时,未曾料到海非川家教极严,父母对这般贸然相跟着送上门来的女子,纵然有大笔嫁妆,也不肯认为儿媳,她只得屈身作妾。她当日拒绝了秦氏的好意,只满心以为自己必定做得了东海门的少夫人,岂料人算不如天算,到如今不过得了个小妾的名头,且极不得公婆喜爱,每日里守在婆婆房内立规矩,日子苦不堪言,若非因着海非川对她还算体贴,早已心生厌弃之意。
好不容易半年前有了身孕,这才松了口气。便是海非川也在闺房里对她赌咒发誓,等她这胎生了儿子下来,定然去求了父母将她抬了作正房。她正在心生幻想之际,紫竹山庄传来口讯,秦氏病逝。
原来她还赌着一口气,等自己有一日作了东海门的少夫人,携夫带子前往山庄见秦氏,也好教她看一眼自己美满和谐的婚后生活,岂料那个人,从小教她养她,一朝不见便天人永隔,教她背着海非川流了许多莫名的眼泪,连自己也不知道是因着什么。
过了没多久,海非川的父母便为他订了一门东海大家闺秀,据说那未过门的新媳不但貌美,作姑娘之时便是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主。东海门中众人皆在背地里议论她这位与着六个月身孕的小妾未来的命运。她虽背地里听到了好几回,也唯有偷偷饮恨暗泣罢了。
海非川这些日子见她恹恹不言,且自己食言在先,未免心有愧意,请示了父母带着她出来散诞几日。这日恰巧路过得云楼,便起了补偿之意,带着她进来挑些随身之物。
此时不巧与谢描描在此间碰面,二人皆是心有鬼胎。一个正为了大妇进门而烦恼,一个却是为了自己身份行踪而烦恼,一致的选择了前事尽忘,只作了一回普通客人与掌柜之间的交易,谢描描由得那伙计将店内最好的首饰拿来了,苏宁挑了一串极是红艳的珊瑚手串,更挑了两支金钗,明铛玉佩之类。更替婆婆左挑右捡,最后才挑了上好的翠玉簪子一个。
伙计正拿了这些东西在一旁包起来,苏宁挺着七个多月大的肚子在一旁指指点点,包间的门猛然被推了开来,叶初尘揪着关斐的衣领立定在包间门口,他朝里一探,先朝着苏宁绽出一个微笑来,直让她看呆了眼去,这才对着已经全身僵硬,愣愣立在苏宁旁边的谢描描念出了这些日子以来极为熟稔的词:“媳妇儿,忙完了没?”
一刹时,谢描描只觉手足冰凉,血液倒流,杀了叶初尘的心都有!
可惜力量悬殊,她又向来是个趋吉避凶的人,且在苏宁面前动手,若再被叶初尘所制,当场占她便宜,怕是更要让她羞愧而死,她岂能容能种情形发生?此时被气得狠了,也唯有颤抖着手,语不成声,咬牙切齿一字一顿道道:“叶初尘,你若是很闲,麻烦去厨房看看午饭!”
叶初尘扬起他那张倾绝的脸来,疑惑道:“咦,媳妇儿,你莫非得了健忘之症?刚刚吃完午饭一刻钟,你就饿了?”
谢描描顿时全身都要颤抖起来,半晌才找回了自己的声音,从牙缝中挤出了几个字:“那就麻烦你去瞧瞧晚饭!”
苏宁与海非川早在叶初尘叫出“媳妇儿”这三个字时,已经惊变了脸色,若非碍着谢描描那张极为难看的脸色,早扑上去揪着叶初尘问个不休。自苏宁前往东海门,虽说不过是一个小妾,到底与紫竹山庄也算得姻亲关系,两家虽距离遥远,也偶有讯息。秦渠眉的夫人失踪,自有无数人关注。便是连海非川私下也曾叹息了好几回:“你那个表嫂谢描描,据我看来,究竟也算不得好女子。也不知道秦兄为她着迷却是为着哪般?”
苏宁又向来不中意谢描描,当下将谢描描替嫁之事解说一番,直让海非川击节而叹:“也难为秦兄这般忠厚人,吃了这一个哑巴亏,竟然还对那谢描描体贴备至,真是难能可贵!”
这会瞧着谢描描虽打扮的不伦不类,但却与这样一个男子纠缠不清。那男子一口一个媳妇儿,便是连海非川也要禁不住气愤,指着谢描描道:“这位兄台,在下乃东海门的少门主,却是识得这位嫂子的,兄台莫不是被她给骗了?”
谢描描如被雷击,当下呆若木鸡,只瞧着眼前荒唐的一幕继续下去。
叶初尘见得这二人居然认识谢描描,且这位东海门的少门主居然在揭谢描描的老底,当下兴奋的点点头,想想又不对,连忙摇摇头,作出一副万分诚恳好奇的样子来,问道:“在下当真不知娘子有何事骗了在下。”
谢描描转过身去,默默看墙上一副兰草图,不再理这房内一干人。
海非川见这人竟被蒙蔽已深,自然气愤不已,对着背过身去的谢描描怒道:“秦少夫人,你这招可用得极好啊!初时替嫁骗婚,觉得不合意了再使一招金蝉脱壳,你可知道这一年多来,秦兄找你找的好苦啊!”
谢描描身形摇摇欲坠,只觉这句话如一把利刃一般立时击中了她的心脏,而她却无力招架,只能眼看着自己那颗心被切得七零八落,疼痛如巨大的潮水四面八方涌了过来,将她瞬时淹没——她沉在了水底,且喜且痛——如果海非川没有说错,这一年多以来,那个人一直没有放弃的在寻找自己……她默默的握紧了拳。
海非川见得她面壁而去,只当她愧不能言,当即一口气不停,将谢描描如何嫁进紫竹山庄,又如何奈不住寂寞,离弃了秦渠眉,那人苦苦寻找一事详加解说,更引得苏宁流出几滴泪来,哀哀泣道:“表嫂,你既然不喜欢表哥,另起再嫁之意,也该讨了休书才对。这般……这般……算什么样子?”
谢描描背着身,并不曾瞧见众人的脸色。她只极力的去看面前画里面的那株兰草,起先瞧着竟也颇有风骨,再瞧去却朦胧了许多,渐渐模糊不清,似雨天在那画上汪了许多水雾一般,她伸出手去,想将那画上不雾抹去,只觉一抹之下,那兰草图却平添了一道红痕,身后有人疾速闪了过来,将她那只手拉开了细看,惊道:“好好的怎么流血了?”再抬头之时不禁呆住了:“你……你居然哭了?”
这个人,正是平日吊儿郎当无一丝正形的关斐。
渐吹尽
ˇ渐吹尽ˇ
谢描描从来不觉得关斐是个好人。
但是那一日,关斐却板起了脸来,对着喋喋不休的海非川与苏宁道:“二位,得云楼是座银楼,闲谈他人之事,还请去茶楼,且不要当着别人的面指责。二位就算是那位秦庄主的姻亲,此类事情也还轮不到二位来置喙。难道秦庄主是三岁小儿,由得你二位随意指点不成?”
海非川梗着脖子,恼道:“这位小哥好不讲道理。在下不过一片好心,你怎能说出这一番话来?莫非你与这位谢家小姐也有些瓜葛不成?”
关斐板起脸来,喝道:“放肆!我家少夫人岂是容尔等玷污的?就算是她嫁过人又怎么样?只要我家少主喜欢,抢了回去又如何?”
苏宁见得关斐这般言语,早收了泪意,捂帕嫣然一笑,上上下下将谢描描打量一番,见她虽然穿着簇新长衫,但这样式怕是只有道姑才穿,再见她一丝不苟将发盘在头顶,横插着一根簪子,当真跟个小道姑无异,只觉这竟是自己近一年以来发生的最为畅意的事情,更是笑不可抑,指着谢描描道:“抢她?”
面前猛然靠近一张脸来,正是那唤谢描描“媳妇儿”的倾绝男子,将她也如法炮制,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且顺手在她面上摸了一把,反问道:“不抢她,难道抢你?”
苏宁虽挺着七个多月的肚子,还是禁不住红透了面颊。
却见得那男子伸出手来,简短吐出了四个字:“关斐,手帕!”
海非川眼瞧着苏宁被调戏,事发突然竟说不出一个字来,只呆呆立在一旁,此时见得那白衣男子伸出手去,名叫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