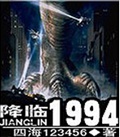大江大海1949-第2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驻扎处没有水源,部队就在城门口找到浅浅的一洼水,像是从地里渗出来的,红红黄黄的,极不干净,但是总比没有水要好。他们就喝这水,用这水煮饭。
二十一军的一个士兵,蹲在空旷处,草纸是奢侈品,没有的,他因此想找一块石头来清理自己。当他用力把一块冰雪覆盖的石头掰开时,发现石头下面竟是一只手臂,一只穿着军服的手臂,冻成青色的。
原来不是没有战壕,所有的战壕都被掩埋了。把战壕挖开一看,里头埋了七百多具尸体,是共军的。这沟里躺着的所谓共军,张拓芜知道,很多也不过是被拉来的农家孩子。挖出来的尸体,摸摸军服里的口袋,每个口袋里都有被雪水浸透了的家书和亲人的照片。
等一下,班长说,如果城内有战壕,那么城外就一定有护城河。
二十一军在城墙外应该是护城河的地方开始挖掘。
雪停了,大地凝结成冰,铲子敲下去,空空作响。天上没有一只飞鸟,地上没有一株树,唯一突出地面的是水塘边高高矮矮的芦苇,水塘被雪覆盖,芦苇在冬天里一片衰败,像鬼魅般的黑色断齿。
多年后,张拓芜读到痖弦的诗,他马上就想到盐城这一片孤苦寒瑟、万物如刍狗的冰封平原。
盐
二嬷嬷压根儿也没见过退斯妥也夫斯基。春天她只叫着一句话:盐呀,盐呀,给我一把盐呀!天使们就在榆树上歌唱。那年豌豆差不多完全没有开花。
盐务大臣的骆队在七百里以外的海湄走着。二嬷嬷的盲瞳里一束藻草也没有过。她只叫着一句话:盐呀,盐呀,给我一把盐呀!天使们嬉笑着把雪摇给她。
一九一一年党人们到了武昌。而二嬷嬷却从吊在榆树上的裹脚带上,走进了野狗的呼吸中,秃鹰的翅膀里;且很多声音伤逝在风中:盐呀,盐呀,给我一把盐呀!那年豌豆差不多完全开了白花。退斯妥也夫斯基压根儿也没见过二嬷嬷。
他们总共找到三千多具尸体,扔在护城河里。全是四十九军的国军,胸前绣着“铁汉”二字,是王铁汉的部队。因为冷,每个被挖出来的人,虽然面色铁青,但是眉目清楚,很多没有合眼,突出的眼睛对着淡漠的天空,像腌过的死鱼。这三千多具尸体,很多,大概也是十七岁。
原来二十一军这段日子饮用的、煮粥的那洼红红黄黄的水,是尸体混着融雪逐渐渗上来的血水。
拓芜的部队在重埋这些无名无姓的尸体的时候,也差不多就是吴阿吉、陈清山在凤山开始行军的时候。他们的班长说,走到中午就回来吃饭,所以什么都不要带。但是他们一直走一直走,口令让他们停住时,发现这是高雄港;一艘又一艘的运输舰靠在码头,等着送他们到中国的战场。
深冬啊,一九四六。
53,如要凋谢,必做樱花
阿吉、清山、拓芜都是一九二八年出生的孩子,他们的哥哥们,比他们大个几岁,早几年来到十七、八岁或二十岁这个关口,作出人生重大的决定。譬如比他们大五岁的蔡新宗、大八岁的柯景星。
蔡新宗的家在日月潭边的鱼池乡,柯景星是彰化和美人。他们二十岁时,碰上的不是改朝换代的一九四五而是战时的一九四二,台湾还是日本的国土,蔡新宗已经改名叫“藤村茂”,柯景星很快会改名叫“河村辉星”。
和多数的台湾孩子一样,蔡新宗和柯景星上学时,每天早上朝会由校长指挥,先向日本天皇的皇居遥拜,在敬礼注视中升起太阳旗,然后齐声唱国歌。国歌叫“君之代”,歌词优美,有中国“楚辞”的味道,虽然孩子们不学“楚辞”:
皇祚
皇祚连绵兮久长
万世不变兮悠长
小石凝结成岩兮
更岩生绿苔之祥
上课的时候,孩子们学“教育……谕”,一八九零年以天皇之名颁发的“教育……谕”,教导孩子们“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少年时,他们就会学“军人……谕”。那是一八八二年所颁,要孩子们效法军人精神,“尽忠节”、“正礼仪”、“尚勇武”、“重信义”等等,而所有这些品格锻炼的最高目标,就是效忠“天壤无穷之皇运”。
随着太平洋战场上的紧张,殖民地的思想教育转为积极。原来大家能唱爱哼的台湾流行歌,一首一首填进了新词,配上了进行曲的节奏,一一变成军歌。“月夜愁”变成“军夫之妻”,“望春风”变成“大地在召唤”。周添旺填词、邓雨贤谱曲的“雨夜花”,人们爱它的温柔婉约,从水井唱到市场,本来是在表达一个青春女性的自伤和自怜:
雨夜花,雨夜花,受风雨吹落地。无人看见,暝日怨嗟,花谢落土不再回。
花落土,花落土,有谁人通看顾。无情风雨,误阮前途,花蕊凋落要如何。
流行歌的感染力强,现在,“雨夜花”的旋律改谱,歌词改写,叫做“荣誉的军夫”:
红色彩带,荣誉军夫,多么兴奋,日本男儿。
献予天皇,我的生命,为着国家,不会怜惜。
进攻敌阵,摇举军旗,搬进弹药,战友跟进。
寒天露宿,夜已深沉,梦中浮现,可爱宝贝。
如要凋谢,必做樱花,我的父亲,荣誉军夫。
54,南十字星的天空
就如同弟弟们在三年以后会排队去报名加入国军一样,这些哥哥们在一九四二年努力地要报名加入日军。“陆军特别志愿兵制度”在台湾开始招聘。第一期,日本军部只招一千名士兵,却有四十二万人争取,还有很多青年陈上血书以表达为国牺牲的强烈决心;第二期也只开放一千个名额,涌来六十万个“热血青年”报名。那少数被录取的,荣耀了整个家族和乡里;不被录取的,还有人因为满腔杀敌抱负受挫,幽愤而自杀。
战事之初,台湾青年还没有资格当日本兵,只能当“军人、军犬、军马、军属、军夫”这个阶级顺序中的军属——军人的佣人,和军夫,为前线的士兵做运输和后勤补给。一直到一九四二年太平洋战争扩张到危险边缘,日本才开始在台湾征“志愿兵”。日本厚生省一九七三年的统计说,从一九三七到一九四五年,台湾总督府总共招募了军属、军夫十二万六千七百五十名,从一九四二到一九四五年则征募了军人八万零四百三十三人,加起来就是二十万七千零八十三名;二十多万个台湾青年中,三万三百零四个人阵亡。
台湾青年们被送到南洋战场之后,在潮湿酷热、传染病肆虐的丛林里,晚上望向星光闪烁的天空时,还会哼起熟悉的“台湾军之歌”:
太平洋上天遥远,南十字星闪闪光
黑潮溢洗椰子岛,波浪冲过赤道线
睨目企腾在南方
守护有咱台湾军
啊!严防的台湾军
历史芬芳五十年,战死做神尽本分
镇守本岛北白川,所传士魂蓬莱存
建立武功在南方
守护有咱台湾军
啊!严防的台湾军……
歌词中的“南十字星”,是南半球的北斗星,只有在南半球看得见,两串闪亮的星链呈“十”字在夜空交错,引人无限的浪漫怀想。
五十年以后,在婆罗洲长大的小说家李永平,后来回忆那段童年岁月时写到,自己的父亲曾说过,他听见日军行军时军鞋踏在地面上那沉重而整齐的声音,也听见日本士兵在慰安所喝得酩酊大醉时,大伙混声合唱军歌“月夜愁”和“雨夜花”,歌声带着浓浓的酒意和悲壮……
蔡新宗和柯景星就在二十岁前后,风风光光地加入了日军的队伍,要到南洋去做“盟军战俘营监视员”。他们在一九四二年七月到嘉义白河受基本军训。受训中有一个环节,让柯景星大吃一惊,就是学习如何打耳光。两排新兵面对面站立,互打耳光,打得重,打得准,才算及格。
一有了“军属”身分,少年们走在街上都觉得意气风发。有些马上就到日本军部指定的商店里去买了看起来像日本战斗兵的帽子,年轻稚气的脸孔对着店里的镜子戴上,觉得自己挺帅气,然后开心地上街闲逛。平常看见游荡的少年就要气势凌人叫过来教训一顿的警察,现在竟然当街向他们举手敬礼;少年心里充满了报效国家的激动和荣耀的感觉。
八月三日,这些经过短暂训练的台湾少年,告别了自己的父母兄弟;没有什么生离死别的沉重,他们踏着轻快的脚步出村,雀跃的心情比较像是参加团体郊游、正奔向集合地点的孩子。
从台湾的四面八方向南方汇聚,最后都到了集合地点,高雄港。
码头上,有很大的仓库,铁皮盖的屋顶。一艘货船改装的运输舰,靠在码头,正等着这些福尔摩沙的少年,送他们到南十字星空下的战场。
55,这些哥哥们
八月三号这一天,激烈的中途岛战役已经结束了两个月。在两天的战役中,日本损失了四艘航空母舰、一艘重巡洋舰,三百三十二架军机,三千五百人阵亡,日军从优势开始转向劣势。在太平洋的水域里,日本船舰随时可能被盟军的鱼雷、潜水艇或飞机轰炸。蔡新宗和柯景星所搭乘的“三池丸”,一驶出高雄港,就在黑浪扑天中一左一右以锯齿路线航行,避开鱼雷的瞄准。
其实,如果是空中轰炸,天上射下来的机关枪能穿透三层铁板,怎么躲都躲不掉。
一个月后,到了婆罗洲,也就是现在属于马来西亚的沙捞越,一个叫古晋的小城。少年们从这里各奔前程,蔡新宗被派到总部古晋俘虏营。他写了篇作文“战场的觉悟”,一笔工整的日文小楷,让长官惊讶万分,马上赋予他俘虏营的文书工作。柯景星分到北婆罗洲的纳闽岛。还有很多在路上由于离乡背井而患难与共、相互扶持的好朋友们,被分到婆罗洲北部,现在是沙巴,一个叫山打根的小城。
吴阿吉和陈清山的哥哥们就这么从台湾的乡下来到了南洋。他们第一次看见原始丛林里浩浩汤汤如洪荒元年的大河,河边的参天大树每一株都像一座霸气的独立的山岳,俯视着蝼蚁似的人。蜥蜴巨大如鳄鱼,拖着长长的尾巴,从浑浊的河水里缓缓游出,趴上浅滩的岩石,用蜡似的眼睛,君王的姿态,看着岸上的人群。
陆陆续续地,更多的福尔摩沙少年被送到南太平洋,甚至三千里外赤道以南的新几内亚。譬如南投埔里的四十个人,都是十八、九岁的,加入了“台湾特设勤劳团”,驻扎在日本海军基地拉包尔。拉包尔驻扎了十万精兵,被盟军日夜轰炸,断了粮食补给,必须依靠岛上的自力救济。埔里少年们万分紧张,日夜劳动,忙着开垦农场,大量养植蔬菜,供给前线的士兵。
他们同时紧迫地挖防空洞和埋尸坑。需埋的尸体,每五十具共享一个大坑;数字不到时,就用美丽的椰子树叶暂时盖着。等着火化的尸体,需要大量的木材和油料。到战争末期,尸体太多,材料都不够了,埔里少年的任务,就是把每一具尸体剁下一只手掌,只烧手掌,然后将一点点骨灰寄回日本。当然,到最后,只够剁下一根根手指来烧成灰,送还家人了。
在南洋,这些台湾年轻人穿着英挺的日军制服,背着上了刺刀的步枪,胸前绣着日本名字,在俘虏营前站卫兵,监视着被日军俘虏的盟军士兵,命令这些白种士兵挑砂石、挖地洞、采铜矿、建机场,在最饥饿的状态之下做苦役。
所谓盟军士兵,也是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如果是澳洲兵,个子高大、金发蓝眼睛的居多;如果是新加坡被攻下时集体投降的英军,那么皮肤黑一点、眼睛炯炯有神的印度兵居多。
古晋、山打根、拉包尔,都有大规模的日军所设的战俘营,这些看起来是日本兵的台湾监视员,有多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呢?
陆陆续续地,更多的福尔摩沙少年被送到南太平洋,甚至三千里外赤道以南的新几内亚。
56,堪萨斯农场
那是一九七七年,我在美国读书。研究所的同学小黛请我到她家去度周末。听说堪萨斯州的农场很大,大到农人必须开飞机从这一头到那一头去勘视自己拥有的玉米田。她笑说,“我家没那么大。不过,用眼睛也看不到尽头就是。”
中西部的秋天,天空蓝得透彻,仰头望久了,会突然吓一跳,好像整个人都被一片无涯无底的水深蓝吸进去。我们站在刚刚收割过的玉米田边,一群乌鸦在田里漫步啄食,突然聒噪起飞,远处一辆拖拉机轰隆轰隆驶过来,驶在收割后凹凸不平的田间,扬起翻腾的尘土。
“我爸。”小黛说。她对着拖拉机里的人用力挥手。
“小妞,”小黛爸爸扯着喉咙从远处喊,“有朋友啊?太——好了。”
拖拉机的轮胎比人还高,穿着吊带农人工作裤的小黛爸爸熄了火,有点困难地从驾驶座上小心地爬下来。他戴着帽子,看不清他的脸。向我们走过来时,我发现,这瘦瘦的人一脚长,一脚短,跛得很明显。
小黛跳上去用力地拥抱他,亲他,他大笑着说,“轻一点,老骨头很容易散掉。”拥着女儿,然后转过脸来看我。
看见我,他突然愣了一会,整个脸阴沈下来。我伸出去准备表示礼貌的手,也就尴尬地悬在那儿,进退不得。
小黛也一时不知所措,然后好像明白了什么,轻快地说,“爸爸,她不是日本人啦。她是中国人——也不是台湾人。”我惊奇地看了她一眼,她使了个眼色。
小黛来拉我,然后一手挽着父亲,一手挽着我,半拖半带地往那白色的大屋走去。一路上用娇嗔的声音和父亲说话。
吃过晚饭,我早早蜷到床上,拥着柔软的毛毯,望向窗外。清润的月光无声地照亮了一整片芳草连天的田野,无限甜美。从谷仓那边传来低低的犬吠,彷佛乳牛也在槽里懒懒地走动。
小黛光着脚进来。她穿着睡衣,金黄的长发乱乱散在肩上,手里拿着一个牛皮信封。
她跳上床,像猫一样弓起腿来,把大信封打开,拿出两张泛黄的纸,小心翼翼地摊开在毛毯上。是一份很皱的、发黄的旧文件,五零年代的打字机打出来的那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