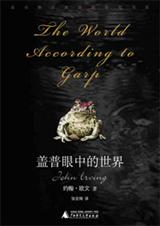平凡的世界(一)-第2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婚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但他又感到,润叶姐对少安哥感情很深,而且看来最近很痛苦。她知道不知道少安哥已
到山西去相亲?假如她真的爱少安哥,而少安哥也没给她说就去找另外的女人,那她会多痛
苦啊!他要不要去给润叶姐说说这事呢?不是专门去说,而是找个借口去她那里,先说别
的,然后无意中再带起这事……
他很快又想:不能!他对润叶姐和少安哥的事一点也不知情,怎么能冒冒失失去给她说
这些事呢!
过了不多一会,忆苦思甜报告会结束了,操场上传来一片嘈杂的人声。
快吃饭时,少平正要拿以前润叶姐给他的粮票换成的几张白面票,去给父亲买饭,金波
却从街上买回来一堆烧饼和二斤切碎的猪头肉。再没有比金波更可爱的人了!他会忠诚而精
明地为朋友着想,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候,给你最周到的帮助。当金波听说他要请一段假回村
子的时候,立刻把家里他住的窑洞门上的钥匙交给他,同时指着吊在那把大钥匙上的小钥匙
说:“这是我窑里箱子上的钥匙,箱子里有纸烟,熬了的话,拿出来抽去,烟能解乏!”
少平笑了笑说:“你先不敢给我惯那毛病!”
孙玉厚老汉也笑了,说:“你们还小,先不敢学这。烟这东西一沾上就撂不下了!”
第二天早晨,金波去县贸易经理部找了他父亲认识的一个司机,少平就和父亲坐顺车回
了双水村……孙少平回到村子的第二天,就跟一队的人上山锄地去了。尽管他生长在农村,
也常劳动,但这大伏天在山里苦熬一天,骨头都快散架了。晚上他累得只喝两碗稀饭,就去
金家圪崂那边睡觉去了。当然,在去金波家之前,他都要顺路去学校一趟,在本村教师金成
的办公室里把当天的报纸一张不剩地看完。看完报纸后,他就得赶紧去睡觉,因为第二天天
不明就要出山。在睡觉之前,金波他妈通常都给他枕头边放一点烙饼或者白馍。金秀也象对
她哥金波一样,见他来时,还给他打一盆热水,让他泡一下脚再上床,说这样解乏……在这
段日子里,严重的干旱已经把庄稼人的心都烤焦了。太阳象火盆一样高悬在空中,山上的庄
稼叶子都快晒干了,所有的绿颜色都开始变灰,阳坡上有的庄稼甚至已经枯黄了。庄稼人出
于习惯和本能,依然在这些毫无收获指望的土地上辛勤地劳作着,抚哺这些快要死亡的、用
他们的血汗浇灌起来的生命。整个村子已经失去了生气,任何人的脸上都再也看不出一丝的
笑容来了。到处都能听到庄稼人的叹息,听见他们忧愁地谈论今冬和明年的生计……现在,
只有川道里那点有限的水浇地,庄稼还保持着一些鲜活。这是因为入伏后曾用抽水机浇灌了
一次的缘故。但是,这点全村人的命根子也已经危在旦夕。因为东拉河里再也坝不住多少水
了——这条本来就不大的河,现在从下山村发源地开始,就被沿途各村庄分别拦截了。至于
哭咽河的水,早已经涓滴不剩——那位神话中失恋男人的眼泪也被这火辣辣的太阳烤干了。
据村里老庄稼人推断,川道的这点庄稼如果再不浇水,恐怕不出一个星期,就和山上的庄稼
差不多一样要完蛋了!
少平一回村就处在这样的气氛中,心情感到无比的压抑。他的熬煎和庄稼人的熬煎一样
多——他的命运和这些人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啊!
中午的时候,他在家里也呆不住,就常常一个人走到没有什么水的东拉河边,坐在河边
的柳树下看一会书;口渴了,就趴在柳树旁边的水井上喝几口凉水。
这天中午,当他又赤着脚走到河边的时候,看见一个人头上戴顶柳条编织的帽圈,跪在
那口水井前面,嘴里似乎喃喃地说着什么。少平从背后认出这是田万有大叔,便忍不住一个
人偷偷笑了。
田万有比少平他爸还大一岁,但这人比年轻人都调皮。他是村里头一个乐天派:爱闹红
火,爱出洋相,而且最爱唱信天游。他自己也不知道他会多少信天游,反正唱一两天不会重
复。而且这人还有一样怪本事:能编“链子嘴”——一种本地的即兴快板。他见什么能编什
么,往往出口成章。少平记得他小时候,村里年年都要闹秧歌,田万有大叔常常是当然的伞
头。他唱秧歌不仅在石圪节,就是在外公社都有名气。日常在山里劳动,大家也都愿意和田
万有在一块,听他唱几声,说几句逗人笑的话,就少了许多的熬累。万有大叔在姓田的他那
一门辈中排行第五,因此村里和他同辈的人都叫他田五,晚辈称呼他五大叔。他哥田万江排
行第四,是一队的老饲养员。
少平一直很喜欢这个农村的土艺术家,小时候常缠着让他唱信天游。五大叔没架子,三
岁娃娃让他唱,他也会挤眉弄眼给唱几句的。
现在,少平看见万有大叔跪在井子边,头戴柳圈帽,嘴里念念有词,不知他做什么——
反正他这样子本身就能把人逗笑。
少平踮着赤脚片,悄悄走到五大叔背后,想听他嘴里念叨什么。
当他敛声屏气站在他背后的时候,才听出五大叔正一个人在祈雨哩!文化革命前,天一
旱,农民就成群结队求神祈雨。现在这类迷信活动已被禁止。可田万有置禁令于不顾,现在
一个人偷偷到这里来向诸神祈告。少平听见五大叔嘴里虔诚地,似乎用一种呜咽的声调正唱
道——晒坏的了呀晒坏的了,五谷田苗子晒干了,龙王的佬价哟,救万民!
柳树梢呀水上飘,清风细雨洒青苗,龙王的佬价哟,救万民!
水神娘娘呀水门开,求我神灵放水来,龙王的佬价哟,救万民!
佛的玉簿玉皇的令,观音老母的盛水瓶,玉皇佬价哟,救万民!
少平原来想猛地“呔!”一声,和田五大叔开个玩笑,但听见那哭一般的祈告声,心便
猛地一沉——这悲戚的音调实际上是所有庄稼人绝望的呼喊声呀!
他又踮着脚尖,悄然地离开了水井边。少平现在连看书的心思也没有了,便一个人上了
公路,赤着脚片漫无目的地向村子前面走去……
第二十六章
严重的旱情使双水村沉浸在一片悲哀之中。山上的庄稼眼看没什么指靠了。全村人现在
把唯一的希望,都寄托在川道的那一点水浇地上。
从省上到地区,从地区到县上,从县上到公社,有关抗旱的文件一个接一个地往下发,
号召各级领导和广大贫下中农,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看来旱灾已经成为全省性的现
象了。
双水村人眼下能做到的,就是在通往米家镇方向的村前东拉河上坝住一点河水,用桶担
着往川道的庄稼地里浇。地畔上的两台抽水机早已经闲躺在一边派不上用场了——这点可怜
的河水怎么可能再用抽水机抽呢?
全村所有能出动的人,现在都纷纷涌到了这个小水坝前。在这样的时候,人们劳动的自
觉性是空前的,就连一些常不出山的老婆老汉也都来了;他们担不动桶,就用脸盆端,用饭
罐提。村里的学校也停了课,娃娃们拿着一切可以盛水的家具,参加到抗旱行列中来——有
些碎脑娃娃甚至捧着家里的吃饭碗往地里端水,这已经不是在劳动,而是在抢救生命。水
啊,现在比什头都要贵重!这就是粮食,是饭,是命……可是,东拉河坝里的这点水,全村
人没用一天的时间就舀干了。除过村中的几口井子,双水村再也没一滴水了。东拉河和哭咽
河象两条死蛇一般躺在沟道里,河床结满了龟裂的泥痂。
全村人在绝望之后,突然愤懑地骚动起来。所有的人现在都把仇恨集中在上游几个村庄
——这些村子依仗地理优势,把东拉河里的水分别拦截了。据去原西县城办事回来的人说,
下山村、石圪节村和罐子村的河坝里,现在都盛满了水,他们一直用抽水机抽水浇地哩。尤
其是公社所在地石圪节村坝的水最多,他们不光拦截了东拉河的水,还把东拉河的支流杏树
河也拦截了——石圪节现在倒成了“双水村”!双水村的人愤怒地咒骂着这些“水霸”——
亲爱的东拉河是大家的东拉河,不是这几个村的东拉河,怎么能让他们独霸呢!
人们由于对这几个村霸水的愤怒,立刻又转向了对本村领导人的愤怒:双水村的领导人
太无能了!他们现在难道都死了吗?这群常指教人的小子在本村耍好汉,现在却一个个藏到
老鼠洞里了!书记田福堂干啥去了?这个强人怎么现在成了个窝囊蛋……
田福堂此刻正在自家窑里的脚地上烦乱地来回走着,手里拿一根纸烟,象通常那样,不
点着抽,只是不时地低头闻一闻。他现在和全村人一样焦急。他知道,今年如果连川道里的
这点庄稼也保不住,别说明年春天,恐怕今年冬天村里就有断炊的家户。到时候人们吃不
上,嚎哇哭叫,甚至到外村去讨吃要饭,他作为村里的领导人,脸往哪里搁?再说,双水村
还是全公社的农业学大寨先进队哩!那时候,别村的支部书记就会在背后指着他的后脑勺嘲
笑他田福堂!”
他现在也和大家同样气愤东拉河上游的几个村庄。这些队欺人太甚了!竟连一滴水也不
给下游放,眼看着让双水村成为一片焦土!
他同时也对公社领导有意见:为什么不给这几个村的领导人做工作呢?难道你白明川和
徐治功就领导东拉河上游的几个村子吗?双水村不是你们管辖的范围?哼,如果我是公社领
导,我就会把水给每个村都公平地均开的……不过,光焦急和气愤并不能解决双水村的现实
问题。眼前最当紧的是,要千方百计保住川道里的庄稼。只要保住这点收成,全村人今冬就
能凑合过去。至于明年开春以后,国家就会往下拨救济粮的,到时候就不是光双水村吃救济
粮,其它村也得吃!要不光彩大家一齐不光彩,别让他田福堂先当龟孙子!
但是,川道里的这点庄稼怎能保住呢?河道里已经没一点水了;如果河里有水,那他田
福堂就是和全村人一块不睡觉,昼夜担水也会浇完这些地的。
他焦急不安。他一筹莫展。他知道全村人都在等着看他怎么办。他也知道现在有人咒骂
他,说他成了个窝囊蛋,让上游几个大队的领导人欺住了。玉亭已经给他汇报了村里谁在骂
他。他现在内心并不抱怨这些骂他的村民,反而意识到,不论怎样,双水村的人在关键时候
还指靠着他田福堂哩!为什么不骂别人哩?知道骂别人不顶事嘛!众人骂他田福堂,是等着
让他想办法哩!大家还是把他田福堂当作一村之主嘛!骂就骂去!
他现在先不管本村人如何骂他,而对上游几个村庄的领导人一肚子火气。他想:不能这
样下去了!如果这件事他再不想办法,也许他的威信将在村里丧失得一干二净!他想他得破
釜沉舟干一家伙!没办法,老天爷和东拉河上游几个村的领导人,已经把他田福堂逼到一条
绝路上了!
他在脚地上转了一阵以后,天已经昏暗下来。他破例点着了手中的这支烟,没抽半截,
他就猛烈地咳嗽了老一阵。他把这半截纸烟扔掉,即刻就出了门。
在他出了自己院子的时候,他老婆撵出来说:“你还没吃饭哩!”
他只顾走,头也不回地说:“饭先放着!我开个会,完了回来再吃!”
他先来到孙玉亭家,让玉亭立刻通知大小队干部,一吃完晚饭就到大队部来开会。他给
玉亭布置完,就一个人先去了大队部。
大队部在田家圪崂这面的公路边上,一线三孔大石窑洞,两边两间堆放公物,中间一间
就是会议室。院子里停放着大队的那台带拖斗的大型拖拉机。
田福堂身上带一把会议室门上的钥匙。他自个儿开了门,一股热气顿时扑面而来。他上
了那个小土炕,把窗户打开,企图让外面的凉气进来一点——但外面和窑里一样热。他解开
小布褂的钮扣,袒胸露怀,盘腿坐在小炕桌前,把煤油灯点亮,等着队干部们的到来。
他静静地坐在这里,脑子里正盘旋着一个大胆的计划。他想闻一闻烟,但发现他忘了带
纸烟,就烦躁地一边想事,一边用手在自己干瘦的胸脯上搓汗泥。
不多一会,大小队干部就先后来到了大队部。除过一队长孙少安出门在外,村里所有负
点责的人都来了。大家似乎都意识到这会议的内容是什么——解决水的问题。但没有人抱什
么希望。
开会之前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主题。大家七嘴八舌,说的都是水;他们一个个愁眉苦脸,
就象山里的庄稼一样没有精神。
玉亭先给各位负责人提起了另一件事。他说据许多人看见,田万有每天中午都跪在东拉
河的井子上向龙王爷祈雨哩。他建议大队要批判田五这种封建迷信活动。
玉亭提起田五和他的“活动”,公窑里所有的队干部都笑了。田福堂说:“算了吧!到
时田五背着牛头不认赃,说他是耍哩,你有什么办法?田五你又不是不知道!”大家都
“嗡”一声笑了。
玉亭看书记否决了他批判田五迷信活动的建议,也就再不言传了。
这时,田福堂咳嗽了一声,说:“咱把会开简单一点。这几天,我和大家一样焦急。眼
看庄稼都晒干了,就好象把我的心也晒干了。现在就指望川道里的这点庄稼,可东拉河里的
水都叫上游几个村子霸占了……”
“我们就等死呀?不能把他们的坝给豁了?”一队副队长田福高打断田福堂的话,插嘴
说。
有许多人立刻附合田福高的意见。
田福堂满意地笑了。他等众人的声音平息下来,说:“我也正盘算这样干哩!你们和我
想到一块了!如果大家意见一致,那咱们干脆今晚上就动手!
“不过,为了避免村子之间的公开冲突,防止混战一场,咱们要暗暗地做这事。等他们
知道了,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