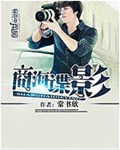柏林谍影-第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勒卡雷 不止是间谍小说的第一人(1)
文/唐诺
在阅读勒卡雷小说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个真实人物,这人名叫阿兰·图灵,天才的数理和密码分析专家,二次大战期间的英国知识分子。
图灵原本是剑桥大学里学术世界的一员,“二战”期间他做了一件最特别的事,那就是应英国政府的秘密征召,进驻白金汉郡的柏雷屈里园,负责德军作战密码的破译工作,其中最精彩的成就,是图灵和他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奇形怪状伙伴(有瓷器权威,有博物馆研究主任,还有全英西洋棋冠军以及一堆桥牌顶尖高手云云),在“二战”进行不到一半,即神不知鬼不觉地破解了德军的神奇密码机“奇谜”。这不仅在往后每一处战场、每一次重大战后帮助盟军化险为夷,它的威力还一路贯穿到最终决定性的诺曼底登陆一役,几近完全透明地准准研判出彼时德军所部署58个师的数量、身份和位置(只误差了两处),从而及时修改了最后D…DAY的登陆作战计划,所以亨利·兴斯里爵士说:“倘若政府代码暨密码学校(即柏雷屈里园)未能解读‘奇谜’密码,收集‘终极’情报的话,这场战争将迟至1948年,而非1945年才结束。”
所以说图灵和他这群被丘吉尔称之为“会下金蛋,但从不咯咯叫的鸡”的解码伙伴从此成了英雄是吗?很抱歉还没有,只因为英国政府要持续保有这个秘密优势,不仅不愿公开“奇谜”机已被破解的真相,而且还把大战期间掳获的数千台“奇谜”机送往各殖民地,借此监视战后风起云涌的各殖民地一举一动。同时,柏雷屈里园亦正式关闭,相关资料全数封存或直接销毁,除了少数人转入政府常规情报机构之外,大部分人哪里来哪里去放回民间,当然,每个人都得宣誓守密。
这个秘密整整被保护了三十年之久。在这三十年的漫漫时光之中,我们差不多可想像这批曾为大英帝国和女王陛下立下不可磨灭功勋的人的尴尬甚至说悲伤处境——对英国政府而言,英不英雄再说,当务之急在于他们是一群“知道太多”的麻烦之人,得防贼般严密监视每一个人;同时,这些人还得时时面对各自身旁之人的询问、质疑和公开指控:当大家都在为国家存亡流汗流血奋战时,你在哪里?你做过什么?你要不要自己说说看?
三十年太长的时间,所谓的真相、功勋、正义云云,在揭晓并褒奖那一刻来临时早已失去了实质意义,只像是噩梦醒来终于可放心呼口大气的慰藉而已;而且你可想而知的,很多人等不起这三十年,锦衣夜行早把所有秘密带往天国上帝的正义法庭去了。
其中,功勋最大的阿兰·图灵是等不及的人之一,也是下场最悲惨的人之一。1952年,他在报告一宗窃案时,居然向警方坦承当时他正和自己同性恋伴侣相处一室的事实,遂以重大猥亵的罪名遭起诉并定罪。他从此身败名裂,已批准的研究计划被取消,还得接受荷尔蒙治疗变成性无能而且变得痴肥,如此两年,图灵终于以一个注射了氰化物的毒苹果自杀,当然不会有英国王子他日来吻醒他,才四十二岁。
勒卡雷一定知道图灵的故事,他没写图灵的真人真事,然而他的间谍小说中始终有着这样子那样子的不同阿兰·图灵,以及其悲伤孤寂荒谬的处境。
行内人的小说
有关勒卡雷和间谍小说,至少对我个人而言,其实可以用很简单,甚至就是一句话来充分说明:勒卡雷就是间谍小说家的第一人,而且第二名可能还没有出生。
这样子讲话,乍听之下不敬,也不妥,而且不全然完全合于事实,我想我们可解释一下——不敬,是因为如此的实话实说可能冒犯了其他勤勤恳恳的间谍小说书写者,很抱歉,我们晓得,不管在虚幻的间谍世界或我们硬碰硬的现实人生里,实话,差不多永远是最伤人、最具破坏力量的;不妥,是因为书写创作不是比百米赛跑不是打一场篮球,正常状况下理应没有第一名第二名这类童稚游戏的胜负排名,除非有近乎奇迹的事发生了,而不巧勒卡雷正是此一书写领域的如此奇迹,他的规格、视野、深度和情感完全超越了所有间谍小说书写者甚至这个类型小说基本框架所能拥有的,他仿佛独自在另一个层面书写,独自探向只属于他一个人的辽阔天空;不全然合于事实,是因为我们并非没读过可堪比肩或甚至更胜一筹的间谍小说,比方说台湾现阶段有中译本可读的,《哈瓦那特派员》,或《沉静的美国人》(《喜剧演员》可不可以也划进来呢?),但这么说我们就更明白了,上述这些作品全出自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之手,一般我们并不以间谍小说来辨识它们,一如我们不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和《罪与罚》并入推理犯罪小说一般,这差不多已直接告诉我们,勒卡雷小说“不仅仅”是间谍小说而已,说勒卡雷是间谍小说世界的只此一人,说真的也并不是多高的一种赞誉,有一大部分的勒卡雷应该被正确置放到小说整体的经典世界才公允。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勒卡雷 不止是间谍小说的第一人(2)
格林本人很喜欢勒卡雷小说,至少从《冷战谍影》(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这部成名作开始,他的慧眼和慷慨引介对勒卡雷的崛起乃至于今天的超越类型地位助了可不止一臂之力;同样的,勒卡雷亦一直真心推崇格林,毕竟他看待世界和情感关怀的方式本来就和格林有惊人的相通之处,他的小说也始终有着浓郁的格林气味,事实上,这两位英籍作家几乎可自成一个谱系来读。
像阿兰·图灵的悲剧,我们首先会惊觉,间谍世界是多么奇怪、多么悖于我们“正常人性”的一个世界,它好像独立于我们的现实人生之外,单独封闭起来,用完全不同的情感、信念和游戏规则进行,很多我们在现实人生中坚信的、视为珍贵的,乃至于已习焉不察铸成我们自然反应的东西,在这个诡异的世界中都得去除,比方说信任、诚实、善意和悲悯云云;但要命的是他们仍都是人,和我们一样拥有着共通的,而且并非有弹性到可任意扭曲折弄的根本人性和需求,我们喜爱的他们一样有反应,我们会悲伤的他们一样有感觉,一样蛮求有个家可回,有朋友在的小酒馆可去可交谈,有亲密可放松一切警戒的人可讲最心中的话,有一个同样有限因此得弄清所为何来的生命本身,这些被用尽力气压制下去的东西不可能就此消失,它们只是黯淡了,但也因此更尖锐更蠢蠢欲动。
这样一个(被强迫)隔绝的异样世界,对你我这样的正常人来说极难凭空想像并有效掌握,遂使得间谍小说的书写一样呈现了相应的诡异封闭气息——作为一种类型小说,间谍小说的总量相对来说并不大,却奇峰突起般有不成比例的醒目作品乃至于像勒卡雷这样的人冒出来;而且它的书写者,似乎一直有着某种森严的资历限制,得多少是在这个世界浸泡过的“行内人”(勒卡雷和格林都有这个他们日后不太愿意提起的资历),而不是先靠门外的破碎资讯和纯粹想像瞻望所可替代。举个最刺激的实例是推理小说一代女王的阿加莎·克里斯蒂,她有缜密的清楚脑子这完全不必怀疑,有丰富到难以比拟的书写实战经历这也路人皆知,事实上她还多少有二手的间谍世界经验来源,但她偶尔伸脚进去写的间谍式小说却令人骇异得只能用一塌糊涂来形容。《四大天王》(The Big Four)是神奇的波洛系列直跌谷底的败笔,《七钟面》(The Seven Dials Mystery)则是一场小学生式的可笑儿戏,间谍小说书写的独特严苛资历要求由此可见一斑。也因此,很长一段时间间谍小说一直“不正常”地被英籍作家所垄断,这当然不可能跟什么神秘的民族心性有关,纯粹是历史偶然,只因为英国这个老帝国长期垄断着跨国的间谍事务,而且大量使用半业余的工作人员,包括驻外的知识分子和新闻工作者,以及旅居的作家或一般商人云云,这中间原本就有笔在手却奉女王陛下荣光之命误闯间谍世界的文人遂成为间谍小说书写的最大供应来源。
这里,我们再进一步把间谍小说置放到真实的时间之流里。现代间谍小说是冷战时期的产物,东西冷战是什么东西?是一长段不能战也不能和的外弛内张或外张内弛的可怖武力和意识形态对峙,是一页他日回顾起来令全世界人僵在那里的荒谬历史,人类世界硬生生被一刀划开为两个阵营,所有人都同时拥有正常人和恶魔两种身份,当我们用人的角度去思考时,世界什么事也没发生而且实在没道理发生,当我们以恶魔的角度看事情时,世界登时危险一如累卵极可能旦夕间化为一个大爆竹。如此诡谲几无交集的冷战二元背反面貌,直接转入间谍小说书写,便把间谍小说裂解为泾渭两种书写方式及其成品。其一是恶魔角度的,可以伊恩·弗莱明为代表,或直接讲就是他笔下反复拯救世界不休的007情报员詹姆斯·邦德,在这组小说中,善恶两方已然分明到电灯开关般不必劳神多想下去,间谍世界剩下的只是行动,或专业些称之为任务吧,由他的上司M下达,用邦德的手来完成,因此,我们可以让思维休息而交由感官来和这组小说相处,是一种享乐,坐云霄飞车或高空弹跳那种脑子一片空白的享乐。另一是正常人角度的,代表人物当然就是勒卡雷,正常人太复杂了善恶永远在相互讨价还价之中,塞不进冷战那种琐罗亚斯德'1'拜火教创始人,认为世界只有一个真神和一个凶神。——编者注'1'式的简易框架之中,当人不再只是单维度的间谍,而同时也是个人时,冷战的核心荒谬性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顺此善恶二分原则所建构成的秩序也骨牌般一个一个倒塌下来。想想,相隔数千里数百里的素昧平生之人彼此何来深仇大恨?这不是太奇怪了吗?就算敌对是可能的、习焉不察承继下来的,又如何能说就是至善至恶之别呢?而既然不是至善至恶之争,这样的不惜以死相搏又所为何来呢?当这组小说通过书写重建起具体的人、具体的实物世界时,光是常识就可以轻易看穿冷战封闭间谍世界的扭曲和变态,那种自以为一举一动事关天下人的安危,那种愿意拼死阻止世界毁于一旦(不管是遭敌方渗透破坏征服的败战形式,抑或大战引爆万劫不复的同归于尽方式)的信念怎么看都只是幻觉,真正伤害人折磨人的,不是未来式,而是进行式,不必等那个甚至永不发生的终极性毁灭,倒是当下且已持续相当时日的人性和道德扭曲,是人被此种神圣幻觉催眠摆布的必然又可悲又可笑样态。也就是说,真正的敌人极可能不是你要杀他他也要杀你那些敌对间谍,他们其实只是你意识形态背反,但处境雷同的相濡以沫可怜虫,而是整个荒唐间谍世界的构成,它是个太小的囚牢,不仅禁锢人,还把人硬生生扭折成各种可怖的样态。
勒卡雷 不止是间谍小说的第一人(3)
从同情到背叛
老实说,如果我们跳出冷战的意识形态泥淖,跳出间谍的封闭世界,纯粹从理论思辨的层面来理性地说明间谍世界的荒谬本质并不难,要用道德来质疑它攻击它那更容易,毕竟,间谍这个古老的行业本来就冒犯了一堆人的基本道德信念,其道德正当性自始至终孱弱不堪。事实上它的存在理由也不靠这个,人们之所以忍受它,最终仍是某种实然的无奈,它是依附在战争冲突下一个偷偷摸摸的次等恶棍,偶尔战争冲突取得某种神圣正义光环,它鸡犬升天般跟着神气,而人类一天没办法根除彼此间的战争冲突,我们也就只能看着间谍霉菌在这上头继续生存并代代繁衍。
但这不是勒卡雷的方式及其真正价值所在。勒卡雷用的是小说而不是理论;勒卡雷是站进间谍世界之内而不是在外头指指点点;勒卡雷也不是打开始就清楚豁脱于冷战两造的意识形态之上,事实上,作为一个相当典型的英式知识分子,勒卡雷是有他基本位置的,他大体上仍站在所谓自由民主和欧洲基督教文明这一侧,包括像《女鼓手》(The Little Drummer Girl)这部小说,当他把笔锋转向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时,他还是把回教徒划到对立的那一面。这样的基本位置本来会局限他,但勒卡雷以他的诚实、不受催眠的清醒洞察力和同情心,以及他无与伦比的小说书写技艺击败了这个限制。
也许就像格林讲的,人不得已总是有一边要站的,但如果我们能把基本位置的选定当成开始,而不是完成,超越其实是可能的,而且还会是一种较有真实质地的超越,只因为那种极不舒服的拘限,往往让你更警觉到自己让步了什么省略了什么,而且你也因此更深刻了解这个基本位置的弱点和漏洞,这通常不是一开始就摆出敌意姿态的门外之人看得到,尤其是感受得到的。
勒卡雷从间谍内部来,不管是《冷战谍影》那样令人心痛的冷血成功,或如《镜子战争》(The Looking Glass War)那样一败涂地的荒唐,勒卡雷总是同情先于批判,他对自己笔下这些间谍不是打开始就准备好用一句生冷的话来结论他们打杀他们,而是耐心地、深情款款地进入他们,包括他们间谍任务外的下班时光和家居生活,包括他们的彼此闲谈和牢骚,包括他们被挤压被搁置的情感和其他但凡谁都有的计划梦想,包括他们内心最深处偶尔冒出来的某个短暂或从此挥之不去的念头云云。当他们不再只是个名字,是个职称或代号,而是个完完整整的正常人时,某种被延迟下来的批判、被延迟下来的愤怒和哀伤就蓄满了情感的风雷出现了——这个愤怒和哀伤由同情转换而生,用最普遍素朴的人性支撑起来。
也就是说,勒卡雷是同时写两部小说的,类型的间谍小说和开放深沉的一般小说,同时创造出两个世界,间谍世界和正常人的世界。这两个世界既彼此暴烈冲撞又相互暧昧渗透,机智与无能,伟大与细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