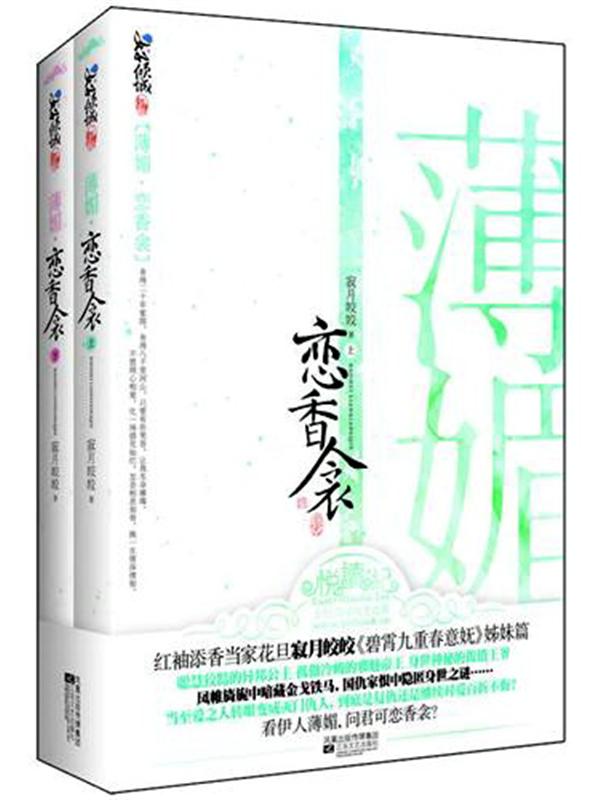寂月皎皎-倦寻芳香散舞衣凉-第7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可萧彦还说,我缺少了掌权最重要的气质:无情。
无情……
踏上侧面的石阶,拾步而上走出石牢时,我再往拓跋顼的方向望了一眼。
他依旧垂着头,盯着手腕上蜿蜒而下的鲜血,出神地像看着春日里缓缓盛开的花。
栗色的头发许久不曾修剪,更加长了,缭乱地披散在肩上,一缕一缕地微微蜷着,像要缠上人的心头来。
心头闷闷的痛开始尖锐。
吏部尚书晏奕帆送我上轿时,我到底忍不住,向他招了招手。
“奕帆,将拓跋顼送回石牢后,找个可靠的好大夫给他看下伤,缺了什么药了,到公主府来取。”
晏奕帆见我吩咐得郑重,即刻应了:“公主放心!只要公主想他活着,下官绝不让他死了!”
我眯了眯眼,沉声道:“我要他在廿八之前,能活蹦乱跳地被关入简陵!”
晏奕帆怔了怔,虽是不解,依旧很快答道:“行,下官请最好的大夫,用最好的药给他治疗!”
这事在当天便被禀知了天临帝萧彦,听说他当即便挥挥手,让按公主说得办。
到第二日和他一起用了午膳后,萧彦笑道:“丫头,你也真够毒的!朕本想着这拓跋轲委实太过无礼,打算亲自带了兵马过去征讨,就拿他弟弟斩了来祭旗出征呢!你却拿了他弟弟生殉萧宝隽,就气他纵然本领通天,也没法在廿八就打到宁都来救人。想他一世无情无义,心狠手辣,独独疼爱着这个弟弟。如今让他想象着自己弟弟不得不在黑暗的坟墓里等死,他纵然手提千军万马也无可奈何,不知会作何感想?”
孤影淡,芳心向春尽(五)
拓跋轲会怎样想?会难过么?
我不知道。
这人永远心如铁石,难得的温柔,也不过为了他自己卑劣的占有*****。
号称宠我疼我,还假惺惺送我一屋子的东西,杀起我来却眼都不眨一下。
他唯一的软肋,大约也只有拓跋顼了。
当日在悬崖上,他肯放过重伤的拓跋顼,已是我见到的他最柔软的时候了。
“无论如何,那是他的弟弟。他自己想打想杀是一回事,被人当成牲畜殉入仇人陵墓是另一回事。何况给牺牲的又是名正言顺的北魏储君,以他的自尊和骄傲,大约怎么也不会快活。”
我快意地轻笑,“父皇,我只要想到拓跋轲会因此坐立不安,睡不安席,我就高兴得很!”
萧彦深深望着我,叹道:“看来你在北魏……着实吃足了苦头。”
再次被人提起往事,我的脸色应该有些发白。但我努力地振足了精神,若无其事道:“多些经历未必是坏事。不然,我还是以前那个不知忧患不知死活的齐国公主,只怕早给人暗算得连尸骨都不知哪里去了。”
萧彦点头道:“怪不得你一心想建立起自己的势力,大约也是总不安心,希望有足够的力量保护自己罢?也好,父皇已经这么大年岁,也不知能保护你多久,你自己学着保护自己总是没错的。”
他转头又问我有没有中意的男子,可以择作东床驸马;我却记起了他有多处旧伤,逢着湿冷的天气便会发作,也追问太医院的用药情况。
彼是衰柳掩映,残荷乱舞,菊英零落,正是暮秋初冬萧索天气,最易动人愁怀。
但我和萧彦并坐于榻边,像任何一对民间的父女般絮絮说着家常,倒也不觉冷意。
可皇宫东北角的颐怀堂冷不冷?
那些杜蘅兰若,到了秋冬季节,连香气都清冷清冷的。
萧宝溶一向怕冷,以往住的翠玉楼一早便会用上银霜炭。
还有刑部的密牢,那里太冷了,即便拓跋顼那样健壮的男子,大约也会觉得冷吧?
或许,天底下有一种冷,叫孤寂。
-----------------------------
送那些奸细人头回北魏的使者,没几天便安然无恙地回来了。
我饶有兴趣地召来询问时,发现一切均如所料。
拓跋轲一如既往地冷漠无情,对使者和使者带来的“贺礼”及传话同样地冷淡,或者说,表面非常冷淡,看不出一丝恼怒之意,甚至按照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惯例,客客气气将使者放了回来。
果然是喜怒不形诸色。
我正抚掌细想时,使者期期艾艾加了一句:“我们走时,魏帝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迟疑半天,使者终于说出口来:“他说,他的弟弟给圣武天王殉葬,圣武天王的妹妹给他殉葬,倒也公平得很。”
我闻言已微笑起来。
我人在南方,如今寸步不出宁都,行动便是数百人相拥相护,防卫极是严密,他想再抓我,也只是做梦。明知其不可行,还说出让我殉葬的话,白白让我更起戒心,已经不像那个隐忍不发城府极深的冷血帝王了。
好吧,你慢慢气愤吧!
你越气愤,我越开心。
这笔债,总要一点一点要回来,直至最后要你的命!
不过奇怪的是,这些日子我为拓跋轲的不悦而开怀时,端木欢颜却有些怔忡,一脸的若有所思。
到后来,他连和我下棋时都能走神,时不时地蹙一蹙眉。
我有几分怀疑他是故意做出这样的恍惚情形来给我瞧。找来他的从人暗暗询问时,果然听说他去过刑部好几次,甚至有三次是在这次救人事件之前。
我不晓得他什么时候和拓跋顼这位北魏皇太弟扯上了关系,悄悄令人去调查端木欢颜的过往时,只知他祖上历代居于东山,少时便以才学闻名。但他少年时并不眼盲,十六岁开始外出闯荡,四处游历,渐渐天下知名。直到八年前忽然得了盲疾,他才回到了东山老家隐居。
拓跋顼大我两岁,八年前还个十一二岁的男童,绝不可能和端木欢颜有所交集。而端木欢颜是土生土长的南朝人,如今被我倚为心腹军师,绝无理由偏帮北魏之人。
疑惑间,我忍着硬是没去追问,只在暗中调遣兵马,准备萧宝隽大殓之事。
直待十月廿六,简陵完全落成,萧彦那边的圣旨也请了下来,追封了萧宝隽为皇帝,谥号为“幽”,后被史家称为齐幽帝。
而端木欢颜终于忍耐不住了,当晚和我奕了一局,忽侧头向我,叹道:“公主,你当真要取拓跋顼性命么?”
我只作不经意般将黑子白子随意在棋盘上摆着,答道:“先生觉得呢?拓跋顼其人,真可用文武全才来形容,难不成让我放虎归山,由他回了大魏去,从此兄弟俩戮力同心,好来取我和父皇性命?咦,只怕也未必取我性命吧,看着我年轻貌美,说不准还会把我当成歌妓舞姬般好好玩弄几天,再把我弄得死不死,活不活吧?”
端木欢颜沉默,握了一枚黑子,一枚白子,不断在两只手掌间翻来调去。忽而骨碌碌一阵响动,黑子从指缝间掉落下来,在地上弹跳了几下,滚出了老远。
=================================
终于有空爬上来,在准备好的更新里加一句话:《风暖碧落》已出版上市,悦读纪出品,上下两册,定价共38元,喜欢的亲希望支持一下,觉得价格还是很公道滴!
孤影淡,芳心向春尽(六)
侍女去捡时,端木欢颜终于将剩余那枚白子随手丢在棋盘上,低叹道:“或许……欢颜不该理会这件事。不过……他是采薇唯一的弟子,算是我师门中最优秀的传人,真这么死了,还真可惜了!”
“采薇?”
“慕容采薇。公主,你如果知道我,就应该听说过他。他和我有同门之谊。”
一提慕容采薇,我才恍然大悟。
早在萧宝溶为我请来端木欢颜为师时我就听说过,南方东山有清凤先生端木欢颜,北方薄山有鸣凤先生慕容采薇,都是当今名士,并称南北双凤。
端木欢颜目前和我算是师徒,而拓跋顼也曾提过,他的师父是慕容采薇。
他带我离开拓跋轲后,甚至说要和我去薄山隐居,想和师徒间的情份并不浅。
有些恍惚地想,不知当时随了他去薄山,如今会是怎样的情状。
萧彦必定还是会篡位的,但萧宝溶再在北方拖延下去,则未必会回宁都自投罗网了;我或许心不甘情不愿地含怨忍辱做着拓跋顼这个曾经的小叔的妻子,或许被后悔的拓跋轲重新抓回了青州,继续过着等不到天明的日子,一定不会有现在的高位了。
而拓跋顼,如果笨点,会安然地隐居着,从此舍弃一身所学做个纯朴却干净的山野村夫;如果聪明点,一定又把我交回给拓跋轲,俯首认错,继续做他江山在握的皇太弟了。
“公主……”
见我久久不答,端木欢颜疑惑着唤我。
我回过神来,笑意发苦:“我知道了,先生想为拓跋顼求情。”
端木欢颜轻叹道:“阿顼那孩子,心里很苦。喜欢一个人不难,痛恨一个人也不难,难的是,他既痛恨着的和喜欢着的是同一个人,而且无论如何没法做到彻底恨你……至于彻底喜欢你,你大约也不肯给他机会了吧?”
“机会?”我笑了起来,“先生,记得当初先给我卜的卦么?浮槎恨相逢,幽泉没疏影。我们从最初相见,便不曾有过什么机会吧?”
他不可能放弃他的江山,我不可能抛弃我的家国。——尽管如今我的家国,早已面目全非。
何况,我也是魏帝拓跋轲看上的女人,他掌握着拓跋顼的所有前程……
我将身体靠到椅背上,随手将棋子弃在地上,看着它们滴溜溜四处乱滚,却始终跑不出这一室之远,懒洋洋地笑道:“先生,我不奢求所谓的机会,还有什么琴瑟和鸣举案齐眉的,大约这一生也和我无缘了。我只想平平安安地活下去,不被人践踏,不被人欺辱……就那么难么?”
端木欢颜好久都没有说话。
他的瞳仁虽是一贯的平静无采,眉宇间却渐渐浮过凄凉之色。
“平平安安活下去,不被人践踏,不被人欺辱……”
他张口,却重复着我的话,说得很慢,似在一个字一个字地品味我的话中之意。
可我哪里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齐明帝封我为文墨公主,算是期望过高了;萧彦封我做安平公主,不管是盼我安于平淡,还是盼我平平安安,总不该是奢求罢?
端木欢颜缓缓地摇头,轻声道:“公主,人的一生,总该有些别的。”
我继续笑着,声音却是空空洞洞:“先生,我要得起么?”
“不怪你。”端木欢颜声音也低沉下来,闷闷得在枯井中回响,“可惜你要的,已经没有人能给得起。”
他正是目盲心不盲的那类人,见人见事很是明白,深知我没办法将就不喜欢的人,而我喜欢的人,就是将就也得不到了。
我安静地又笑了笑,仰着头看了片刻天花上的百鸟争春图案,还是酸疼得受不住,便将一块绣了孤零零一枝青梅的丝帕覆到眼睛上,很快便觉出眼窝处的湿润被丝帕粘湿了,寂寞地蔓延开来,冷冷地润透了眼睫和眼圈周围的肌肤。
这时,我听到端木欢颜低声道:“你知晓你再也得不到,所以索性把你曾希望拥有的所有美好都毁了,从此断了心思,一了百了?”
我吞咽了一下喉嗓间的不适,保持着声线的稳定:“先生,你觉得,这样是不是对我更好?对我们大梁也更好?”
端木欢颜沉默了很久,才道:“你若坚持这样做,欢颜也无异议。不过……也许,你可以为自己的幸福留一条生路吧?”
“没有了。我的幸福,已经走到尽头了。”
我依旧拿丝帕盖着眼睛,慢慢地回答。
这一次,端木欢颜再也没有说话。
许久,许久之后,我才听到他立起身,唤侍女扶着离开屋子的声音。
听着他摸摸索索的脚步快要到门槛前,我哑着嗓子淡淡道:“简陵,里面有条地下河流穿过。原本河中养了鳄鱼,我在相山闲着无事时,已叫人将鳄鱼捉光了。陵墓两头阻拦鳄鱼逃走的铁筛也已拿掉。”
端木欢颜顿下脚步,似一时没弄清我想说什么。
我声音更轻了,自觉像是在梦呓:“那段时间,先生正教我山川河流的走势,我就学着研究过那处河流的走向。它应该通往相山北麓的一处地上河流。”
端木欢颜的呼吸粗重起来,顿下的脚步又抬起,迅速走得远了。
而我,躲在那方丝帕下继续笑着,笑着自己的无能和懦弱,笑着自己到底做不到绝情绝意。
我笑得泪流满面。
凤凰谋,金戈青冢路(一)
十月廿八上午,齐幽帝萧宝隽出殡。
一路浩浩荡荡,白幡招扬,纸钱飞散,喇叭唢呐声嘶力竭的吼吼声中,真少假多的呜咽哭声此起彼伏。
纯白的长长队伍中,有十六人抬着的幽帝巨大棺椁,有安平公主的素色轿辇,有各色牺牲和殉葬用品,更有一个被用铁链捆于囚车上的活人,一身孝服,用白布套了头,只留下一头栗色的长发,凌乱地在山中在乱舞。
与头发的散乱相比,那僵直的姿态更显得虚弱而狼狈,不复原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