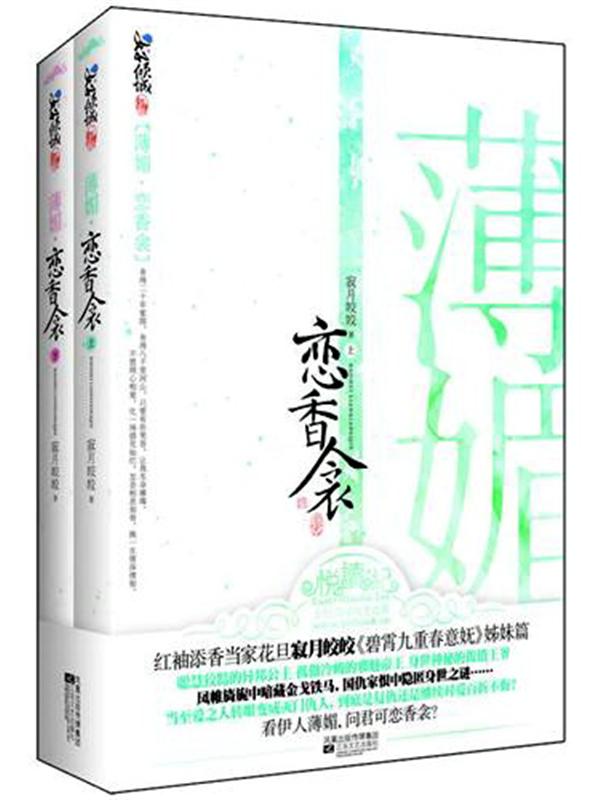寂月皎皎-倦寻芳香散舞衣凉-第1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四爪为蟒,五爪为龙。
这两种代表最高权势的神兽向来与我的三哥无关。一卷书,一壶酒,一张琴,数名舞姬,便是他轻袍缓带的神仙日子。
“阿墨,我知你能做到。”萧宝溶将一缕挡到我眉眼前的乱发拂开,低沉说道:“你够聪慧,也够珑玲,最会察颜观色,只是素常在三哥身畔,你毋须掩盖自己的真性情罢了。以后……便多长一颗心眼,好歹忍耐一段时间,三哥一定还把你带回江南来!”
忍不住,我虚弱地问:“三哥,这也是……三哥的处世方法么?”
萧宝溶并不回避我的问题,低缓说道:“前者用于盛世自保,后者用于乱世制敌。若有人伤害我的阿墨……”
他又将我揽到怀中,怜爱地抚摩着我的长发,清晰地说道:“若有人伤害我的阿墨,我也不介意……双手染血,生灵涂炭!”
他的心跳很不规则,却很有力,连臂膀都变得异常地刚硬,让我不由便想起了阿顼铁腕般的怀抱。
和我有一月之约的阿顼,今生今世,还有机会再度相逢么?
我有种哭都哭不出来的惨痛,芒刺般扎着,缓慢地在心口抽动。
原来他竟是对的,人与人之间,原没什么分别。天堂与地狱,高贵与卑微,根本就在一线之间,顷刻便能天翻地覆。
外面有人在小心翼翼地叩着门棂,低声地回禀:“惠王爷,皇上有旨,若惠王劝服了文墨公主,还请尽快回府。”
永兴帝竟然连我和惠王的告别都容不得!是在提防萧宝溶,怕他用什么法子带我逃出宫去,让他没法子用我换回他的宝贝儿子么?
我恨毒地瞪了传话的人一眼,转头看萧宝溶时,他那素常云淡风轻的眸中,同样闪着怨毒。
但他终究没说任何不满之辞,连话语也已恢复了和寻常一般地云淡风轻:“知道了,本王这便回府。”
锦衾寒,夜阑更漏残(十)
他凝视着我,缓缓松开了手臂,将我抽出他的怀抱,很吃力般站起身,慢慢向外走去。那修长优雅得身形,被近午时的阳光压得变了形,一点点挪动时,如同一纸没有魂魄的剪影。
“三哥!”我蓦地又叫唤。
萧宝溶站住,微微侧着脸,却没转过身。那阳光太炽烈太明亮,映得他半侧水晶般的眸子七彩潋滟,却是虚浮的七彩潋滟,叫我忍不住又滚落了泪,忙用袖子胡乱擦了,问道:“男女间的事……不痛苦吧?”
寻常见萧宝溶带了他成群的姬妾玩乐,每日看来都很快活,才让我想着,也去找几个美少年来陪我。
如今……我竟像身在噩梦中一般!
这样的噩梦,我还能醒过来么?醒过来,依然可以任性打闹玩耍,计算着找谁做不能拘束我分毫的倒霉驸马……
隔了许久,萧宝溶才抛下了一句:“有情,便不痛苦。”
他忽然加快加大了步伐,迅速踏出了大殿,留下惊痛悲恨的几个字,轻轻在殿中弹跳萦绕:“希望……我能来得及……”
萧宝溶的身影已经不见了,我竭力将我所有的听觉寄于他离去时踏在石板上的脚步声,可连脚步声也越来越远,很快便抓不到一丝痕迹。
殿中再无一人,空荡荡地只剩我一个,惊惶地转动着眼珠。
凤凰柱,玉藻梁,鸳鸯帏,珍珠帘,山水松鹤的檀木屏风,童子相戏的珐琅香炉,连环青琐的门窗,流丽妍艳的丹墀……
那等的繁华富贵景象,却让我越来越冷,越来越冷,双手抱肩,依然有冷意毒蛇一般穿梭过我的躯体。
孤寂地垂下头,裙裾边绣的一对穿花蝴蝶,彩翼翩翩,舞得兴高采烈,却再也不曾想过,再美丽,也不过锦绣华衣上可有可无的点缀,舞得再欢喜,也舞不出针刺线扎处的方寸之地。
隐藏自己,示人以弱。
够了么?
伺机而动,一击必中!
我能够么?
呼吸入的空气,带了春日的凉意,将肺腑一点点润得冷透。偏又有种从骨血中钻出的疼痛如火,烈烈地燃烧起来。
冷热交激。
激得我只能软倒在地毡上颤抖着,看着毡上大团精绣的富贵牡丹,似谁展开大大的笑脸,冲我得意地笑。
大齐永兴七年春,齐师大败于江水之北,太子萧康并五千骑兵被御驾亲征的魏帝拓跋轲生俘。永兴帝遣使求和,以江北十八城池及文墨公主作为条件,换取魏师所占的广陵及太子萧康。平素不理朝政的惠王萧宝溶带部分文臣竭力谏阻,永兴帝不纳;惠王固请延宕时日,侯大将军萧彦回援,为永兴帝斥归,令无事不得入宫。
凤帏深,谁道是销 魂(一)
而我,从两国确定下和约的那一天起,逍遥公主的岁月便注定走到了头。也许,那是因为所有的快乐,均已在我暄嚣骄纵中渡过的十五个春秋透支殆尽。即便我的城府阅历,都能一下子成长到萧宝溶所期待的高度,那一天,依然是我一生避无可避的转折点。
奉命押送我的使臣吴德是丞相吴鑫的侄儿,吴皇后的堂兄。侍从也经过精心挑选,连随嫁侍女都是皇后的人,一路寸步不离地盯着我,不知是怕我寻短见,还是怕我逃走。我的随身短剑早被收走,在我拿弹弓打破其中一名尾巴般盯着我的侍从的头后,弹弓也被收了。
给我打的侍从,虽然算是白给我打了,使臣也不敢拿我怎样,可是当晚竟不曾有人送晚饭给我。喝问侍女时,却说是皇后懿旨,若是公主闯祸,便不给饭吃。
他们好算计,从宁都到一江之隔的广陵重镇不过两日路程,便是不吃,也饿不死。只要有个公主交过去,事先说明我桀骜不驯,到了魏帝手里,不论有个什么好歹,都与齐国无干了。
我文墨公主萧宝墨的死活,与齐国无干……
当晚卧于驿站时,我并没有感觉出饥饿。当到吃饱喝足的侍女在隔壁床上发出均匀的呼吸,我控制着自己发冷的身躯,一遍遍地咬着锦缎的被头,直到缎面扯破了,内里的棉絮沾上了松动的牙齿,口中的鲜血浸上了雪白的棉絮……
吴皇后,吴鑫,吴德,萧康,甚至我的好大哥永兴帝萧宝隽……
我的这些好亲人,好亲戚,我都会记得,我会记得很好。
没有饭吃,只是我不听萧宝溶话受的第一个教训,算是我不能隐藏自己本性的惩罚。
隐藏自己,示人以弱……
伺机而动,一击必中……
漏声残,青灯短,夜阑长。有孤雁穿云而过,切切哀鸣,闻来梦魂俱伤,却已无泪可流。
永兴帝和吴皇后显然早就打定了主意,绝不让我坏了他们的救子大计,生怕我见了魏帝做出什么破坏两国议和大计的事来,一到广陵,使臣吴德便将我困在驿馆,令人严加看守,自己带了舆形图和珍宝去见魏帝。
我再也没有愚蠢地撒泼放刁,极安静地坐在妆台前,梳理着自己那头浓密的青丝。
镜中人肌肤剔透如玉,眉目不描如画,眼睛和母亲极像,水盈盈的幽深黑色,只是母亲久经岁月沉淀,眸光缓缓流转时,泛着高贵而迷离的素辉,难以形容的内敛的忧郁,让人由不得便心生怜惜;我的眸子却年轻灵动,如一汪山间奔流的清溪,转动时几乎可以听得到泉水的轻快潺潺声,若抿唇一笑,更让那泉水蒸腾出氤氲的酒气来,熏人欲醉。
凤帏深,谁道是销 魂(二)
我的脸型较小,下巴略尖,唇是小巧的红菱状,若不玩不闹时其实看来很是安静娇柔,所以会给人一种性情温顺的错觉。示人以弱,应该不难吧?
可示人以弱,真能避免我未来的噩运么?
铜镜中那小巧的红菱唇渐渐颤动,手中也不觉用力。
忽听“喀嚓”一声,手中连珠花纹的檀木梳断了,尖尖的梳齿扎入掌中,颤巍巍地在血肉里抖动,殷红的鲜血缓缓浸润入木质的断齿中。
随侍在房中侍女犹豫了一下,终于上前来,帮我拔出断齿,拿帕子给我拭去鲜血。
我盯了一眼她那不咸不淡的神情,自己用丝帕缓缓地缠绕着。天青色的丝帕,绣的是青翠兰草,印上一排四五个血点,慢慢洇开,顺着丝线延伸,如缓缓绽开的蔷薇。
正冷冷看着那血花开愈艳愈烈的时候,外面传来匆匆的脚步声,目光轻扫,已见着吴德略弯了腰,领了一群人过来。
“管公公,请!”吴德侧身闪在一旁,将一个北朝装束的内侍总管模样的人引入。
他们身后尚跟了数名侍女,个个身材高大,看来竟比江南的男子还要健朗几分。我也曾听说过北方人比江南人要粗犷些,可也不至连女子也全都高大成这样吧?
那个瘦高个儿的中年内侍,吴德称为管公公的,正略带疑惑地望着我。
想起吴德可能向魏帝编排我的“劣迹”,我在气闷中顿悟,这些高大侍女,怕是特地选来对付我的!
以弱示人……
敛了丝帕,我站起身,带了畏怯,往后退了一步,背脊用力靠上了妆台的边缘,硌得生疼。
“吴大人,这是……”我惊惶地睁大眼珠,将指甲将方才刺破的肌肤上一抠,疼痛之中,泪影顿时泊起,含在长睫前,随着我的眼珠转来转去。
几名侍女已走到我跟前,个个牛高马大,我本就继承了母亲的纤巧单薄,加之身量尚未长成,才不过她们肩高,这样泪光盈盈地地和她们站作一处,我不知道会是怎样一种对比。
那中年内侍眼光只在我脸上一转,已指住我问吴德:“这位就是南朝那位能舞刀弄剑的文墨公主?吴大人,你没弄错吧?”
看来吴德还怕我一怒刺杀魏帝,说得比我预料得还要夸张。依旧凝着泪,我瞧向吴德,倒要看看他怎么说。
吴德也正盯着我,眼底迷惑中带了警惕,到底不好再改口说我心机深沉,只得干笑道:“咳,到底大国威仪,咱们公主也敬惧几分哪!”
魏是大国,齐是小国么?南北对峙已有百余年,若真有甚大小之分,北朝怎不将南朝吞并了去,反而诸胡内斗,比南朝要更混乱几分?
凤帏深,谁道是销 魂(三)
若是以往,我早该以公主的身份指着吴德斥骂了,但我如今只是看着,带着泪光悲哀地看着这个齐国使臣,为了保住能让他们吴家富贵绵长的太子,在魏国的阉竖跟前丢尽了大齐的颜面。
吴德已走上前,维持着干笑向我依礼参见:“公主,这是魏国皇帝身畔的管公公。”
那中年内侍已经堆上笑来,屈身行礼:“公主,老奴管密,见过公主!”
“快……快请起……”我小心地望一眼吴德,又往后退缩了一步,轻轻道:“以后还要管公公多照应呢。”
管密起了身,瞥我一眼,依然笑着,声音越发地柔和:“公主,这便请公主移驾,前往皇上驻跸之处吧!”
明知祸事,却躲不过。
我顺从地应了,我握了帕子拭了拭泪水,勉强向吴德一笑,柔声道:“吴大人,回去转禀大皇兄和皇嫂,让他们好好保重身体。阿墨会记挂他们,永远记挂着他们!”
说到最后一句时,我差点隐藏不住自己的恨意,嗓音尖厉起来,忙将丝帕捂了唇,只作强忍着呜咽,然后丢开一脸茫然的吴德,当先踏出了房门,那些本打算抓住我或捆了我走的侍女,只能垂了手跟在我身后,看来的确像是我的侍女了。
据说广陵目前驻有十余万北魏兵马,但魏帝拓跋轲所住的原广陵府衙中并未见到多少官兵,仗剑执戟的卫士却是不少,看来身手俱是不弱。
我虽有侍女随行,但北魏显然信不过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