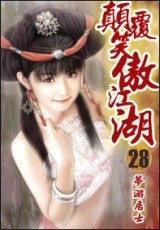江湖草-第1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胡青一副如痴如醉的打着拍子哼着小调听着对面一男一女的一弹一唱。
小蝶表面上漠不关心内心却是打翻了鼓在狂跳着。她不还在怡红院吗?听说她已经投入苏三娘门下,不去接迎宾客,来这酒楼弹唱作甚?旁边那手抚古筝的老人又会是何方高人?可是,等一下,她们到底是真人呢还是别人容易假扮呢?小蝶虽不擅长易容术,但一般的雕虫小计在她眼底招然若揭,瞬间便被识破。可是此时这个飘絮,身上脸上,举手投足,几乎都没有一丝破绽了。跟真的一样。
小蝶摇摇脑袋,七分醉意袭了上来。她看了看旁边,胡青趴在桌上已睡得象只煮熟了鸡蛋,她心下暗叫一声不好,只觉得眼皮沉沉的,琴声淙淙入耳,她脑里念着她不是有什么忘记了的东西,只是好想睡好想睡,挣扎着挣扎着,眼皮缓缓的合上了。
那的确是飘絮没错。那个弹琴的人是她花钱在路边雇用的。
“死人,别装了。”她轻轻地推搡小蝶的肩头。飘絮小心地俯在她的耳边,假装低头讨赏钱。
“听着,我现在是偷跑出来的。我看到妹妹了,现在已经落入苏三娘的手中。有消息再跟你联系。”
飘絮收拾起行头,匆匆离去。桌子上趴着的黄小蝶也不知是真醉还是假醉,一动也不动,衣裙随风飘起,任由晚风吹抚。
15。恶人.贩子
黄小蝶和胡青是贼,是一条线上拴着的两只蚱蜢,也是穿一条开裆裤的兄弟。她们既瞧不起富人,又不屑与穷人为伍。他们憎恨恶人,但又鄙视好人。说穿了就是除了他们自己外,他们谁都瞧不上。他们偷过的金银财宝足可以买下一个国家,可他们有时连敞开肚子喝酒的钱都摸不出来。他们经常劫富济贫,哦不,是偷富济贫,方式不一样,本质一样的嘛。他们从来不愿意让人感谢他们,甚至不让那些受助的人知道他们尊容尊姓。他们经常努力地使自己看起来象坏蛋,然而他们即便是小奸小恶的施坏,也要求拥有绝对的深度和宽度。这正是他们沾沾自喜的地方。江湖,原本就是一个是非难说,善恶难辩的地方嘛。好人怎么样,坏人又怎么样?有区别吗?谁又来告诉他们怎么去区别?
但是,是个人都知道,做贼,哦不,是牵羊大盗,是没有钱途的。毕竟是见不得光的职业。
这个世道,最有钱途的职业是强盗,明张目胆地抢。而最吃得张开的人是恶人。明目胆地恶。
越恶便越受欢迎,越恶越受人尊敬。术业有专工,要做个十恶不赦的恶人,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沙风堡就是一个云集各类五色恶人的大本营。这里的恶人拉帮结派,恶人形成集团化,组织化,智慧化。
沙风堡的大当家花匠和二当家铁匠,就是凭着一副杀破狼的胆量和老子天不怕地不怕的狠劲一步一步爬到而今当家的位置。其实其中很多人都不知道,为了让自己做个优秀的恶人,他二人不知道吃过多少苦,历经过多少痛苦的内心折磨。就拿大当家花匠来说吧,他是喜欢种花的。种花的男人都是心慈手软的好男人
可是,在这里,慢慢吞不行,心慈手软不行。他不得不把自己逼成那么一个样子。蓄起胡子,身披胸毛无数;手拿大刀;说话时撩出又黑又长的腿毛,动不动就对底下兄弟拳脚伺候;管他眼前是肉是人就一刀地砍下去,象砍西瓜一样。说话一开口就是极具粗鲁的漫骂,这群龟孙子,愈是这么凶恶,他们就愈是崇拜。
他也是被逼无奈啊!这不,就因为一个下人把他泡了一天的袜子不小心倒掉了,他正火冒三丈,也不管手中的猪脚就朝下人脸上拍了去。而且还不许躲,老大发脾气谁敢躲?老大切脑袋就跟切菜啊,一个不合适轻则残废,重则小命呜呼。
谁让老大这么有个性了!他们打心底眼里崇拜着呢。可花匠却私底下曾跟老二说过,兄弟们都以我为榜样,我当个龙头哥,却要我六亲不认,我容易吗我?
丐帮张无牙私下里派遣人打听到,沙风堡竟在贩卖人口。
瞎?贩卖人口算什么?杀人放火,奸淫虏掠对他们来讲;就跟喝饭喝水拉屎撒尿一般,家常便饭嘛。
这帮暴徒。张无牙恶狠狠地咬牙切齿,义愤填膺,激动不已。正当想把此消息告知歌,哪知道庄歌的话让他的愤怒转为揪心的疼痛。
“什么?白小兽不见了?”张无牙扭曲的脸岂是大惊失色能以形容的。
“昨儿夜里就没有见到人了。这丫头平时弯弯肠肠的,也没在意。今天也没有见着人,才知道事儿坏了。”庄歌真是沉得住呀,此时还那么双手抱胸神定气闲的。也许这天下就只有一个人能牵动他的铁石心肠吧。
“莫非是这帮捱千刀的人贩子所为?我一把火烧了他们。”真是想什么事儿来什么事儿。
“不行。若真是落他们手里,岂不是打草惊蛇。白小兽那条小命还能活吗?”
可是……那怎么办?她一个小姑娘家家的,落入这帮人手里,会发生啥事我不敢想象。
张无牙真坐不住了,早没了形象地在室内乱转圈子,活象只热锅上的蚂蚁,急得片刻也静不下来。若不是庄歌抓住他的肩膀,早冲去找沙风堡算帐了。
这小子分明是喜欢上了白小兽。男人只有对心上的姑娘,才会有这种在意。
庄歌笑笑,却故意不去点破。只因情这东西是毒药,毁人不倦啊。
“风沙堡贩抓那么多人,都卖到哪儿了?”庄歌倒是对这件事更感兴趣。
你!张无牙气结,他的眼睛如果能够发射东西,只怕无数利箭早就已经毫不留地将庄歌射蜂窝了。
冷静,冷静,保持形象。庄歌伸出手,象拍小弟弟一样拍拍这个情绪不稳定的人。“以我对白小兽的了解,想卖她,还没有那么容易。”
形象二字倒是立马把张无牙拉了回来,哎呀,他立马跑到镜子面前,仔细地梳理头发,“对,不能乱,一乱就不好看了。”他对着镜子左照照,右照照,竭力冷静下来。
深夜,月落乌啼。叩叩。三声为暗号。
庄歌静候在窗外。张无牙从屋内走过来,“你无须如此慌张,当我听暗号时,就从床上起来,照了镜子,泰然自若地穿衣服,我觉得眼带不合适,就把它解下来,又换了一条,没有丝毫慌张!每当重要事件发生,记住,一定要镇静,镇静!”
“那真是太好了,”庄歌说,“那你为什么不穿裤子呢?”庄歌摇头,一个情窦初开的傻冒儿。他后悔要他带出去了。
“眼带,记住夜行一定要带眼带。这才象个夜行侠。”一路里张无牙的话出奇的多。听说有糗事的人通常话都比较多。意在欲盖弥彰,可通常他们都不知道,有些事情是愈描愈黑的。象只苍蝇,还绿头的。
沙风堡。“当家的,洗脚水来了。”下人谄谄地笑着,端过水盆。“贱人。”花匠一边看自己的指甲,一边皱眉头。噜,他伸过满毛腿,脚尖向下人点点。
“呕。”下人极力捏住鼻子极力忍住那股味道。小心地伸出手,为那只恶心的脚*服,屏住鼻息不敢出气。
嗯,舒服啊。花匠将脚放进盆里,呼呼过瘾地闭上眼,享受起来。那下人将手轻轻地伸下椅子下的一串钥匙。东西到手,下人一声不响地退下。
“呕。”庄歌同情地帮张无牙拍拍后背。“到手了吗?”张无牙痛苦地伸出那串钥匙。老天,为什么倒霉的事总是我?
为什么呢?呵呵,总得有人来做这个角色,不是吗?
……
机敏地晃过几个警戒,小心躲过花园里以及阁楼上的几个暗哨,庄歌和张无牙躲在一丛茂密的矮树下,眼前二个守卫或站或靠,在厢房外吹牛聊天。庄歌朝张无牙打了个眼色,当一声往水池中丢出一颗石子。谁?警卫神色一警,循出声处追索去。屋内传来声势浩大的鼻鼾声,张无牙皱了下眉,这个龙头大哥入梦得也太快了些。
“走。”庄歌双脚一提,便闪出一丈开外。大侠就是大侠,随时都这么酷利落的同时,不用装都能这么酷。
张无牙将钥匙在门上轻轻一弄,铁锁卡一声打开。二人迅速闪进房间。龙头大哥的书房也不过如此,还自称恶人呢,竟然把自己的屋子弄得跟个装闺房似的。一屋子的芳香扑鼻,各色名贵兰花争吐芬芳。庄歌四处盘查了下,张无牙向他耸耸肩,他们并无发现什么有用的线索。失望之时屋后竟传来说话声。
“今晚你又得忙一趟了!还是在李码头。”此人说话听起来象个小头目儿。
“是。下属这就带人去相助。”听起来似乎是大动作。
同样低迷的夜,月朗星稀,因探险添了些深不可测的神秘,只是张无牙想不明白为什么要把美丽的脸蛋摸上灰,这样活象个张飞。一点美感都没有了!
“专心走路,不要东张西望。”庄歌就象个监工,眼明如炬,专揪开小差的份子。他们赶在那帮人的前面,脚踩疾风。
张无牙只有跟着他左转右旋的份,不足半柱香,繁华的街巷已隔了很远,尤如如巫山云烟,被远远地甩在身后。张无牙抬头,天上星光点点,这地方他不熟!几乎是出自本能的,一路上,他还没有忘记了要记下天上的标识。生存,自我生存,这是丐帮的弟子要掌握的第一本领,也是最大本领。他们在夜色里向城郊渡口悄然摸进。张无牙很识相地紧闭起嘴。他也感觉到了一丝浓郁的危险讯号,他们绝不是一般的小探险,绝不是。
江南的河大多涓秀清丽;而这李码头却因地处三角地势而异端的波澜壮阔。至此汇流后,这些无情的水将带着如烟往事与雄雄抱负,浩浩荡荡地直达东海。当白茫茫的河泛射刺日的白光印入眼睑时,张无牙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
一只停泊的大船象巨鸟展翅一般伸起巨大的帆,船上船下人声鼎沸,无数带着脚链手链的男人女人象牲口般被另一些人鞭斥棒喝;他们拖着沉重的步子向船仓缓慢行进。
“天啊!他们在干什么?”张无牙趴在庄歌身边,压低声音的声音里有抖音。
“贩卖人口。”庄歌的声音压得几乎只有他面前的草能听到。
“这些人都是从哪里来的?要运到哪里去?”
庄歌哪能回答!他也想知道。他眼里迸着隐隐愤怒的火星子,旁边的张无牙如果侧过头就能看到,它们象燃烧的复仇天使,迸出熊熊的火焰。
庄歌也许是个严肃的人。严肃的人都比较认真。张无牙如果能近距离地回一下头,就可以如此地鉴定出他。他们各自猜测面前发生的事情。然而张无牙是个感性的人,有点自恋,有点臭美,但心地善良,他的世界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小得他只能顾及到自己的情绪。不是除强扶弱,不是的打抱不平,不是拯救那些可怜的人,而是那才刚萌出新芽般鲜嫩美好的爱情,当然是关于白小兽的。
但他什么都没敢说,因为一个黑衣服的监工,吹着口哨向他们这个方向走过来了。他朝他们趴卧的方向一步一步靠近,在离他们脑袋一步的地方停下。这死人竟伸手扒开裤子。漱漱漱,一股骚臭的液体冒着热气哗啦啦地泡在张无牙的脑袋上。庄歌将手死死地摁住那颗挣扎的脑袋。张无牙咬住拳头,忍住!忍住!
可是,实在太臭了,还冒着热气!男人啊,大丈夫啊!孰可忍,孰不可忍!张无牙猛地站起身,撒尿的男人还没有弄明白怎么回事,已经哼哼倒地。庄歌收起横劈的手掌,迅速将他拖至低矮处。
张无牙在月光中沮丧地抬起了头,脸上一阵抽畜,嫌恶地抖搂身上的衣服。“好衰啊!好臭啊!”为什么每次都是我?他悲状地抗议。
庄歌的脸也是抽搐的,可他用一种得内伤的方式忍隐着。此时不是笑的时候。
船上还有一帮凶神恶煞的恶人,身着异族服装,肥硕的鹰勾鼻,身着类似于波斯人的宽厚大袍。他们中偶而有几个凑在一起,叽叽咕一阵,又速度散开。很显然这是一只经过专业训练的团队。
“不能让他回去了,”想起他们对那些目光吊滞,疲惫痛苦的人动则拳喝棒斥;无半点怜悯之心,可怜的白小兽没准也在上头呢。张无牙气愤得鼻孔直冒气,象只被击怒的公牛,双眼泛红了,他泄恨地又朝那具失去知觉的身上踹了一脚。
“留个活口。”庄歌不得不提醒他,变得有点不耐烦,白小兽的朋友怎么都这么冲动?
那边有动静!沙风堡那拨人终于抵达了。浩浩荡荡的,约摸有二三十个精状蒙面大汉,个个膘肥健状,武孔有力。张无牙乖乖地收敛起声音,嘴巴张了张想说话,庄歌的一个制止,他只好闭上,大气不出。
“阿迦逻,请先停下。上面有话交待。”蒙面的带头人大声向船上喊话,是先前在沙风堡听到的那个声音。
一个波斯人双手合拢,欠身施礼。“请问还有何事?”不似普通的强盗,而是傧傧也礼的强盗。愈来愈复杂了,庄歌眉头结皱。
蒙面带头人走近那波斯人耳语一阵,庄歌用力摒息,全神以注,排除其他干扰,只能是断断续续地听他说什么“死城”,咒语什么的。
那二人似是说完了,也听完了,并且双方有些僵持。而后那波斯人摇头,再而后似乎经过了一些权衡后不得不让步,再然后他们似乎达到了某种妥协。
“那后悔有期了!”蒙面人抱拳人辞状;波期人欠身双手合十还礼。只呼几口气的工夫,那帮浩浩荡荡的人人状浩用无比轻灵的声音消失在旷野上。
波斯人上岸,船工船手各就各卫,大帆高扬,起锚,开船。张无牙眼睁睁见一船的人被带走。他挣脱开庄歌的制钳,咬咬刚才被捂死的嘴,现在都变形了。“你为什么拦我?白小兽在上面!白小兽在上面!”他沮丧地欠身。他当然知道,他怎么能不知道呢?以他们两个个的力量,何以跟一船的强匪抗横?
只是那只船,会开向何方?白小兽又会身在何处?会遭遇什么事情?谁人能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