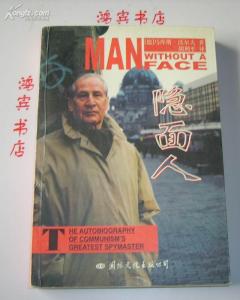隐面人─原东德外国情报局长回忆录-第3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和平时期处死间谍其实是没有道理的。我经历过的叛逃事件中既有东德人员,也有西德人员。今天仔细想一想,觉得死刑起不了什么威慑作用。一个人投敌的动机很复杂,通常还掺杂了本人的一种自信或自以为是的心理,觉得自己可以瞒天过海。
至于臭名昭着的“湿活儿”,即谍报这一行内秘密处决的做法,这种事的确有过,而且今天也照样有。我在这里…一举出在中央情报局手下失踪的人的例子无异于引火烧身,反会被人倒咬一口,指责我如何隐瞒苏联谍报机构的多次不法行为。50年代时期,保加利亚和波兰的谍报机构素有冷面杀手之称。东德的反谍报机构在这方面也不干净。这里我要再次说明一下,流传甚广的绑架处死叛逃人员的事件其实多半是绑架时强力安眠药用多了的结果,而不是蓄意谋杀。
可以说,杀害叛逃人员是虚弱而不是强大的表现。对于这种水平极低的勾当,我不屑一顾。间谍小说里绘声绘色描写的湿活儿其实是一种很笨的办法。相比之下,我们对莫伊茨海姆这样人的利用要高明实惠得多了。先把他当作双重间谍,以后又变成三重间谍,从而得到最佳结果。我们的过失在于利用了人性的弱点和贪婪。然而这样做的并非东德谍报机构一家。 库龙为我们干事非常认真,常常在合同规定以外的事上帮助我们。鉴于他的价值极高,我特别做出安排,无论白天黑夜他都可以通过一个专用电话号码找到我们。遇有紧急情况时,他可以随时通风报信。库龙在西德反谍报机构里深受信任,可以接触到西德策反东德特务的大部分机密。通常他先不哼不哈,静以待观,等西德方面得手后再通知我们。过早地打草惊蛇会引起西德的疑心,于他于我们都没有好处。
只有一次例外。几十年来,我们在波恩的基督教民主联盟里……科尔的党……有一名间谍。早在科尔在莱茵省从政时期,他就是科尔的一位老朋友。此外,他还兼为弗利克大企业集团做事,从1981年起一直作为该集团的代表游说执政的基督教联盟政府。波恩的政界与产业界之间的那些肮脏勾当他全知道,不失为我们了解西德国内政治内幕的宝贵渠道。
一天夜里,正在反谍报机构总部里值班的库龙听一位同事说,一名东德间谍嫌疑犯与这位政治鼹鼠接头时受到跟踪。两人走进一座公寓楼后,西德特工人员布下天罗地网,很快就要动手收网捕鱼。库龙立即意识到,如果两个人当场被抓获的话,我会失去一个在西德的极有价值的政治消息来源。他于是当机立断,拨通了紧急电话号码,用暗语通知我们:“你们的人在安德纳赫大街受到监视。”我们采取了极其冒险的做法,直接给两人所在的房间打电话,用一种口音假称拨错了电话,实则是通知他们逃跑的暗语。
我们判断,现在监视他们的人已经快下班了。另一拨人午夜后换班。如果动手抓人的话,应该是凌晨时分。两人于是假装熄灯入睡。午夜刚过,我们的这名间谍通过地下车库逃出大楼,经瑞士回到东柏林。第二天,这位鼹鼠离开公寓后,西德特工人员冲进房间捕人,哪里还有那个不速之客的影儿,也没有找到任何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
日后这个鼹鼠终被挖出,受到审判并被判处短期徒刑,缓期执行。鉴于对其他鼹鼠的判刑都较重,我猜想波恩政界里一定有他的熟人替他求了情。
连续6年,库龙向我们提供了一流的情报。在他不知情的十几岁的儿子的协助下,库龙想出一种办法,以极快的速度把计算机信号录在普通录音电话的磁带上,从而大大改进了我们以前的方式。过去发报时加密过的字母发出的僻僻啪啪的声音很容易被对方的反谍报机构监听到。库龙的办法大大加快了传音的速度。人耳听上去不过是声音略有一点走调,或是一两下短促僻啪声,和电话线上的小故障没什么两样。在另一端,库龙发出的信号通过编好的电脑程序转录到一盘磁带上,然后以发报速度的几分之几放出并解译。库龙后来又研究出一种更简便的办法,发出的信号可以直接转到一张电脑光盘上。我们这边的分析员只需插入光盘,经过许可后,即可直接从电脑荧光屏上看到发来的情报。这将译码所需的时间又缩短了宝贵的几分钟。
我们与库龙之间卓有成效的合作一直持续到1989年。它表明,如果一个谍报机构内部管理不善,技术上的优势是有限的。技术知识可以用钱买到,而出色的组织、严明的纪律和正确的直觉是买不来的。例如,库龙周围的同事本该觉察出,他的消费水准超出了他的收入。这种迹象以后越来越明显。不过库龙不像艾姆斯那样花起钱来大手大脚,而是极其小心谨慎,总是找出各种借口做掩护。他同我们联系时做得很漂亮,丝毫不露马脚。平时生活也很节制。此外,科隆西德反谍报机构总部里的保卫处处长蒂德格是个酒鬼,家庭生活一团糟,还因赌博欠了一屁股的债,哪里还顾得上库龙。
1985年夏天,我打点好行装正准备去匈牙利度假时,电话专机响了。电话是从与西德接壤的马格德堡专区打来的。一个自称是塔贝尔特的男子不邀而至,要求见外国情报局的人。库龙早已告诉过我们蒂德格的化名是塔贝尔特。我下令不要再盘问什么,从速把他送到柏林。想到边防人员通常对访问东德的人很不客气,我又嘱咐给他一瓶啤酒并安排他用餐。卡尔·格罗斯曼专程去通往柏林的高速公路路口接他,以确保他坐的车穿过柏林市时万无一失。格罗斯曼曾成功地跟库龙打过交道。他主管的第9处已渗透到西德的反谍报机构里。
我知道这回送上门的是一条大鱼。西德方面一定不会善罢甘休,肯定要千方百计把这位重要的谍报官员弄回去。蒂德格叛逃我方极有可能是一时冲动的心血来潮。我们在位于东柏林附近乡间的普伦登为他找了一幢安全住所,安排他住下。我自己的乡间别墅也在这里。几百米外就是为政治局成员修建的地下掩蔽室。如果美国人真的扔原子弹的话,政治局成员可以躲到这里。这一带岗哨林立,戒备森严。西德谍报机构要想把我们这位新朋友从这里抢出去简直比登天还难。
蒂德格想直接见我,但被我婉拒了。当时我正准备退休。考虑到这是一桩大案,波及面会很广,我想最好还是让接替我的维尔纳·格罗斯曼接手此案。我感觉,首先出面接待蒂德格的人会赢得他的最大信任。由格罗斯曼直接处理此案可以避免中途再换人。
我们的人温和地盘问了蒂德格。他看上去狼狈极了,一副不修边幅的模样,眼睛布满红丝,一点不像是西德谍报机构的高级官员。为了不致搞错,我们要他出示身份证。身份证证明他确是联邦宪法保卫局的成员。他自我介绍说,他叫汉斯约阿希姆·蒂德格,并且解释道:“我是来投靠你们的。”我打电话告诉了米尔克这一好消息。即使是听到敌国重要人物叛逃过来的消息,米尔克最关心的仍是他的地位。他极为不满地抱怨安全部在马格德堡专区的头头没有马上通知他这一消息。“今后,凡属失物招领情况的,一律先送到我这里!”他用带有浓重柏林口音的粗哑嗓门厉声说。
蒂德格证实了我们从库龙那里了解到的有关他沉沦的情况。他染上了赌博和酗酒的恶习。一次,他和妻子在家喝醉酒后打架,妻子不慎丧命。事后对他进行了调查,看是否应接杀人罪对他提出起诉。最终他妻子的死被定为意外事故。他的几个孩子因为母亲的死一直对他怀恨在心,根本不眼他管。工作上,他因为个人生活无度受到处分。他心里明白,让他留在反谍报机构里的惟一原因是为了堵住他的嘴。在上司的监视下,他不至于把知道的机密讲出去。蒂德格觉得自己已丧失了基本的尊严。“假如上面就一个类似我这种情况的人问我的意见,我会建议立即开除他。”他坦承道。
我后来阅读盘问蒂德格的记录时,不由得产生一种感觉:堂堂一个西德谍报机构里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头子更像是电视肥皂剧里的人物。按理说,于这一行的人应该洁身自好。而眼前这个人精神上完全垮了。对他来说,只剩下两条路:要么自杀,要么叛逃。“可我没有勇气自杀,”他坦率地承认。
许多人对蒂德格的叛逃感到扑朔迷离,怀疑他早已叛变。我可以首次明确地说,他叛逃前不是我们的人。对蒂德格逃到东德的举动,我和其他人一样感到惊奇。我倒有过一种预感,没准儿哪天他在科隆实在混不下去了会跑到我们这边来。但我们并没有主动去找过他。是他一天晚上搭乘火车跑到东德找到了我们。蒂德格是个少见的说话不转弯的叛逃者。他可以说是我遇到过的惟…一个称自己是叛徒的叛逃分子。他不想用什么改变信仰之类的托辞为自己的决定涂脂抹粉,而是直截了当地说:“我在第二个德国日子会比在第一个德国好过点儿!”此话干真万确。我们为彻底治愈这个踉跄跑过来的酒鬼煞费苦心。当初刚把他带到安全地点时,他体态臃肿,面色苍白,眼睛周围一圈深深的青晕,看上去活像一头大熊猫。我们给他派了一名医生,一名护士,外加一名健身教师。在他们的帮助下,蒂德格戒了酒,1个月体重减了30磅。由于再也喝不上酒,平时又严格按照减肥食谱控制饮食,他需要从其他方面得到慰藉。我们发现他的性欲极为旺盛。波茨坦地区有一些女党员是当地谍报机构的关系户。她们会应我们的请求与对方叛逃过来的人交朋友,谈恋爱。这种事经常发生。大多数男人在审查期间精神上受到极大压力,需要女性的关怀和体贴。我们确保请来的女同胞已做好与这些人发生性关系的思想准备。
她们不是什么妓女,而是为人实际,忠于祖国的女党员。为换取我们过去称之为的祖国对她们的答谢,比如分到一套较好的房子,或是等待买车的名次排前一些,她们愿意做这种事。尽管如此,我们请到的第一位女士没呆几天就因受不了蒂德格而逃之夭夭。第二个是位女教师。她总算坚持了下来。我们不禁松了口气。蒂德格这种男人极不讨女人喜欢。记得当时我曾想,这位女教师爱国爱得可真够意思的。不过即使是最让人恶心的故事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愉快结局。蒂德格与女教师后来结成伉俪,直到我写此书时还生活在一起。
蒂德格有着电脑一般的记忆力,各种人名和他们之间的关系过脑不忘。他填补了我们的许多空白,但并没有他本人以为的那样多。他哪里想到,他的同事库龙也是我们的人。蒂德格叛逃后。新闻界披露了他在任期间的种种不称职行为。西德反谍报机构的形象为此一落千丈。不仅如此,蒂德格在反谍报机构里的上司和老朋友.新上任不久的联邦情报局局长海伦布罗赫在指责反谍报机构内部人员不称职的浪潮中被迫辞职。看着西德那边乱开了锅,我们开心极了。不过后来我感到海伦布罗赫在西德情报机构中还是一位较正直的首脑。想到我手下不是一位,而是两位鼹鼠拆他的台,一丝同情油然而生。
蒂德格逃到东德后,我们有了收拾加劳这对夫妇的借口。库龙早已告诉我们,这两个人被西德收买。由于不想让西德觉察出自己内部有个鼹鼠,我们一直没有动这两个人。现在西德反谍报机构会觉得是蒂德格出卖了他们。加劳和格林德双双被捕。1986年12月,加劳被判无期徒刑。格林德4个月后被释放,但受到警告不得对任何人提起过去的事。1988年夏天,她丈夫死于包岑监狱。格林德硬说是我下令杀死了他。
事实并非如此。加劳是一个性情敏感,自尊心很强的人。阶下囚的日子尤其让他难以忍受。我相信,他是在得知他的名字没有列在西德要求与我们交换的间谍名单上后才在狱中自杀。由于他先后被自己信任的西德谍报人员出卖过两次,人们后来对他萌生怜意。可在我眼里,他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间谍。虽没有死罪,判他坐狱一点不冤枉他。 1990年10月5日,两个德国统一后的第三天,库龙来到东柏林与我手下的一位高级官员讨论他的去处。当时人们争相自保,背叛事件层出不穷。我手下的一名爱将抵制不住西德方面的诱惑,答应帮他们破获我方的间谍。此人正是当初发展了库龙,接待了蒂德格的卡尔·格罗斯曼上校。出卖他人的人最终轮到自己被人出卖。奉命保护我们在西德反谍报机构里的两名头号鼹鼠的人结果自己也成了叛徒。面对眼前的一幕幕,我感到一种被嘲弄的苦涩。
格罗斯曼的背叛意味着库龙和为我们干事的其他重要间谍的戏已经唱完了。库龙本人也明白这一点。他默默无语地从我们的一位高级官员手里接过付给他的最后一笔钱10000马克,并同意接受东德外国情报局当时为保护它的炭发可危的间谍所提供的力所能及的帮助……把他介绍给克洛勃。在苏联谍报机构的协助下,或许他可以逃到莫斯科。
苏联当时一门心思改善与西德的关系,对我们极为冷淡。接替我任外国情报局局长的维尔纳·格罗斯曼与他们反复交涉,刚柔并用。最后克格勃终于同意,我们的重要间谍中的任何人只要愿意,均可去苏联避难。库龙最初同意去苏联,时隔不久又改变了主意,担心一旦去了苏联就再也出不来了。
库龙佯称需要回科隆与妻子商量一下是否去苏联。一到科隆后即给西德反谍报机构的保卫处挂了电话,称他有要事相商。他打算再要一次花招。他告诉上司说,克格勃想拉他做间谍。他提议以双重间谍的身份为西德工作,帮助西德反谍报机构了解苏联人对什么情报感兴趣。长期以来这正是他为我方做的事。在当时库龙面临的压力下,一个曾克服了巨大心理障碍投靠敌方的叛徒往往会再次回到自己人一边。危急关头库龙试图孤注一掷。不过这一次他的运气到头了。
库龙刚来到自己工作多年的科隆反谍报总部的办公室,即被拘留并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