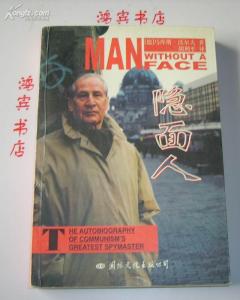隐面人─原东德外国情报局长回忆录-第1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严重脱离群众。英国人一向认为他们先发现了诸如劣质消费品和官僚习气这类现象。
我觉得很可笑。菲尔比在莫斯科难得有机会与文化修养很深的人交谈。但我不同意西方称他在莫斯科度日如年的说法。不错,除了莫斯科他无处可去。但菲尔比比其他间谍更能随遇而安。
我感觉,克格勃安排菲尔比、布莱克这样的人去生活水准远远高出苏联国内的东德和匈牙利等国家度假,是为了减轻他们内心的压抑。克格勃无时无刻不在担心,这些西方要人有一天会逃回祖国,令莫斯科丢尽面子。他们若想逃走的话,并不是很难。菲尔比告诉我,在莫斯科的英国情报机构就曾通过种种途径几次邀他回国。
菲尔比喜爱东德的乡村。每次他来东德时,我俩都要山南海北地聊上一通,谈书,谈思想,甚至谈烹调。我俩一起动手包俄国饺子,然后比较各自饺子的特点。包这种饺子,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口味可以放进自己想吃的馅儿。一次度假结束后,他送给我一本他写的回忆录,扉页上写着:“尊敬的沃尔夫中将同志惠存。逗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期间,承蒙热情款待,不胜感激。金·菲尔比。”这本书是西德出版的。他又在后面补了一句:“联邦德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版本的翻译水平大有改进之余地。金:”也许他觉得向东德外国情报局局长赠送礼物时出于礼貌应当批评西德几句。无论出于何种目的,我觉得后面补加的一句话很有趣。它反映了菲尔比一丝不苟的学究气。
在世界情报史上,菲尔比和布莱克属于悲剧性的人物。人们对他们的政治观点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他们事业上成就辉煌。布莱克的遭遇尤其不幸。他不是一次,而是先后两次失去家园。第一次是他逃离英国时。第二次是苏联垮台。他被迫在一个背弃了他所信仰的事业的第二祖国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经历了从西班牙内战以来本世纪许多重大事件的菲尔比先于布莱克去世。也许他是两人中更幸运的一个。我从未因菲尔比背叛他的祖国感到过不自在,因为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出于信念。他从一开始就坚信,苏联这个国家最好地体现了他的反法西斯主义的理想。一生有信仰的人,会毫不动摇地沿着自己选择的道路一直走下去,不管路途上遇到什么惊涛骇浪。当然,每个人为自己选择的道路和追求的目标各不相同。有的人。如阿瑟·克斯特勒,早年追求正义、平等等共产主义的理想,后来因为苏联的种种过火行为心灰意冷。我的老朋友莱昂哈德就是这样。我以前感到很难理解这些人。不过我与他仍保持着联系。我想现在我俩已彼此理解了。
随着冷战规则的逐渐明朗,对方的间谍也不再像是魔鬼的使者,而更像是东西方游戏中的棋子或卒子。一旦落入敌国情报机构之手后,他们更有可能成为阶下囚,而不是刀下鬼。不过处决间谍的事仍时有发生。通常是因为某个政治家想借此向本国人民或敌国表达一种立场。情况的变化使我意识到,交换间谍有可能成为情报工作中的一件有利的武器。我开始更为仔细地研究我方关押的间谍情况,看是否有可能用他们换回西方关押的我方间谍。
通过在国际上代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东柏林律师沃格尔和代表西德的律师施坦格,两个德国就交换间谍形成了一套做法。随着岁月的流逝,铁幕两侧双方交换间谍变得更加容易,即使交换的间谍被判长期徒刑也无妨。沃格尔通过在敌对国之间穿针引线发了一笔小财。
东西方在国际上交换的首位重要间谍是1960年在苏联上空被击落的美国侦察机驾驶员鲍尔斯。这一事件令艾森豪维尔在政治上极为尴尬。由于处理不当,艾森豪维尔与赫鲁晓夫原定在巴黎举行的首脑会议也泡了汤。坐在莫斯科富丽堂皇的工会大厦圆柱大厅的观众席上观看鲍尔斯的审判,一种阴森感油然而生。30年代这里曾是斯大林导演的一系列装模作样的公审的地方。我当时恰好因其他事在莫斯科,顺便想去看看热闹。我坐在硬长条板凳上,头顶上方是彩色粉笔图案的天花板,上面悬垂下来的晶莹闪亮的水晶吊灯更适于舞厅,而不是法庭。
这是斯大林死后首次在大庭广众之下审判间谍。那年夏天,审判鲍尔斯一案是莫斯科街谈巷议的主要话题。普通的莫斯科市民在法院周围围观,想看一眼从苏联空中掉下来的这个美国人。克格勃的同事们小声告诉我,总书记本人打算亲自核准判决书。
鲍尔斯被带到了被告席上。法庭工作人员用俄语向他宣读法庭规则时,他显得茫然不知所措。他长了一张柔和的娃娃脸。每当听不懂提问时,眉毛习惯地拧成个疙瘩,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很招人喜欢。我对这个敌人突然萌生了一丝同情。通过一位毫无表情的翻译,鲍尔斯老老实实地回答了审判员的提问,供认了他任务的性质和派遣他的单位。“傻瓜!”我自语道。
结果鲍尔斯的天真和与苏联方面的合作态度恰恰正中超级大国的下怀,为它们首次交换重要间谍创造了有利条件。鲍尔斯只被判了10年徒刑。我在克格勃的朋友解释说,从轻发落鲍尔斯是向华盛顿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莫斯科愿意交换间谍。
在大西洋彼岸,克格勃上校文贝尔正在美国亚特兰大市的联邦监狱里服刑。艾贝尔的父亲是彼得堡一家工厂的工人,德国后裔。他热忱地投身于布尔什维克事业,几次见过列宁。1947年,艾贝尔(真名叫菲舍尔)奉克格勃之命,来到美国潜伏下来,化名戈德费思,对外以摄影和绘画为职业。他在纽约市布鲁克林区租了一间画室,以此为据点操纵一批窃取美国政治、贸易和军事机密的间谍。1956他遭逮捕,次年被判30年徒刑。1962年2月10日,经沃格尔牵线联系,苏联用鲍尔斯换回了他。
几年后,艾贝尔来到东柏林,向东德外国情报局介绍他的经验。克格勃已提升他为将军,主管苏联在英美的间谍网。除了请他给我们新招收的学员做报告外,我还安排他同我手下的高级官员见了几次面。他可以谈笑风生,就看和谁在一起了。我们互相举杯祝贺各自在情报工作方面的成就,然后聊起二、三十年代的险风恶浪,甚至还谈起我父学的剧本。艾贝尔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人物,喜爱化学和物理,对爱因斯坦尤其着迷。他的画相当有水平。当初他在布鲁克林曾以做画掩护间谍行动。他送给我的几幅小画我保存至今。1971年艾贝尔去世后,他的遗编为了能够在他的墓碑上的克格勃化名下面刻上他的真名,在苏联人面前磨破嘴皮。苏联人保密惯了,哪怕一位优秀的间谍已长眠地下也不例外。
1961赫鲁晓夫和肯尼迪总统在维也纳高峰会议上愤怒交锋之后,冷战出现恶性升级的苗头。赫鲁晓夫回国后向军队发表了讲话,强调西柏林的重要性。我清楚地认识到赫鲁晓夫与肯尼迪争吵的严重性。通过安插在英军驻柏林司令部和北约总部的两位间谍提供的情报,我们获知,针对莫斯科有可能再次下令封锁柏林的前景,美国人正在紧张地准备反措施。我翻阅着根据大批微型胶卷汇集而成的一叠保密文件,意识到任何一方稍有不慎,就可能触发战争。而且柏林将成为这场战争的爆发地点。
1958年,美国当时的国务卿杜勒斯成立了一个绝密的美国机构,起名为活橡树,专门研究一旦莫斯科再次封锁柏林如何反击。该机构最初归属于北约司令劳里斯·诺斯塔德将军。一天,通过我们潜伏在驻德英军司令部的人,我收到一份诺斯塔德将军签署的题为“对苏联意图的初步分析”的文件的主要章节副本。时隔40年后,直到我写这本书时,这份文件在美国仍然没有公开。根据活橡树制定的方案,如果西方在柏林至西德的100英里走廊沿路上受到的低度骚扰逐渐升级的话,即派出一支军车队,以坚持西方进入柏林的权利,并试探苏联的反应。文件接下去提出了更广泛的军事选择,从派出一个由美、英、法士兵混合编成的营沿走廊搜索前进,直至三国以一个师的兵力沿走廊开向柏林,维护西方进入该城市的权利。只有美英法三国军队参加这一计划,因为只有这三家才有权派部队通过东德领土前往它们位于柏林西区的各自的占领区。
我一般不会对什么事惊惶失措。然而活橡树方案却令我不寒而栗。通过莫斯科的消息来源我得知,赫鲁晓夫喋喋不休地大谈柏林,甚至还对美国大使卢埃林·汤普森说,解决柏林问题关系到他“个人的名誉”。他为了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了”。我了解赫鲁晓夫逞强好胜的性格。他的这番话更让我坐卧不安。历史上大国为了维护自己国君易受伤害的名誉多次兵戎相见。
当时我浑然不知,北约活橡树方案在内部遭到强烈反对。许多年后,中央情报局公布于众的文件中透露出,英国国防参谋长蒙巴顿勋爵曾就这一方案警告过肯尼迪:
派一个营沿这条走廊去柏林的结果会是什么?俄国人会在他们的前后方各炸毁一座桥梁,然后卖票给那些寻开心的人前去看热闹。如果说派一个营是一场闹剧的话,派一个师将会酿成一场悲剧。部队行进时为了不至于停下来,需要30英里宽的正面。这将被视为对东德的入侵,并会引发全面战争。
我不禁松了一口气。英国的老兵还没有被铤而走险的活橡树方案冲昏头脑。直到1987年,活橡树的成员才得到北约组织的承认,并获准像其他北约组织工作人员一样,在军装上佩戴有SHAPE字样(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英文缩写)的徽章。该机构一直保留到德国统一后才解散。所幸的是,赫鲁晓夫改变了主意,不想为本质上是一个德国问题冒引发战争的风险。此后该机构在美国战略思想中的地位日趋减弱。赫鲁晓夫开始寻找另一种解决办法……混凝土对策。
第七章 混凝土对策
许多年后,当后人把冷战看做是庞大帝国之间的一场冲突时,当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史书中只是一个脚注时,我的国家恐怕将以修建了一堵阻止自己人民外逃的墙这一事实名留史册。柏林墙不仅将一座名城一分为二,还划分出争夺人类未来的两大意识形态和军事集团。耸立的柏林场成了战后欧洲分裂,乃至冷战本身的残酷与荒诞的最强大象征。
柏林墙建于1961年8月13日。此后,我一直在这堵墙后面生活和工作,致力于保卫和完善修建了柏林墙的这一制度。在我的眼里,这堵墙既是力量的反映,又是虚弱的表现。只有一个对自己的意识形态有坚定信心的制度才能做到把一个大都市分隔成两半,在一个国家的两个部分之间划出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也只有像我们这样虚弱和有着根本缺陷的制度才会有这样做的必要。
1989年11月9日晚上,我打开电视,听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公民可以自由到国外旅行的消息。电视屏幕上,首批东德人正在络绎不绝地穿过突然开放了的边境。我深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末日已经来临。像我们这样一个生存安危全系于国内稳定的国家经受不起这样的冲击。时钟仿佛一下子停摆了。我神情迷惘,和妻子一起看着电视上播放的东德和西德公民在柏林边界的无人区地带互相拥抱的画面。有的人只趿拉着一双拖鞋,好像在睡梦中间人这一即将决定德国乃至欧洲命运的不寻常之夜。
当然,东西德边界从来没有完全关闭过。对于因公旅行的东德人,它是敞开的。这些东德人首先需要经过审查,获得“出差干部”的资格。也就是说,他们政治上是可靠的,在西德没有直系亲属,而且接触不到任何东德的机密。70年代,随着两德关系的改善,东德放宽了出国旅行的限制,允许退休人员出国。这样做是基于以下合乎逻辑,甚至可以说是玩世不恭的考虑:倘若退休人员滞留西德不归,东德经济上不仅不会受到什么损失,反而还可以因此少付一笔养老金。毋需赘言,我们在国外的间谍以及给他们捎信的联络员也可以持伪造证件自由进出东德。
普通老百姓对可以出国的人极为羡慕。在这个没有旅游者的国度,人民极其渴望有旅行的机会。出身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大多数大学生去的地方都比我多。西方的评论员对共产党国家的特权阶层成员说东道西时常常把这一点置之脑后。尽管我有种种特权,却从未有幸光顾过马德里的普拉多博物馆,大英博物馆或是卢浮宫。所有东德人的生活经历都很狭窄,虽然我比别人见的世面多一些。由于情报工作这一行的需要,我先后去过东非,荒漠的西伯利亚,黑海海滨,瑞典的大森林以及具有亚热带气候的风和日丽的古巴。我有一套不错的公寓房子,一部汽车和一个私人司机,还可以应东欧集团内其他国家情报机构的邀请去这些国家度假。但所有这一切总是和我的工作与职务连在一起。到头来,我对外部的大千世界同样茫然无知。
虽然我们连西方普通殷实之家所享有的舒适和自由都没有,但我个人远不至于和普通东德老百姓一样忍受物质生活的匮乏。我们从苏联人那里继承了一套特权阶层享受特殊待遇的做法。这一制度始于1945年。当时政府官员、科学家和其他对共产主义事业有用的人可以多分到一些短缺的物品,我们称为定量供应。以后这种做法形成了一套制度。一个叫“平安”的商店专门提供这类商品,它的店员后来增至5000余人。通过以外贸部为首的一个关系网,我们享受着种种特殊待遇。这套制度的建立是为了保证国家高级官员可以得到比本国生产的常常是质量低劣的商品更多的东西。这套分配制度等级分明。政治局成员有供应西方商品的特殊商店。他们挑剩下的东西给我们情报部门,然后再是其他部委和贸易机构。这一切实行起来十分简单。高级官员的日子为此过得很舒适。面对这些特权的诱惑,我没有力量说不。多年后,学生质问我时,我老实承认了这一点。学生对我的回答感到满意,因为他们理解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