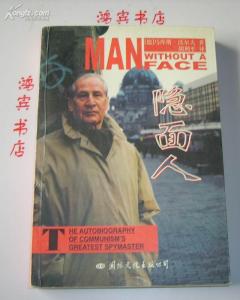隐面人─原东德外国情报局长回忆录-第1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见面前他告诉鲍尔,我是内政部主管经济事务的一位高级官员。我与鲍尔的谈话持续了几个小时。其间我打出了一张又一张牌,但一无所获。无论问到什么问题,他都对答如流。面对我的步步紧逼,他从容不迫。甚至当我揭他的老底,告诉他我们知道他与美国人有联系时,他仍然丝毫方寸不乱。这是我手里握有的最后一张王牌,然而却完全失效了。
这个不修边幅的商人原来是只老狐狸。我这个年轻气盛的情报官远远不是他的对手。由于他与上层社会关系很深,我们不便对他进行讹诈。通过这件事我吸取了一条有益的教训:一名情报人员切忌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实力。
我对鲍尔真实身份的推测很快得到了验证。下一次与施泰因吕克见面的日子到来时,他没有露面。美国情报机构对他进行了极不客气的盘问,并告诉他我的真实身份,警告他以后不要再与我保持联系。施泰因吕克认真记取了这一告诫。以后的岁月里,他继续加深与德国和美国武器商的关系。当初我对他感兴趣的原因也恰恰在于此。
由于我的冒失,结果失去了一个宝贵的关系。施泰因吕克本来可以继续心照不宣地为我们做事。我们经过多年的实践摸索,逐渐改进了收买人的方法。我们认识到,劝说有可能为我们搞情报的人在一份文件上签字是不明智的。不少人出于各种各样的动机愿意与一个敌国的情报机构打交道。若要将这种关系明朗化,他们则会避而远之。他们其实更喜欢一种含糊不清的关系。我告诫过手下的人:如果你觉得对方的回答会是否定的,最好别问。切忌用官僚机构的繁文礼节来束缚活人。多年来,我们逐渐废除了苏联祖师爷热衷搞的形式主义的那一套,并取得很好的成效。
我们还想方设法打入克虏伯这个庞大的军火工业王国并试图争取洪德豪森的同情。洪德豪森是克虏伯厂的董事会成员,喜爱艺术。他似乎比他的其他同事更了解东德。对波恩政府压制两个德国之间的贸易的立场他曾提出过批评。然而我们很快看清了他的意图,他同我们拉关系仅仅是为了替克虏伯捞取好处。
在一次讨论德国统一问题的大会上,我们与维德曼不期而遇。维德曼是德国统一的积极鼓吹者,也是维尔特(魏玛共和国期间曾任参赞)的一位老朋友。维德曼表示,光在口头上反对加强华盛顿与波恩的联盟还不够,并暗示我们资助他在波恩开个公司。我听后十分欣喜,于是和他签了一个合同,其中规定了公司上缴给我们的赢余部分。对我们情报局来说,涉足风险资本投资还是开天辟地头一遭。在我们的资助下,维德曼成立了向固定工资收入劳动者提供经济援助事务所。这是一个游说团体可以在政府各部门和其雇员中开展活动。通过这一渠道,我们与鲁道夫·克里勒搭上了线。克里勒是西德总理府内一个部门的头头,负责防务政策和军事联盟问题。这位极有权势的官员经常光顾我们这家事务所,开怀畅饮莱茵地区产的葡萄酒的同时还透露一些有关德国政治内幕的小道消息。
这次成功刺激了我们的胃口。我们打算将这个事务所扩大为一个非法巢穴(情报行业里的术语,指一项长期潜伏任务)。东西德关系紧张时,它可以成为一个联络点。我们在事务所里安插了一名特工,负责偷录来访官员的交谈,兼接受、处理和向国内汇报情报。我们还吸收了维德曼的女友,给她起了个化名,叫埃里斯。她的上司在西德总理府内工作。不过有一个问题令人难堪。虽然维德曼能言善辩,却经商乏术。事务所的日常开支大大超过了它的收入。这种情况不可能对外界隐瞒很久。我们推断西德的反谍报机构可以看到各家公司的纳税记录。无需多久,它就会纳闷,这家事务所的经费从何而来。一切结束得比我想象的还要快。情报局总部里的一个工作人员叛逃到西德。因为担心事务所里的这名特工会因此暴露,我们把他撤回东德。
所幸还有埃里斯。不过她的上司后来从总理府调到科学教育部。我们对她的兴趣也随之减少。她在该部工作的10年里向我们提供了一些政府资助的敏感的研究项目的详细材料。据此我们制定了自己的窃取科技情报的计划。
50年代初期,除了维德曼的事务所外,还有一位家在波恩的迷人女老板似乎也极有发展前途。查阅东德准备大赦释放的在押西德人名单时,苏珊这个名字引起了我们的注意。1951年她参加莱比锡贸易交易会时,东德反谍报机构以间谍罪将她逮捕并判处8年徒刑。她的档案里职业一栏填写的是自由撰稿人,我手下人因此对她产生了兴趣。一位上校在她尚不知自己即将获释时约见了她。走进接待室,他看到眼前是一位身材苗条的妇女,年龄约在34yo35岁之间,虽身着国服,眉宇间却透着倔强和自信。对于她的被捕判刑,她仍然不服,认为她受到的待遇是不公正的,丝毫不想取悦扣押她的人。同时,她还谈了自己对德国面临的问题以及阿登纳的亲美政策的看法。我们的人问她,是否愿意换个场合继续谈下去。她被释放后,两人再次在东柏林的华沙大桥上见面。她同意回到西德后向我们提供情报。我们给她起了个化名,叫莉迪亚。
令我们欣喜的是苏珊在波恩安了家,还办起了一家沙龙。一些知名人士常在这里聚会,讨论政治和文化。通过苏珊,我们得到了有关西德政治党派中一个极右组织的很有价值的情报。这个名叫救援自由的组织的头目是基督教民主联盟的一名政治家,叫巴泽尔。该组织通过海外人士插手东欧各国,并与奥匈帝国皇室的后代、政治上极为活跃的奥托·冯·哈布斯堡结成同盟。巴泽尔日后爬上了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的宝座,并以此身份与勃兰特竞选总统。他坚决反对勃兰特试图给予东德外交承认的努力,令我们头疼不已。
苏珊被东德逮捕之前曾与任柏林市长的勃兰特热恋过。勃兰特给她写过不少情书。1961年议会竞选期间,勃兰特的政敌,包括施特劳斯向外界泄露了这批信件的内容。以前我们一直把施特劳斯视为敌视社会主义的狂徒。他在公开场合也是这样表现的。苏珊提供的情报促使我们第一次重新考虑对施特劳斯的这种成见。苏珊认为,施特劳斯是一个头脑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她向外界透露施特劳斯和勃兰特约定在她家举行私下会晤时,顿时谣言四起。人们纷纷猜测有可能实现一个大联合,从而社会民主党人战后将首次进入政府。勃兰特在回忆录里证实确实会晤过施特劳斯,但未提会晤的地点以及他与苏珊的关系。
我常常不解,到底是什么原因驱使这位妇女偷偷溜到柏林与我们秘密接头,并向我们提供政治观点跟她更接近的组织和个人的情报。尤其是在此之前,东德曾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她逮捕下狱。她当然明白我们是干什么的。如果她是一名双重间谍的话,她会设法打听我们的情报活动。可她从未问过任何问题。她只收下我们为报销她的开支付给她的钱。除此之外,一分也不多要。为了给她去柏林找一个借口,她还编造出一个家住西柏林的女友。
1961年修建柏林墙后,这条极其宝贵的消息来源突然中断。当时有几个一直向我们提供情报的西德人切断了与我们的联系。她是其中之一。我觉得苏珊这个人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有迹象表明,她开始为西德情报机构工作,并同西德陆军少校扎格纳一起消失在远东。当初苏珊就是从他这里听到救援自由这个组织的名字的。在远东期间,扎格纳先后在几个国家担任西德武官。1968年时,苏珊已在一名叫朗格曼的西德间谍控制的情报网内做事。朗格曼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眼线,欧洲及远东都有他的人。
斗转星移,物是人非。昔日曾帮过我们的苏珊摇身一变,竟成了西德联邦情报局驻香港站的站长,代号150。东京、马尼拉、雅加达和新加坡等地的情报分站均归她管。70年代我们搞到手的西德情报组织的档案材料里提到,她曾一次得到9.6万西德马克的报酬。由此推断,她该不是一般等闲之辈。1968年,克劳斯·金克尔当上西德情报组织的首脑后,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清除冒牌间谍,废止格伦的莽撞做法。尽管格伦之后又换了两任首脑,这种做法仍然十分普遍。苏珊离开了西德情报组织。据说她拿到30万西德马克,条件是不得透露联邦情报局插手西德政治的内情。从此她销声匿迹。直至今日,她到底是哪一方的人,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对我仍是一个谜。
经过施泰因吕克一事的挫折,我悟出了一点:刺探联邦德国政治秘密的秘诀在于四处撒网,广开情报来源,对向我们提供情报的人,要让他们感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右翼方面,我们同京特·格雷克建立了联系。他是一位爱国者,战前曾任国会议员,因反对希特勒坐过监狱。后来参加了1944年试图暗杀希特勒的密谋集团。格雷克的例子说明了为什么一些铁杆保守分子最终和我们站到了一起。他们反对阿登纳企图借美国产婆之手接生一个新德国的政策,与他势不两立。格雷克公开会见乌布利希,以表示他对阿登纳政策的不满。为此他被驱逐出阿登纳的政党。我们仍然与他保持往来,把他作为了解基督教民主联盟圈子内情况的一个重要消息来源。他提供了大量这方面的情报。
当格雷克的助手是英国情报部门的间谍的消息传出后,格雷克认识到波恩当局十之八九也在着手准备收拾他,借此把所有反对亲美政策的人打成共产党间谍,把他们搞臭。事不宜迟。我o]立即通知格雷克逃到东柏林。一直是保守分子的格雷克万万没有想到会有这种结局。不过当时我们话说得很直率,他别无选择。如果阿登纳决定拿他开刀,杀一儆百的话,他在西德也不可能保持社会知名人士的地位。
我们安排他在东柏林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露面。格雷克解释说,他是出于爱国才与我们保持联系。我国领导人对这次宣传上的胜利沾沾自喜,甚至可以说有点得意忘形。从此他们胃口大开,只追求要人叛逃的一时轰动效果,根本不考虑一个没有暴露的优秀间谍胜过10多个弃暗投明的间谍这一点。以前我有一个人,化名蒂姆,真名叫施密特·维特马克。他是基督教民主联盟的议员,负责欧洲安全问题的委员会成员兼基民盟青年分部防务委员会的主席。由于他的地位,他成了工业界巨子们的红人,未来基民盟主席的人选。1954年夏天,我度完假后回来,看到沃尔韦伯留的一张便条,通知我必须把维特马克撤回东德。我愤怒至极。为了出一次记者招待会的风头,竟不惜牺牲一个向我们递送波恩加入北约组织详细条件的人。况且我知道维特马克一定极不情愿放弃他在西德前途似锦的仕途,跑到东德默默无闻地度过余生。但我无能为力。不管一个情报机构多么敏锐,它始终是政府手里的一个玩意儿。
我觉得有必要亲自告诉维特马克这个消息。我事先想好的几条政治理由一点也没有打动他。他不满足于仅仅当一部永不停转的宣传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没办法,我只好谎称西德反谍报机构正在跟踪他。惟一避免坐牢的出路就是立即逃到东德。他表示,只有妻子同意才能做此决定。我们推测,虽然他妻子知道他为东德搞情报,但不会对移居东德兴高采烈。我们于是劝维特马克返回汉堡前先给她写封信。我们的信使赶在他之前火速回到汉堡,先把消息告诉了她,使她精神上对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有所准备。面对要么丈夫受辱坐牢,要么在东德一栋临湖的漂亮房子安家,开始新的生活,她选择了后者。
1954年8月26日,维特马克在东柏林的记者面前露面。他透露说,阿登纳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有重大隐瞒。按照以往在这种场合的做法,我们还让他透露一些通过其他来源得到的情报,以增强宣传效果。这一口是苏联军事情报局提供的情报,即波恩正计划建立一支拥有24个师的陆军。这完全不符合波恩政府在公开场合表示的立场。
维特马克被安排到外贸委员会当副主席。我始终为把他召回东德的决定感到遗憾。我常常怀疑,我们是不是为了一条大标题而葬送了一位未来的国防部长。格雷克成了全国民主党内的一名干部。该党代表东德的退伍军人、手工业者和小企业家。可怜的格雷克只好在这个闲差上度过晚年。 当年轰动一时的叛逃到东德的事件完全不是我们策划的。叛逃者甚至根本就不是我们的什么情报来源。他的职业反倒是侦破我们的间谍。此公乃是西德反谍报机构(联邦宪法保卫局)的头子,名叫奥托·约翰。今天很难感受到这一事件在当时掀起的波澜。那时,所有德国人的履历和忠诚仍受到他们昔日敌人的怀疑。左派人士在社会上仍享有威望。
约翰本人反对纳粹。在参加了一次纪念1944年7月20日反对希特勒的未遂政变十周年纪念活动后,他从西柏林消失了。失踪前,有人最后看到他与一位老相识,妇科科学家沃尔格穆特博士在一起。1954年7月ZI日,他在柏林郊区的苏联军事基地再次露面。有证据表明,他俩同乘沃尔格穆特的车到了东柏林。
西德顿时陷入一片恐慌之中,指责共产党情报组织蓄意挑衅,绑架了约翰。说来也巧,正当波恩政府发言人宣称约翰不是自愿离开联邦德国的时候,这位情报头子却在东德广播电台上斩钉截铁地说,他来东德完全是自愿的,因为阿登纳已沦为美国人的工具。美国人“出于与东德士兵打仗的需要,拥抱那些丝毫没有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中吸取教训的人。这些人正在等待时机,为1945年的失败复仇”。他还披露说,西德情报网使用的人主要是纳粹分子。这番话出自他的口极有分量。
然而,和冷战白热化时期发生的许多事件一样,这件事也不像看上去的那么简单。下面我把自己所知道的这一怪诞事件的始末首次公之于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