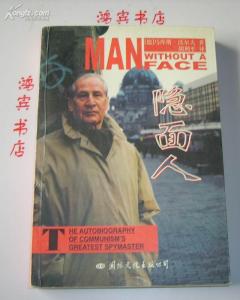隐面人─原东德外国情报局长回忆录-第1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夹子里收藏的昂纳克一生中不甚光彩的材料当中又多了一份。几十年后的1989年,当检察官搜查米尔克的办公室时,发现了这份材料。
清洗一旦开始就难以止住。4年后,乌布利希施展手腕,又一次把沃尔韦伯免职,安排米尔克接任国家安全部部长。他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坐到1989年才下台。米尔克的辞职犹如一场闹剧。他在东德议会上装模作样地和大家告别说:“我爱你们所有的人。”
第五章 边干边学
50年代初的德国像一张巨大无比的蛛网。各种公开或秘密的关系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阵营里的人都有难言之隐或是秘而不宣的特殊关系。没有一件事黑白分明。没有任何人可以完全信赖。看到的外表往往是假相。人人生活在神经高度紧张之中,彼此相互猜疑。比利·怀尔德拍摄的反映美占区生活的电影,尤其是《域外恋》这部片子,以及我弟弟拍摄的反映俄占区初期日子的电影,均捕捉到了这种气氛。 两个德国均称,它们的目标是实现国家统一。鉴于战后德国的分裂源于战胜国之间的利害冲突,我个人觉得这一目标在可预见的将来根本无法实现。1953年6月东德境内的骚乱也坚定了华盛顿和伦敦的信心:击退苏联势力扩张的战略一定会奏效。由于受到政治、经济以及军事方面的压力,统一的希望更加渺茫。西方把重新武装西德,将其拉入西方军事同盟置于议程之首。尽管如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领导人仍然死抱住德国统一的口号不放,全然不顾大批的东德公民移居海外。
我国领导人最关切的是设法使东德具有自己鲜明的特征。他们内心深处始终无法摆脱“第二个德国”与生俱来的脆弱感。一种近乎于荒诞的爱国主义崇拜应运而生。我们设计了自己的军礼服。我本人就有5套。对一个从未服过役的人来说,成就可谓不小。在这期间,乌布利希鼓吹的一个颇为奇怪的想法是再次使用军事象征手段。鉴于我们曾批评西德沿袭希特勒军队的好战的民族主义传统,这一做法无异于一百八十度大转弯。1951年在东柏林举行的苏联阵营内的世界青年运动会上,第一次公开演奏了传统的军乐。我和许多共产党人一样,对此深感不安。我们一直认为,这种尚武主义与音乐的结合构成了纳粹主义的温床。当进行曲响起的时候,我转过身,问和我一起站在观礼台上的俄国犹太人作家爱伦堡对此有何感想。他像典型的俄国人那样耸耸肩,回答说:“德国人一向喜欢正步走。”
与此同时,我们新成立不久的情报局正在埋头熟悉情报这一行。一个情报机构刚成立时,难免会受到墨菲法则的影响。在科技领域尤其易于犯错误或是作出错误的判断。
50年代期间,成千上万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公民源源不断地通过当时几乎完全开放的边境,移居西柏林和西德。1953年6月的起义之后,外流的人数大幅度增加。起义后的3年里,民主德国1800万人口中有将近50万人逃到西德。
我们的间谍混杂在人群里进入西德并不困难。他们通常年纪很轻,坚信共产主义。日后取得的不少成就都是靠这批人铺的路。他们到了西德后,一般被收容在难民营里并受到盘问。不过只要事先编好一个可信的理由,比如想投奔在西德的亲戚,夹在大批新移民里很容易蒙混过关。我们的人打出各种各样的幌子,如想隐瞒过去曾是纳粹党员或党卫军成员的历史,但被发现了,或是发泄过对政府的不满言论。我们甚至还把这类含有“污点”的材料放进其他部保存的关于此人的个人档案里。即使西德反谍报机构设法搞到了哪个间谍在东德的档案,也难辨真伪。我们局不用西德有亲戚的人,以防西德情报机构仿效我们的办法,也通过亲属关系打入到我们内部。
每一名派到西德的间谍都执行一项预定的任务。间谍的培训采取人盯人的办法。每名间谍的训练由主管这项任务的联络官负责。训练的内容仅限于情报工作的基本知识以及获取我们所需情报的一些技巧。让他们掌握与自己任务无关的知识和技能毫无意义。这样做有时反而使他们的任务不必要地复杂化,从而增大风险。时机成熟时,我们还把间谍从西德召回东德,接受新的训练。
我们的间谍去的是西德,一个和我们有着同样的语言和文化的国家。这显然是一个有利条件。苏联派间谍渗透到美国就难多了。反之亦然。随着两个德国分裂的日益加剧,派人潜入西德越来越难。柏林墙修建后,中间混有我们间谍的络绎不绝的东德移民一下子变成涓涓细流。这意味着,间谍事先为自己编造好的履历更要滴水不漏。即便如此,西德还是处于劣势。因为从西德移居东德的人寥若晨星。这样的人一旦到了东德,马上受到严密的监视。不过话说回来,西德也不太需要派人去东德。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在大批对现实不满的东德公民中间收买人做间谍。
在西德站稳脚跟需要一系列的官僚机构的手续。为了应付这些手续,我们的大部分间谍通常先找一份简单的体力活干上一段时间。具有某种手艺或在某个行业有工作经验的人选因此更受欢迎。但不是所有的间谍都经过这一阶段。前面已提到过,当时东德移居海外的几乎所有的科学家和理工科的学生都在我们感兴趣的公司或研究机构里找到了工作。此外,我们还通过与西德科学家非正式的接触了解到一些情况。他们中不少人对原子弹和生物化学武器构成的威胁忧心忡仲。广岛和长崎遭到原子弹的袭击使他们身心受到极大的震动。这批人成了我们套取情报的方便来源。
有些间谍设法打入了严格保密的单位。有的当上了大公司的高级主管。然而,刺探到作出重大决策的波恩军事与政治核心的内部机密则难上加难。
1953年的动荡过去之后,次年在波恩召开的西方盟国外长会议成为我们最关注的对象。这是西方第一次在我国门口召开这样的会议。上面会要我搜集什么样的情报,我心里没底。苏联人像往常一样要我们制定出一项具体的行动方案。抱着碰碰运气的心理,我绞尽脑汁起草了一份行动计划,希望我的部下能够搞到大量的高质量的情报。
莫斯科派来的特别顾问仔细研究了摊在我办公桌上的草图,然后像一名找到发动机故障原因的修理工一样对我说:“会议期间还需要有一个‘玛莉娜’。”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玛莉娜一词在俄语里是山莓的意思。不消说,我们的这位克格勃朋友这里不会指水果甜食。后来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词在俄语土话里还有妓院的意思。他是指我们的人应设法把偶尔走出会场的官员引到妓院里消遣消遣。
当年我根本不懂得如何利用色情搞情报。此事过去多年后我才摸索出了一套办法。可我不想在苏联同事面前显得自己幼稚无知,于是指示部下火速将位于东柏林南面的一栋我们有时用的小房子改造成一个妓院兼陷阱。客厅里安装了窃听器。卧室的灯具里面藏了一台红外线闪光照相机。当时这类器材还十分落后。摄影师不得不龟缩在卧室狭小的衣橱里,直到屋里的人离开才能出来。
下一个难题是物色合适的妓女。我们找到一位曾任柏林警察缉捕队队长的高级官员(1945年到1949年期间,东德与西德携手打击卖淫和色情行业。)。他一副不修边幅的样子。尽管卖淫这一最古老的行业在我们这个清教徒的新社会里转入了地下,可他对妓女经常出没的地方以及如何找到她们了如指掌。不幸的是,他把我们带到了穆拉克贷。这一带的妓女一向是柏林皮肉市场中最差的。我那时的上司干了一辈子情报工作,对这种事早已见多不怪。他打电话告诉我:“那儿的女人,一马克让你玩你都不想沾她们的边儿。”
没办法,我们只好把正统的理论置诸脑后,本能地求助于自由经济的刺激手段。在卡尔·马克思大街上的一个牛奶饮食店里,我们遇到几位更有姿色的姑娘。尽管她们白天都有一份正当的职业,但表示为了社会主义祖国,愿意晚上再干一份不那么正当的活儿。根据制定的计划,我们派一些人分散到西柏林新闻中心以及外长会议地点附近的餐馆和酒吧里,伺机邀请与会的官员或顾问共饮。如果谈得投机,便把他们领回“玛莉娜”,参加有姑娘陪伴的“小型晚会”。
迄今为止,一切顺利。然而午夜时分,我的电话突然响了。出现了一个“未曾料到的情况”。有人要求对这些女孩进行卫生检查。结果发现其中一位并不像自己所说的那样检点。她患有淋病。我下令将她从这次行动中除名。
西方外长会议开幕了。我们布置好了的人等得心急火燎,可没有一位客人上钩。那一年西方部长们的幕僚们品行好得不一般,因为只有一位西德记者上钩,而且还是会议结束后的那天晚上。我们的人殷勤地陪着这位客人又吃又喝。各位姑娘也各就各位。谁知杯盏交错中我们负责当晚行动的头头不小心误喝了为客人准备的搀了春药的酒。当晚安排的最后一项节目是看黄色电影。这类电影在东德当然受到禁止。不过每当我们需要时,原缉捕队队长总能给我们变出几盘来。喝了春药的这位头头看得目不转睛。而他的猎物却对电影和姑娘毫无兴趣,躲到厨房里与女佣人聊起天来。
第二天早上,那位记者是惟一头脑清醒的人。他已洞察主人的良苦用心,表示愿意为我们做事。这次行动总算有所收获,不过实在得不偿失。我们给颇为失望的女招待付了钱,打发她们回家,并严厉警告她们不得对任何人说起这次砸锅的行动。
此事后来还有一个奇怪的结局。我们派人去见这位记者时,他未露面。出来见我们的是一位叫冯·努许斯的同事。他自我介绍说,他在发行量很大的西德《明镜})周刊工作。这种安排是他俩事先商量好的,还是西德反谍报机构策划的,我始终不得而知。努许斯倒是极为热心,说他认识部长周围的人。我对他的话半信半疑。不过以后许多年里他向我们提供的情报同我们通过其他来源得到的情报相符。努许斯后来当上了《快捷》画刊的总编。这份发行量很大的右翼杂志是东德的死敌。任总编期间,他继续为我们做事。
我们开始利用莱比锡贸易交易会同商界人士发展关系,并通过他们结识保守的政治家和社会知名人士。后者认为,与东德保持合作关系可以确保两个德国之间不致爆发全面冲突。东西德商人在莱比锡交易会上达成的交易受到西方战略物资禁运规定的严格限制。甚至像钢管这样的基本商品也在禁运之列。为了绕过这些限制,商人们很自然地彼此建立了秘密的联系方法,偷偷做非法买卖。东德党中央下属一个部,专门负责从事这类秘密商业交易。以后我们情报局接管了该部的大部分职能。我常常借用滥了的高级贸易代表或部长理事会的代表的身份去莱比锡。
我和施泰因吕克就是这么认识的。他是西德的一位钢材贸易批发商,同一些工业巨子私交很好,如奥托·冯·阿梅龙根。阿梅龙根家族拥有的钢材公司20年代初期率先与苏联做生意,并参与修建了满洲里的铁路。一次我与施泰因吕克一起吃晚饭,席间告诉他我是东德内政部的一名将军。我俩一见如故。第二天上午,在西德钢铁联合会的一次内部会议上,他把我作为他的同事介绍给了联合会的董事莫姆森。有施泰因吕克陪伴在我左右,这个诡秘的上层社会小集团里似乎没有一位绅士注意到我的在场,更不要说介意了。施泰因吕克的妻子韦尔哈恩出身于资本主义德国最显赫的家族之一。她哥哥是阿登纳的女婿。我听说后兴奋异常。她的嫂子是西德天主教会头号人物弗林斯大主教的侄女。
我与施泰因吕克的关系经历许多春秋。为了不使联系中断,我隔一段时间就请施泰因吕克吃晚饭,还为自己编造了一套关于我家庭的谎话。位于劳赫凡韦尔德的一栋小楼充当我的家。东德电视台一位漂亮的播音员假扮我的妻子。每次请施泰因吕克来家做客之前,都把她孩子的照片挂在墙上。随着军火交易越做越大,我与施泰因吕克的交谈也越来越有价值。70年代中期时,他已是洛克希德公司的顾问,与西德空军司令来往频繁,对巴伐利亚州的政治领袖、西德国防部长约瑟夫·施特劳斯的活动也有所了解。我从来没有试图发展他做间谍,也没有请他为我们搞情报,虽然他应该可以猜到我是干什么的,如果不是我的真实身份的话。我俩之间最后断绝关系完全是我不留意造成的。起因是施泰因吕克的朋友鲍尔。
鲍尔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商人。他用西德的动物脂肪换取东德劳西茨地区产的毛皮。干这一行当似乎很难发大财,而鲍尔显然很富有。我们的怀疑不无道理。1945年前的某个时候,他曾在弗利克工业集团担任过高级职务。弗利克集团战前拥有利润颇丰的劳西茨褐煤产区。我们找到了一张他在一次教会活动中与阿登纳站在一起的照片。这张照片同他平时寒酸的小商人形象判若两人。我们怀疑,他的背后是希望德国有一天统一的西德大工业家。他的真正使命是替他们先在东德站住脚。根据东德的刑法,他的行为既属于特务活动,又是颠覆行为。我于是有了退鲍尔就范的砝码。至少我是这么以为的。
我知道他同一个名叫汉斯·吉努斯的人是密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吉努斯曾在德国中产阶级抵抗运动与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战略情报局之间穿针引线。掌握了这一情况后,我决定与鲍尔全面摊牌。我约他在东柏林一家专门招待政府贵宾的约翰尼斯霍夫大饭店见面。鲍尔长得又矮又胖,穿一件旧西装,简直难以想象此人是个圆滑的间谍。施泰因吕克显然很欣赏自己新扮演的中间人角色。见面前他告诉鲍尔,我是内政部主管经济事务的一位高级官员。我与鲍尔的谈话持续了几个小时。其间我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