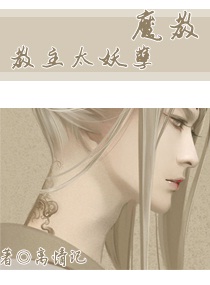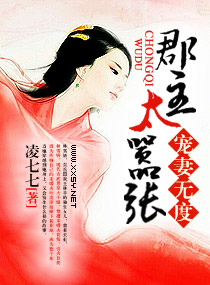������-��45����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ȫ����װ����֮���������ǹ�������������������������������������Ƶģ�����Ů�˰���ֻʣһ�����£��ŷ����⿴�������������ӣ�����Щ�ϣ��������ָ�Ҳ����������Щ������֪�Ǹ�ƽ�����ܸ��ڹ������ߣ�������������С�ĸ�ƨ��С��������ͻȻ���˽��������ֽŷɿ죬һ��ذ��ֱ���������ϡ�
���������ǵ��ڣ�����������ע������������������Ů�˵������ϣ����ݵ������˽�������������Ҳ��֪Ϊ��ʧְ�����������˽��������»���������������һȭ���Dz��в�Ů��С�Ӵ��ڵأ��ۿ���ͷ��Ѫ����������ޣ����˹�ȥ������ʵʵ���˼��£��ۿ�������ǻ��Ҫ��������������棬���ǹ���������ȴ���Ѳ��������˹��������������������˴�������
���������������貫���ĵ�һ��ʿ�������˼���������Ȼ����Ҳ�������Ķ��֣�ֻ�����䱻���˰�ذ�ף���Щ���㣬��Ů�����Dz�Ҫ���������ô���������ս�پ����ѡ�
�����������ԣ�������������������ٵ�����������������ʲô����ʱ�������ӵ�С��ɽ�����ڣ������緢�ˡ�
�������������ó�ˮ��ķ�ŭ������˷�ӿ����������������Χ����թ�ܵ��س��ˣ�������������ҪȢ���ǵĹ�������������ʵ���Ȣ�����������Ȣ������ȴ������˵�������ĵ�����ɽ������ͥ��������ʹ��ƣ�ͻϮ�������ʣ��س��˲�����ϲ��������ô������ʹ����̸һ̸�������ڿ�����ˣ��������֮���ʵ��������ģ�
�����������Һܿ죬���ҵ����������ŭ�ĸ�Դ�����ǵ�����Ů�ˡ�����ս������������ô������������������ȫ��ŭ�𣡺���ѫ�������ߵ�ǽ�ߣ����롱��һ��������Լ��Ĵ��ٲ���ΡΡ�������ۿ���Ҫ�͵�նɱ�����س�������
���������Һô�ʱ�����������ˣ�����侲��Ů�ˣ�����ж�������еĴ����ϵ������������ϵ�ذ�ף����ٵذ����������˿ڣ���һ�仰��ʱƽϢ�����ķ�ŭ�����������������ʡ���������˵��
�����������ǰ������ã��ؼ�ʱ������ؼ����á����ǣ������Ӻ����ij�檣������ǰ��������С�����ڼ������ŵ����������һ�����µ��س����������ʣ���ͻ��ȥ���������һҹ��ɱ��һ·���ӣ�����ԭ�ȥ���������ˣ�����ֻҪ�˻����ţ�ֻҪ���ڲ�ԭ�������Ϊ�ҡ�
����������������������һdzˮ���壬�Ӷ�����һ����֮����һ������̨����һľ���Զ����ɲ��Ҿơ�ľ���ڰ���ˣ��������ڵ�𣬲�ԭ�����û��˼�������飬������ʩ�Ի���֮ʱ���Կ��ô˵ء�
������������ѫ���Ŷ��ļ���̨����������ڤڤ�з·���������ָ����������Ķ���֮�ʣ������������������������ô����������������Ѹ��ۏˮ���ӣ�Ȼ�����������ۼ������ź��沼����ˮ��������֧��������һҹ���س������Ӧ�úܿ�ͻ��������
�����������ǣ�����ѫ���������ˡ���ԭ����ô��������ԭ�ǵĻ������ӵ�����ȥ����������˵����ԭ��ô����������������������ﶼ�����ӡ����ǣ������˽��Ѷ���������س��������������ɰ������°����˼�̨��ľ�ϣ����¶����ɲݣ����Ҿơ���������һ֧��������밢�����������ټ��Դ���
���������ٻ�ͷ��������Ȼ���ؾ������������ԭ���˹���dzˮ���壬Ҳ��ʮ���ɿ����Է��ܿ�Ϳ�������ߵ����Σ��������ǵĹ������ڲ�ԭ�峿������У�����ɢ�ң��²����壬��ɫ���࣬�����ڸ߸ߵ�ľ�ϣ�ֻҪ�������ۼ�����ָһ�ɣ��������Ĺ����ͻ��ڻ��У��������ϵء�ʹ����ֵء���ȼ�ա�
���������DZ���һҹ������ѫ�˿������ҵ���һ˿�ƿؾ���ijɾУ����ܸ��ܵ������������Ľ������������Ǹ���ͷ�Ľ��죬������ˮ����һ��أ�������ߵĹ���������ټ���������ֹס��
������������ѫ����ϸȥ����������һ���������ף�ͷ�����������������֧��������������ķ�ɫ�������ؾ��߳��ij���ͷ�����ף��ֲ��ã�����������һҹ���س��������ʱ������ô���ˣ���ô˦Ҳ˦�������������������Ǻ�ѹѹ�������У�����Ҫ�쳣ͻ��Щ����֪����Ϊ������ʿ���ϵĽ�˿���ߣ��ڳ�����������ԣ���Щ���ۣ������Ǵ�δ����ȴ��������ʶ����ò����Щ���ġ�
�������������������Ҽ������𣿡�����ѫתͷȥ���Ǹ��˿��������ε�Ů�ˡ��������ѣ���Ȼ���������ߣ����벻�������Ѳ������������ˡ�
����������������������ɱ��ʮ���꣬ȴһֱѰ���ŵ��ƶ����ӣ��������������������������žټ������ƣ�һ����ƣ�ȴ����û�лش�����ӵ����⡣
����������������ȴ�Ǻ���ѫ����Ĵ𰸡��۰������ԭ�ĸ���Ѱ��ʮ���꣬��δѰ�ŵ��ˣ����Ǹ���ס�ˣ����Dz��ǿ��Խ�����������Ȼ������ӵ�֮�䣬����֮������ͷ���ߣ�����������ָ�������������˰�����һ�䣺
���������������Ǹ��������㣬��Ըȥ���أ����س�������ȹ����ţ�����ĺ�������������
�����������ߣ������������صغ���һ����Ť��ͷȥ���ߺ��Ѳ�������������
���������������������벻�롭��������ѫ�����ʰ����������벻�뱨������δ���ڣ��ѱ��Լ��ľ������⼤���˷��������ɴ�ֹ�������ˮ�IJ��ʣ�ֱ�����������軰ȥ�ʺ������ˣ�
��������������������������±�����ֻ��ۏˮ�������Ҿͷ��˹���������Ȼ���Ҿ�һ�ѻ�������ԭ�����������ƶ��������Ǹ����������µ����ӣ�����Ϊ��ľ�ϵ��Ǹ�Ů�ˣ����κ��¡�
��������������Ҳ�൱������ĺ������������ñ��������˱�ͷ��
������������ѫ�ͼ��ź����������������������ؽ���ж�±��Ϲ�������Ҫ�ٲ�������ߡ�����������ͻȻ��һ��˻�Ƶĺ��������������壬�ܾ����������е����飺
������������ī������������
��������ԭ�����ǰ���ľ�Ĺ�����֪��ʱ�����ˣ����ź������˵ľٶ�������ϧ�ɡ�����ˣ���Ȼ���������ѫ����Ī����ŭ��������Ȣ�˸���������������������������������Ů�ˣ���Զ��������������ô���ðɣ���Ȼ����ԭ��һ��ʿ�ò����ģ��Ǿ�ֻ�в�ԭ�������ӵ�С�
�������������������������������⣬�����ϼ�̨ȥ����һ̳δ������Ҿƣ�������ͷ����ľ����Ů�����ϡ����Ƚ��µ���Ѭ��ֱ���һ�����������ĸ��죿
���������������Ҿ�һ����û����Ϣ����ؼž���������������ۏˮ�Ļ��������Ǻ����������ƿ�ʩ�������ؿ�ʼ�����һ�����߹�����
������������ѫ�������ţ�ֻҪ�����й����������ϥ�����Ͽ�ʼ¶��ˮ�棬����������뷢������������ģ��������������游��������ѹ��ʮ������ĸ���Ȼ��һ�ѻ���˹�����������ԭ����ˡ��ȶ������ɱ���������ǵĹ����Ѿ������Ի��ɻ��ˡ�
������������������һ��һ�����ߣ�����ѫפ���ڹ�����������࣬���������֣��ȴ��ż���������ʱ�����������һƲ�����Ű�����Ҳ������ǰ��ͣ���˹����ֵ��Ҳ࣬������Ȼ������ֻ�������Ťͷ��ȥ�������룬��Ů��Ҳ�dz�����أ��ѵ���Ҫ�����˽����Ǹ����˵�����ô��
���������ɵ���ʯ�䣬���IJ����������еļ���һ��գ�ۣ�����Ȼ���֣��Ǽ�����������Լ���
����������һ˲��һ������������ѫ�������أ����ޱߵķ�ŭ����ҵ�ʹ���У�������������������
����ʮ���µ��������ң�����
��һ�̣���������ͻȻ���꣬һ����ɱ�˺���ѫ��ȴѸ�ٵ�ȼ�ڶ�֧��������ż�̨��ʱ��ҹ�������֣��Լ���������������û����ң�ֻ�и��ҡ�
���������������ڵ����ң����ֺ��绽�꣬������������ζ��û�ٳ���������Ƥ��֮�࣬����֮ʹ��Ҳû�ٳ�����
����������������һ���Լ�ϲ���Ķ��ɣ�ȴ�ֲ��ò���ն����������˵�ȥ������һ���Լ����µģ����������Ǽ���������������Ӣ�ۣ���ͷ��ȴ�����������ѵ������ˣ��Ѿ���˼��һ���ؽ��֡����ţ�����������������������Ϊ�Ƕ��Ƕ��£���ҹ�ŷ��֣���������������������DZ��˵�ʩ�ᣬ���磬�̨���ƴ�����������������һ����
�������������ȵ�����������ǣ���Ϯǧ�ǰ�������ؼң�ȴ������ѫһ���������ˣ�������ľ�ϣ��������Ķ����ǣ���в����������ˡ�
�����������ԣ�����ľͷ�������������һ����ۏ��ˮ������ʱ���������Q�ö���Ҫը���ˣ����յļ���һҹ���䣬���еļ�������Ŀʣ����ϵ�ʹ���·�ͳͳ��ʧ��ֻ�ж�����һ���������������е�ۏˮ������ľͷɵ�ӣ�����ѫ���ˣ�ֻ����ȭͷ��ɱ¾����ô������������
����������������ѫ��һ����������Ȼ����ʱ������������һ��������������Ҳ�������˿������ǽа�������Ů�ӣ��ڿ��������ý����ĸ�������ʬ��Σ����վ������Ƕ����������δ���������������İ����ɣ����ж�������ж�����������������
����������������һ�̣��ǰ���֯��Ů�ӣ�Ϊ���İ��������������һ�����ġ����µ���һ֧���������ľ�����������һ�������Ц�⣬����Ц���ϣ�����ҹ����ǰ����ץ��������ָ�ۡ���һ��ҹ�����˿̵Ķ�ǣ����ź��һĨ��ϼһ������Ц��м��ʣ���Թ�ޣ��г�Ц������Щ�������˵���ζ�����Խ���֮�˵�ͬ�飿����������
��������ҹ������������ٴα����������Ů�ˣ����ɱ����ȴ����ɱ����
��������������������ס�֣�������������īվ�ں������룬��ŭ�ش����ǰ�������ȴ����δ�ţ���ָһ�ɣ����������ֱֱ����ľ������
��������ҹ���������۾���������һ�̵���١�����ͷ���ţ�ɢ�ҵij��������ϵĵ��£���¶�ļ������ѱ��Ҿƽ������¶����ĸɲ���࣬Ҳ�Ǿ���Ũ�ҡ�����һ��������մ������������һ���ط������ǽ�������һ���ɲݣ�����ֻȥ����ԭ����ȥ�ˣ�û����ѫ�˿̣����ڲ�Զ�����������Ѳ�����ĸ������Ӳ���һ�Թ���ԧ�죿
��������һʱ�䣬��˼���룬������꣬ȴ���첻���Ǽ�մ����Ҳ�������������ڡ�������������ͷһ����̧���д������̲�סʧ��Ц��������
�������������峿¶�أ��������������֧�������������µĸɲݶ��ð��Щ�����ӣ�ȴδ��Ѹ�ٵ��ţ����˿�֮�ơ����ң����ɲ������ǣ������ˡ���ԭ�ϵĹ����꣬��֪��ʱƮ��һ�����ƣ����������ͽ���������
��������ҹ����̧������������ˮʪ��ɿʵ�˫��������ɤ��Ц���ٿ��ڸ߸ߵ�ľ�ϣ�������ǰ��һƬ��ս����ͬ��һ�����⽣Ӱ������Ϸ��
������������ѫ������������Ҳ��������Ӱ�������Ⱥ�����ף��ڻ����п�ʼ��ɢ��dzˮ���������ǣ�����ˮ����ɱ�˹���������Щ�ȶ��ܵ�����������ǣ�����ؾ���ս�������ߣ����µ����ꡣ
���������ܿ죬��ǰ�Ļ�ս����Ļ��ģ��������������˭��˭��������˭Ҫɱ˭����Ҳ����ȥ���ˣ����������ֻʣ��һ���ˡ����İ�ī���Ӻ�����ɿ���ܹ���������Ⱥ�ж���һ�Ѵ����������ֱ�߾��룬һ·������һ������ɱ������ɱ�����ɫ�����ڣ��������������ߡ�
�������������ں���ѫ�������������գ���ֵ��˿̣�����Ϊ���ϵ�˵���Լ�����һ���������������˿̣����ĵȴ���������������Щ��������ޣ��뽫���յ�ί��������һ����ί��ȫ�����ߡ�ȴ�����г�ӯ��������ǰ���������꣬���������ƿ�������
������������ī��������������������ľ�Ϸ��������ƺ����������������������������Ҿ������У��Ƚ���һ���������Ź�������������
��������һͷ����Ǹ�������ʵ�Ļ����������ھ��ã���������˲�䰲ȫ�ˡ�
��������������ů���ž����䣬ҹ�����㳯�����������˵ý�Щ��ȴ����������������������ޣ������ӻ�δӿ���ۿ��������й��̵�����һ�εεص������ϣ������ڱ������ˮ�У����������ĸд���
�����������Ǹ��������Ϳ������������˱����������������ǿ���������������ί����ʹ����������ɢ����ľͷ���촽����ȴ����˵����������ȫ����Ӳ���뽫�����ú���Ƕ��������ȥ��ȴ������һ��������䱦������ӵ���������ܸ��������ģ����Ľ�������������̫����������ʹ��ʹ���ܵ����˺�������Ǹ�Σ�����δ�ܻ�������
��������ҹ����������Ҫ�IJ��࣬�ٿ������������ں���ֻҪ��������������˴�����ˣ������ɵ�̧��ȥ�������ᣬ��Ҳ��ɵ��������ˮ��ˮģ����������β��øɾ���ֻ�����ſ�ǻ���庢���Ƶĺ�����
������������ī����ޣ��Һúõġ���
�����������š����������ñ���Ӧ��������ֹ��ס���п���������˫�֣�������£�dz�������ڣ���������������ָ��һ����ɣ����Ǵ��϶�ǵ��˺ۣ��ʵ�С�����������Ͱͣ�
����������ʹ����ʹ�𣿡�
����������ҹ�����ѫ�˴���һ����������ѣ���֮һҹ������������ʹ����ľ���˿̴��꽽�����ϣ��ַ·�������Щ֪����ȫ������ǧ��師���ң�����廨���ƴ�һ�㡣�������ã����ĵĸ�֮���¡�
��������������ˣ�������ǰ�����ܲ��˵�չ¶������������������������ս�������ж�����ϵ����ף����������ս����ֻ������������������㺡���������ζ����һ�ֿ�ɬ�����ۡ�
������������Ŭ��������ɤ�ӣ�����˵Щ���ɵģ���ͬ��ǰ���µ�������
������������ī����Ҫ����ʹ���ˡ����ң��������ѧ����������ױ������÷��ӡ������˺ۣ����ÿ�����һĨϼ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