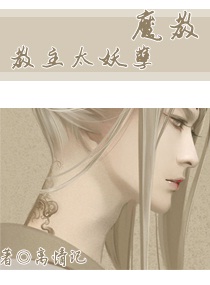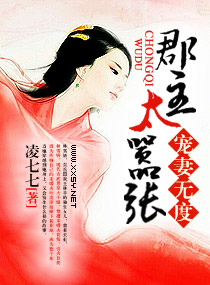长公主-第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实则已经将脚高高抬起,又重重踩了下来。
果然,长公主指了指不远处的皇宫正大门,声音里掩着一丝轻快笑意:
“呐,最能看尽曦京繁华,世间百态的,就是这泰安宫门守门卒,不若就让他守这城门,如何?”
第七章郊天大祭典()
冬月十二,冬至。
冬节大如年,天地阴阳二气转化之极点,一阳之始,君道长,故贺。
尊曦朝祖制,冬至举行圜丘大祭典与太极殿大朝会。
从午夜开始于圜丘设祭坛,坛旁边设天灯竿,禁寺庙鸣钟擂鼓。卯时,皇帝至圜丘,在太常寺礼仪官的引导下,行祭天大典。在繁琐仪式后,还得赶在辰时之前回宫,于太极殿,接受文武百官与外藩使者朝贺。
所以,这一个时辰之内,须得步步紧凑,一步都耽误不得。这卯时之前的准备,也需得有条不紊,一点也错不得。
沈子卿舍了后半夜的睡眠,寅时不到,便一身整齐朝服礼冠,赶至圜丘,检查诸事宜是否妥当。虽有太常寺的人从午夜开始,便着手祭典,可太常寺卿乃皇帝亲政后任命,于这国之祭典尚无经验,他身为当朝宰执,有督促指点之责。
待见着祭坛肃然,天灯灼灼,祭品礼器、钟磬鼓乐等万事齐备,让太常寺卿拿了陛下的祭辞来看,也未觉不妥,才不禁松了口气,于祭坛旁边捡了个座位坐下来,闭目小憩。
本想灵台清明地养些神,可在这巍然祭坛边上,似乎特别接灵气,往昔的家事国事,一串串地涌上来。
南曦四大世家,圆形方孔柳,大马金刀明,朝堂不倒的三叶沈,猛见那凤凰儿回首。柳家掌着曦朝的财政命脉,又做着皇商的暴利买卖,财能通神,盘根错节,如那百足之虫,就算死了也僵不了。明家与凤家世代将领,京畿禁卫,五路节度,保家卫国,开疆扩土,兵权在握,那也是硬气得很。只有他沈家,无财力无兵权,仅凭那所谓的治国之才,要在朝堂上作“不倒翁”,谈何容易。
嘉元二十三年,前太子私通萱妃,淫乱宫帏,东窗事发,父亲沈邦彦身为太子太傅,被罢免相位,贬官南疆岭城,朝中相国门生清洗一空,一时间,沈氏一族欺男霸女、贪赃枉法的案子不管陈年烂谷子的,还是西瓜芝麻大的,涌出大大大小小几十件,百年世家遭受重创,一蹶不振。
彼时,他只得重新押注,以翰林闲职的身份,主动请缨,秘密潜往北辰,脱了一层皮,成功迎了那对姐弟归国。未曾想,这赌注,还真是押对了,那看似皮懒的女子,实则心机深沉,胆识谋略不输于男儿,又比男儿还要灵气些。眼见她挑了两位兄长互相争斗,斗得两败俱伤,身首异处,她再牵着今上,一路行至那皇朝最高处,而他沈子卿,自然也以辅国大功臣的身份,站在了这熙乾朝堂的最首位,沈家也得以复兴。
可这富贵荣华,还真是一条不能回头的不归路,往前,能上九重天,停下来,却会化为乌有。
那娇娇小人儿的心意,他何尝不明白?只是,他的苦衷,她又何尝懂得?快一月不见了吧,那挑食之人,又不喜规律作息,不知会不会又清减了,那清冷的脸庞浮现眼前,心里一阵紧疼。
沈子卿一阵恍惚神游,睁眼定神,不觉已近卯时,皇帝来了,长公主……也来了。
微弱的晨光下,仍看得出……明艳,她少有脂粉浓妆,可每每这般扮相,却很是摄人心魄。
那妮子一来,便在人群中左顾右盼,待一眼寻到他,便略带了笑意,盯着他看,后来索性往他身侧一站,不挪动了。也不顾这是礼乐煌煌,庄严肃穆的祭祀大典,不过,这妮子耍起横来,从来不分场合的。
他微微欠身示意,然后便置若罔闻,掐着时辰,示意太常寺卿,指引皇帝,开始祭祀仪式。
“於赫圣祖,龙飞晋阳。底定万国,奄有四方。功格上下,道冠农黄。郊天配享,德合无疆……”
从皇帝颂祭辞开始,迎帝神、奠玉帛、进俎、行初献礼、行亚献礼、行终献礼……繁复的仪式,一步步,一套套,从天光微亮,一直到晨曦破晓,再到朝霞漫天。
皇帝是他一手教出来的,今日一身祭服朝冠下,越显沉稳天子气度。身边与他并肩而立之人,亦是一身香色公主朝服,虽也宝相庄严,可他偶尔余光瞥过去,总觉得今日那脸上气色,红晕得有些过于妩媚了。
待行跪地叩首大礼之时,沈子卿才发现,那红晕,哪里是什么妩媚气色——
众人礼毕起身,他亦正要起来,却发现身边那人跪在地上,垂首闭眼,不见有起身之意。
他以为她是跪在地上久了,睡着了。这妮子贪这晨间懒睡,是出了名的。
他附耳过去,轻轻唤了几声,无应答,这才伸手过去扶,只觉那人身子绵软,顺势就瘫倒过来。
他以为是晕了,腾手轻抚她额间,发现滚热烫手,竟是发着高烧。赶紧想要起身,招呼她的侍女上前来伺候,送回宫传太医诊治。
刚一起身,却发现腰间一紧,有股力道将他扯住,他低头一看,一只白玉小手紧紧抓着他朝服上的雕纹镂金封带,那人在他胸前吐气如兰,悄声说来:
“别走,就这样,让我靠会儿。”
第八章泰安守门卒()
马车里,夜云熙头痛欲裂,浑身无力,那高热引发的全身酸疼,如有百虫啃噬。可这四肢百骸的难耐,却比不上此刻心中的窝火。
昨夜沐浴斋戒,她泡在温水里,突发奇想,曦京坊间称沈子卿为谪仙人,听说没有女人能近他身,当然,她也不例外。可若是自己病到在他面前,他会是何反应?遂不顾青鸾的劝阻,硬生生在冷水里多泡了半个时辰。
她知道自己有些疯狂了,不过,比起没来由的疯狂,更让人失落的是,方才,自己已经是那般楚楚可怜的模样,那人脸上却看不出任何表情,低声责了一句“胡闹”,又强行扯开她扭在腰间封带上的手,招呼青鸾上前来伺候,便仍了她在原地,起身随着陛下先行回宫,行那劳什子大贺朝去了。
像是生怕在她身边多停留一刻,就要入了言官的眼,惹了坊间的闲话,有损他的名声一样;又像是生怕多耽误一刻,便要误了今日辰时的大贺朝一样。是了,他不是那百官之首吗?那晨光之中,煌煌朝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何等的荣光!
头晕疼,外加心纠结,不由得呻吟出声,算了,还是赶紧回丹桂宫,请老太医开个能昏睡过去的方子,然后,自生自灭吧。
心里盼着回去,马车却突然一个急刹,停了下来。
“此刻太极殿正行大贺朝,所有人须下车马,步行入泰安门。”
这朗朗声音好生可恶,又好生熟悉,夜云熙猛地掀开车帘子一看,那屈膝跪地之人,不是昨日那个姓凤的石头侍卫,还能是谁?昨日才将他从殿中都尉贬至宫门守卫,这是真的尽职尽守,还是故意与她作对?
“这……殿下病着呢……”青鸾立在马车边,拿不定这主意,是要尊这冬至朝会规矩呢,还是要顾虑自家主子的身体?
“挂冬仗之时,泰安门内禁行车马,请长公主殿下下车步行。”那跪地之人又抬出这仪卫兵仗说事,冬至大朝会之际,宫城内外遍布排列井然有序的步骑兵甲,同时悬挂旌旗、击鼓、奏乐,称“挂东仗”。
“可这……”青鸾还在支吾,夜云熙有些恼了,平日里那么伶俐的丫头,今日怎么跟舌头打了结似的,她索性虚抬起手,打断她的侍女:
“本宫若是偏要乘车入宫,又怎样?”
这曦朝祖制,国典礼仪,她向来尊之敬之,此刻宫中,十步一岗密密麻麻的仪卫兵仗,她亦不想太过招摇,不然,御史台的人没准能拿唾沫将她淹了。
可眼皮底下,这守门卒太来气,三番五次,总是在她心里憋屈时,突然冒出来,杵在跟前,强迫她,忤逆她,冒犯她…总之,给她添堵。正如此刻,也不答她的问话,也不抬头起身,兀自跪在马车前面,如一块顽石,挡住了去路。
夜云熙的倔劲儿上来了,提了朝服礼裙,朝青鸾喊道:
“青鸾,扶我下车。”说着,也不等青鸾上前扶稳,便跳下车来,顿时只觉得头重脚轻,脚下踩棉花,赶紧靠在青鸾身上,稳了稳重心。
再咬了咬牙,强行提了真气,一把推开青鸾,上前两步,一脚猛地踹出去,果然,她那几下花拳绣腿,有时还是能派上些用场的,虽然脚尖疼得如针扎,但让她开心的是,这次,那顽石没来得及防备,终于被她踢倒在地。
若是平日里身强力壮之时,准能将他踢飞起来,撞旁边的青石墙洞壁上,那才解气——正当她还有些意犹未尽,觉得还有提升空间之时,突然间呼吸一促,眼前一黑,宫内依稀礼乐鼓声突然飘远,最后好像是青鸾抢过来扶她的呼声,然后,便什么都不知道了。
第九章我抱她回去()
熙乾三年的冬至,凤玄墨终身难忘。
前一日还是陛下跟前的红人,殿中都尉虽算不上什么品级,却是御前当差,长伴君侧,加之陛下信他用他,加以时日,必有出头之日。可转眼间,因长公主轻飘飘一句话,就被贬至泰安宫门——守大门。
先不提这宫门口的风吹日晒,禁军同僚的冷眼语刀子,只说,这日,从寅时宫门开,至辰时太极殿朝会,贵人们进进出出,呼啸而过,眼高于顶,只留衣袖清风或身后尘土,与他这小小守门卒有关。
可这位长公主一来,就让他迅速成为宫城八卦的主角——不出一个时辰,整个宫里便将会传遍——泰安城门口守门的小卒子,阻拦长公主鸾驾,被长公主一脚踢翻在地。
可这还仅仅是开始,未曾想,那被皇宫上下津津有味嚼了许久的八卦重点,还在后头——
那当口,侍女青鸾一边扶着晕过去的长公主,一边圆睁着眼,对他说道:
“殿下发着高热,不省人事,需传太医诊治,你若继续纠缠,耽误了诊治,这罪过,你有几个脑袋,能担当得起?”
原来是发着高烧,竟还有那般力道,看来昨日马车上那两下,还算脚下留情了。不过,这女人也真是倔,非得将自己给折腾倒晕过去……凤玄墨心里思忖,心里一股莫名的痒痒暖意,那张千年冰山脸上,鬼使神差般,竟浮了一丝笑意。
然后就看见,青鸾那本就圆的大眼,睁得圆得不能再圆,像是看见什么不敢相信的画面,有些怒不可揭,接着便是口不择言:
“你还笑,若不是昨日你冒犯殿下,让她受了风寒,今日能生病吗?”
风玄墨心里咯噔一声,这宫门口,可不止他一个守门的,旁边森然守卫,整齐列着呢,这青鸾姑娘说的,太有些……不清不楚了。
可再去看那闭着双眸晕睡之人,脸上底色苍白,却又泛着不正常的红潮,微微蹙颦,睫毛扇动,像是极不舒服。
那蝶儿薄翼般扇动的双睫,像是有种魔力,引着他一个跨步上前去,只手拦腰背,只手揽膝后,将她抱起。
不忍看青鸾那圆眼睛已至极限,他又仍下一句话:
“此刻宫内禁行车马,我送殿下回宫,姑娘可派人先行去太医院请御医。”
说完,将怀中人儿揽紧了,转身入宫门,过广庭,沿着东侧长长宫道,一路往内宫行去。
风玄墨长年习武,臂力与耐力自是不在话下,加之怀中那人看着高高的个子,却出奇地细幺轻巧,一路走来,身侧的青鸾,还需得不时小跑,才跟得上他。
行走颠簸中,怀中那人亦有些觉知,伸了纤手来抓他衣襟,又将脸凑他胸前。他凝神细听,还有些微微呻吟声,想来是难受吧。
彼时,他抱她在怀,行在这高墙宫道间,仪卫兵仗,依稀礼乐,他只默念着抱人的初衷,既要不触犯这国典规矩,又要将这难缠的女人,外加她的侍女给打发了,当然,还带些因自己昨日将她从被窝里拖出来,让她受风寒的歉意。
再多些,也就是觉得这女人安静下来,还有些……乖巧。却不知,这拥卿入怀,是一件多么可遇而不可求的事,这一年的冬节,老天爷不知道有多垂怜他!
第十章腥甜的旧梦()
迷迷糊糊中,夜云熙觉得口干舌燥,嗓子冒烟。眼睛被什么东西蒙住了,不能视物,却仍能感觉到沙漠骄阳的灼热。
遮住了双眼,反倒打开了其他的感官:四周出奇寂静,只有脚下沙沙声,耳边是一个人的有力心跳声,头顶上还有匀称缓和的呼吸声:鼻间萦绕的,除了夹杂着尘土风沙的干燥空气味道,还有一个男子的浓烈气息。而自己,就挂在这人的怀里,在颠簸摇晃中前行。
夜云熙记得真切,从北辰最南边的南关城出来,一头扎进这浩瀚沙漠之时,一半精卫,护着云起,悄悄向西绕道入南曦,而一半精卫,则跟着她与沈子卿,招摇地走“黄金路”,果然如皇甫熠阳所言,遭到了接二连三的阻击。
到得后来,护卫分散了,车驾也扔了,马也中箭倒地了,只剩下沈子卿与她,终于逃脱了穷追不舍的杀手,却误入了香雪海深处——香雪海这名字,貌似销魂美景,实则是吃人不吐白骨的浩瀚沙漠。
沈子卿拉着她,准确地说是拖着她,辨认着太阳的方向,在黄沙里徒步向南,也不知走了多久,她又累又渴,眼睛被日光刺得生疼,有些视线模糊。
再后来,她开始脱水虚脱,不能视物,脚下如灌铅,迈不开步。心中渐渐生出绝望,这辈子,大概再也回不了南曦了吧。
再看沈子卿拖她拖得辛苦,她即担心拖累了身边的人,两人都交代在这里,又生怕他弃她不顾,留她一人清醒地自生自灭。复杂心思中,索性自己先挣开了手,往地上一靠,滚热黄沙熨着疲惫酸痛的肌肤身体,只想将整个人都埋进去,好好睡上一觉,后来,……后来好像就失去知觉了。
而此刻,这人终是没有弃她,抱着她走一段,又背着行一程,也不知哪来的力气,还拿布条蒙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