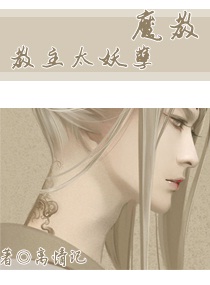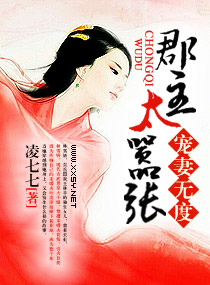长公主-第11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第一百七十九章惑世灾星命()
那锦书,是北辰送来的,皇甫熠阳的绝笔信。
拜他所赐,皇甫头风发作,不能理政,退位半年,隐居深宫,勉强为三岁的新皇撑腰,数日前,固疾无治,驾崩归天。临终前,搁着诺大一个王朝江山要交代,却念念不忘派密使给她一敌国公主送来书信。
这叫她情何以堪?那书中,除了“三郎绝笔,小昭儿亲启”几个字以外,其余,什么也没有,却比任何只言片语,更让她心生哀戚与愧疚。皇甫的意思,她看得懂,不是在怪她,而是在求她。
求她,在余生之年,都能记得起他这个人,记得起他的好;求她,看在他的份上,对他丢下的孤儿寡母烂摊子,能照拂便照拂。
的确,那黄澄澄空茫茫一片锦锻,如同一把锋利的刀子,在她心上刻下了一道深深的痕迹,心头血作证,她会感念他一辈子。
再则,这书信,本是走的隐秘渠道,直接送到将军府,却被夜云起的人给截了下来,翻检过后,再捎带着皇甫驾崩的消息,一道给她送来,送到之时,偏偏是她生辰日这天,午时的节点上。云起的意思,她亦想得明白,亦不是在怪她,而是在……赞她。
赞她,深谋远虑,在北辰为质之时,一个求生保命的无心之举,却在多年以后,替曦朝消除了一个心腹大患,且不费吹灰之力。如今,北辰主少,政乱,恰是乘虚而攻之的大好时机。
赞她,克亲灾星,惑世乱四国的命。十二岁那年,七月十七日午时,在她的生辰宴上,先皇后薨。如今,西凌王,北辰皇帝,皆因她而亡,这于夜氏大曦开疆辟土的宏图大业而言,是何其伟大的功勋?
看着那无字锦书,想着夜云起的用意,正觉得自己快要化作一滩泥,无所自立。也不知是天意,还是赶巧,那雪狐来凑热闹了,平日飞檐走壁到处撒欢的灵兽,此刻却软趴趴地伏在桌上碗碟边,赶也赶也不起来,伸手去扒拉着一看,那四蹄畜生,竟是心生感应,眼中含泪,且已奄奄一息。
夜云熙就再也无法自持,哇地一声又哭了出来,管他山崩地裂,海枯石烂,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几近晕厥。
凤玄墨不知她心中覆侧,只以为她见着故人去世而悲恸,将她按在胸怀里,扶着她肩背,一阵轻拍,想要平息她的激动。
然而,那决堤的泪水,虽由皇甫与雪狐引起,但更多的,却是……对未来的恐惧,如何能平息?
“我就是个灾星命……你不要对我太好……离我远些……”她伏在那人怀里,想将他推远,却伸臂将他攀得紧紧的,终于,哭诉出心中的担忧与恐惧,却又满是依恋与不舍。
她想起阿依莲临走时说的,你莫要忘记了你的克星命,你越是这样缠着他,说不定反倒害了他;
想起七月七日夜的蹊跷,那么多的孔明灯,竟升不起来一个她想乞他平安的心愿;
想起他爱她如命,却总是为她受苦,熬筋磨骨,刀口剑伤,征战拼杀,波折起落,违誓天罚,情蛊禁术,身体之痛,心之煎熬……
她不是个克星是什么?
那人沉吟半响,终于听明白了她的话中之意,突然死命地将她往怀里箍,往骨子里嵌,一边大掌扣住,狠狠搓揉,一边急急地吐出些慌乱之语。
那些话,从他心底深处而来,直直地进到了她的心里,一点一点地撞击她的惧怕——
他骂她傻,说从来都是他让她受苦,怎么会是她克他?她是什么命,他都不怕,他生来就没了母亲,毁了城,灭了族,后来还杀了亲父,这天煞孤星的命格,谁能比得过他?
又说,他一定会陪着她,一直陪她到头发尽白,牙齿掉光的时候,等她不再留恋这人世间之时,送她走了,他再走。
听来无比安慰,却又无比心酸。越是渴望,期盼,越是害怕,倒头来镜花水月一场空。
索性继续窝在他怀里哭泣,任由泪水与酸楚泛滥蔓延。倒得后来,心神散乱,无法敛拢,四肢发软,无法自立,东西也吃不下了,便央他带她回房里休息。
凤玄墨正手足无措,蹙眉瞧着她那糟心模样,怜得发慌,赶紧照做。一路抱了她回房,解衣脱鞋,交颈缠肢,却是规矩地陪她一阵午睡。
心思猛烈激荡之后,便是困顿来袭,加之那人将她缠抱着,且还从头到脚,寻着穴位给她一阵点按轻揉,倒是放松下来,迷迷糊糊地就睡过去。
恍惚中,觉得这好好一个生辰日,怕是自母亲去世以来,最热闹隆重,最有人疼爱的一次,却被一封锦书扰乱了心境,留了遗憾,也不知,何日才能重来。
……
一觉醒来,发觉日头偏西,身边空空,那人不知何时起身走了,独留她一人,在丝薄锦被里躺着。
再凝神一摸,发现自己竟是初生婴孩儿般,不着寸缕地裹在丝被中。身无多余束缚,心中淤积亦发泄一空,怪不得睡得稳沉,连梦影都未寻着半个。
只是,摸到身上好几处黏糊糊的……残留,有些哭笑不得,不知那已经没了底线之人,是如何将她剥成光溜溜的软虾,又是如何趁她熟睡之时乱来了一番,她竟丝毫无记忆,也实在是没脸,也没那想象力,去细想了。
被他这样一番折腾,倒也心神稳定,想起午间在厨下那不能自已的哀伤,竟生出些距离之感。想起那灾星克命之说,虽说心中仍是沉重,却也能鼓起勇气直视面对了。
克就克吧,如他所言,兴许,他就是那受得住之人呢。兜兜转转,坎坷几年,千难万险,出生入死,如今不也修得了同床共枕眠,且又是难得的恩爱两不疑,她应该惜福,知足,而不是终日贪婪惶恐才是。
大不了,生时同衾,死亦同穴。生当复来归,死亦长相思。
遂此后日日,继续过着那蜜浸过的日子,心安理得地受着那人的娇宠。
只是,暗地里,也旁敲侧击,探听这征伐布置。得知那一直驻扎在京畿大营里的五百云都隐者,皆要随他出征,且萨力和早已往返了边关几趟,如今又回了京畿,等着与他一道开拔,便觉得心安了些。
又去求贺兰铮,求他跟着凤玄墨出征。好言好语,好酒好肉地伺候了,贺兰铮却懒得搭理她,她索性劈头盖脸给那伪疯子一阵臭骂,说他空有一身通天入地,起死回生的法术本事,不用来保护贺兰伊的儿子,不用来向北辰人讨云都之债,却藏在她家里装疯卖傻,吃闲饭养老等死,算什么?
贺兰铮果真被她激得暴起,彻底抹了那疯癫面具,跳将起来,冲她大吼,去就去,我当他亲儿子,比你还心疼他!她看着那最忌别人说他苍老无用之人,燃着雷神怒火,跳进她的圈套,又心安了些。
于那床第之事,也存了些克制。一则,怕寅吃卯粮,把那血气男儿给掏空了。二来,出征在即,倒时候少不了长途跋涉,搏命拼杀,需得提前养精蓄锐,不可乱耗了气血。又让给厨下做些滋补壮身的吃食,一口一口地,守着他海吃山吃。
就这样旷了他数日,那些滋补汤水,又吃得他赤红了双眼。有时唉声叹气,一脸痛苦地看着她,拉着她的衣角,求她垂怜。那可怜兮兮的模样,若是身后有尾巴,怕是早就摇起来了。
她忍着轻笑,硬着心肠,次次都撵了他去书房休养。本来也是,按曦军惯例,大军出征前,将士皆是要禁房事的。只是,究竟有没有禁,禁不禁得住,只有各人自己知道了。
七月二十八日,大军出征前一天,那人终是熬不住了,夜色未尽,便逮了个机会,将她按在窗边软榻上,欺身上来,要霸王硬上弓。
夜云熙瞧得唏嘘,想着这离别在即,怕也绕不过去。索性一个蛮劲翻身,反将他压在榻上,伸手替他解带宽衣,说是不能让大将军劳累了,不如换她服侍他。
那人哪里受过如此恩宠待遇,不禁喜出望外,乖乖地仰躺了,笑意盈盈地,双手扶在她的小腰上,由她纤手翻飞,捉弄摆布。满脸渴饮甘泉的欢喜,仿佛只要她肯施舍,怎么都好。
正衣带渐宽,意乱情迷之时,又是青鸾那妮子,不合时宜地出现在门口,说是陛下身边的高公公来了,请公主去云台,看钦天监大巫之卜言。
夜云熙被扰得心下火气,顿了动作,飞快地想了想,钦天监大巫今日卜卦,定是大军出征之前的问吉。可这出征卜言,自然会在明日誓师时酌情宣布,与她有何相干?叫她去看什么?心生疑惑,然而,皇帝派了心腹近侍大内总管高公公亲自来请,她只有去的份。
美目流转,带些恼怒神色,朦朦水汽,去看那榻上之人。
那人倒是好脾气,扶她起身,一边给她合衣整饰,一边轻声嘱咐她:
“快去快回。”
“你到书房里,看会儿书,消遣消遣?”她瞧着那忍口模样,觉得有些对不住,便出言哄他。
“不,我就在这里……等你。”那人浓浓地叹了一声,嘴角一撇,骄气说来。忽又揽过她后脑,在她唇上狠狠地吃了一口,探手在她腰臀间,重重地抚了一把,才放开她来,示意她下榻快去。
那做派,明明小气,却又大度,明明难耐,却又强忍。散乱黑发,敞胸抹怀,箭在弦上,浑身发浪,却抽着冷气,迁就着她,真是妖得不行。
第一百八十章钦天监之卜()
纵然是妖得不行,惑得她心旌摇荡,仍是只能扔了他在那窗边软榻上。唤了紫衣,替她换宫装,整饰妥当,带了青鸾,立即跟着高大全进宫,径直上云台去。
皇宫西面,云台宗庙,供奉夜氏历代先祖,亦为钦天监观象之所。
每逢国之重举,或皇家大事,皆要祭祖求吉,观象问卦。征伐前夜,自然是皇帝亲自上云台,与钦天监大小巫史一道问吉。
而那观象问卜的卦言,通常会由大巫酌情润色后,在第二日凌晨的三军誓师之时宣布。不管是凶是吉,被那些华藻词章一修饰,与那煌煌礼乐中颂来,便听不出个所以然,统统变成振奋人心的吉言了。
是故,夜云熙倒并不好奇紧张这问吉有何不妥,多半是她那皇弟,多年的习惯使然,每遇大事,总喜来找她说一说,询一询她的主意,实则像孩子般使点小性子,在她这里求一份宽心安慰罢了。
行至宗庙前面的云台,白玉大石铺就的阔场上,见着灯火通明,高冠黑袍的巫史,乌压压跪了一地。皇帝站在殿门中央,衮冕祭服,负手而立,见她来了,便冲着她微微一笑,示意她上前去。似乎是专门在等她的到来。
她于场中两路跪地的巫史中间走过,略仰了臻首,瞧着几阶之上的皇帝,幽亮宫灯下,映得那沉着容颜更加清冷,一身沉色冕服,衬得那高长身姿越发挺拔。
她突然生出一种陌生之感,生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清醒认识,她的弟弟,如今,已经再也不是那个凡事需要询她的少年儿郎,而是一个杀伐决断干净利落的大曦君王。
不由得有些发怵,今夜这阵仗,透着些鸿门宴的煞气。只是,她又想不出,她如今这深宅妇人的境地,还有什么是值得天子忌惮的?
心中翻转,举步上阶时,就差点被脚下裙裾绊住,赶紧双手提裙,踩得稳了,才一步一步地拾阶而上。
等她上了台阶,皇帝便伸手来牵她,一边扶着她进殿,一边笑着与她解释:
“不是朕不识趣,非要在这夜里扰皇姐清静。而是今夜的观象卜言,实在是有必要,请皇姐一看。”
对她,一如既往的恭敬,周到,只是,那似笑非笑的声音里,透着一丝阴寒。
待入了大殿,更多的阴寒之气,便从四面八方,围拢上来,将她缠绕。
大殿尽头,是夜氏历代先祖的牌位神龛,油灯戚戚,连接着遥远的年代,逝去的记忆。空旷殿中,连个坐处都没有,高大龙柱,青玉地面,幽光反射,亮得能照出人影,却只有清冷肃然,不带一丝红尘暖意。
尤其是龙柱旁边立着一人,更让她心生寒冷。
那人高冠黑袍,消瘦面容,鹰鼻深目,仿佛浑身沉寂,与这大殿融在了一起——这位大曦的钦天监大巫,隐在深宫不为人知,却是先帝最器重的观象占卜之人,亦是她从十二岁起,就一直不想正脸去瞧的人。
夜云起扶着她,径直行至大巫面前,从那高举齐眉的两份文牒中,取下第一份,也不说话,只示意她打开来看。
夜云熙接过一看,封面上尚有先帝嘉元年间的密存印记,再细看那日子,嘉元十七年七月十七日。刹那间,她认出这份文牒来,不就是她十二岁生辰之时,大巫所卜得,说她是惑世灾星的天象吗?
瞧着那已经破开的封印,她也不想再一次翻开看了,索性递还了回去,冷了声音,与皇帝说道:
“有什么好看的,这份密宗,我与你不是都看过?”
她不知皇帝将这封存于曦宫藏书楼之顶阁的密宗,拿给她看是何意。云起登基时,她摄政掌权,曾带了他,一道去藏书楼,登上顶阁,强行拆开了看过。
“不看也罢,皇姐可还记得,上面都说了些什么?”皇帝接过去,执在手中,兀自翻开来,凝目细看,带着不可思议的笑意。
她如何不记得,大巫说,七月十七夜,帝星降曦宫,已豆蔻初成。可扶少主,可乱四国,可平天下,可开盛世。但帝星错降女儿身,切记循善引之,万不可堕为惑世灾星。
可是,那又怎样?先帝震怒,不也束之高阁,对她宠爱依旧。彼时她姐弟二人看罢,不也付之一笑,只言要携手图谋天下。
然而,她却忘了,此一时,彼一时。彼时,他是个根基全无的傀儡皇帝,尚需依靠她的家族势力,仰仗她的铁腕扶持,而如今,她的皇弟,似乎已经不再需要她了。
所以,此刻,皇帝合了文牒,抬起头,依旧似笑非笑地看着她,叹息说来:
“朕只是惊叹,大巫卜算预知的神通。嘉元十七年,两位英武神勇的皇兄尚健在,皇姐多数时候,在千语山学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