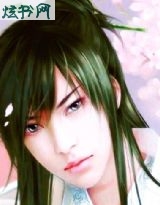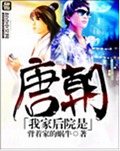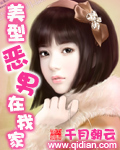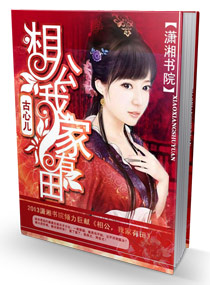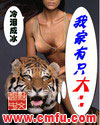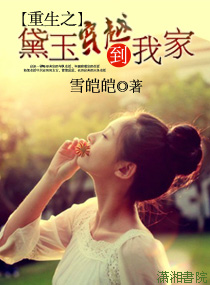翻开我家老影集-第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看不到的,是我们民族独有的宝贝啊。” 她还记得:两人在电影院里看《三毛流浪记》,舅舅感慨地说:“太像了!我和岸青那些年,除了没给资本家当儿子,真是什么都干了。”有这种童年经历的他,格外珍惜今天的生活。然而在保家卫国问题上,他坚定地做出了选择。 出于保密,舅舅没有告诉舅妈自己的去向,一别经年,再也没了消息。已经知道儿子牺牲的外公在忧思成病的她面前,如坐针毡。他决定选择渐进的办法告知真相。比如,他在和儿媳谈话时,经常向这个方向引导:开慧不容易啊!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在家里,没有我的消息。那个年代,不坚强的女子是做不到的呀!直到有一天,中南海摄影组长侯波奶奶笑眯眯地给了舅妈一张照片,上面的舅舅穿着朝鲜人民军服装——她当然还不知道真相,自己还以为在小两口之间带了信,做了好事呐。舅妈顿时明白了什么。 她再找到外公,一老一小先在中南海湖边散步,然后找到一棵古树,在树下坐定。外公开始谈起毛家历史,已经牺牲过五位亲人,他们和自己的关系,当年的故事,怎么牺牲的,家人得知后什么态度,等等……外公看着掩面而泣的儿媳,是否又想起了自己得知噩耗时脱口而出的古文:“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一位位亲人离他而去,只有眼前的古树历经无数代人仍然存在。后来,外公也离开了人世;再过若干年,你、我也将告别尘嚣,但是那棵树可能还是当年的样子。以前,从照片上面、书本当中和老人那里,我熟悉了舅舅和另外五位先辈。现在,我又在大树身上看到了他们,他们仍与我们同在。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三节 岸青舅舅的80年
岸青舅舅1947年在苏联上大学时
我的岸青舅舅,今年80岁了。 经历了1923年来这么多风雨的舅舅,能够跨过新世纪,真是一件应该祝贺的事。现在,他已是北京毛家辈分和年事最高的老人。作为外甥女,作为红色家族研究者,我希望老人能健康、愉快地生活! 岸青舅舅与我的外婆贺子珍曾经彼此关爱,在莫斯科相聚的日子恐怕是岸英舅舅前半生和外婆在苏联期间最开心的了。后来再加上我的妈妈,四岁的她一到异国,马上成为两个哥哥宠爱的对象,给了生下不久就孤身留在保育院的我妈妈从来未有的满足感。1947年,外婆带着妈妈和岸青舅舅一起回国,直到1949年她把两个孩子托人送到他们父亲身边,舅舅在外婆身边断断续续生活五六年。由于这期间得到的珍贵的母爱,岸青舅舅在20世纪50年代曾和妈妈说过:我觉得贺妈妈好!我想念贺妈妈! 虽然外婆和岸青舅舅此后再没见面,我认为他们的心灵还是相通的。而后来无法把儿子留在身边的外公,也和后来托妈妈关照外婆一样,交给了她关照岸青舅舅的任务。几十年来,妈妈从未忘记父亲交给自己的这个职责,始终把岸青舅舅放在心上,哪怕自己也曾重病缠身。他们的兄妹情是让人感动的。 搬进中南海之后,岸青舅舅病情已比较严重,他向外公身边的王医生说,自己脑子里有两个小人在打架。直到有一天,病情发展到他拉着妈妈的手说:咱们跳中南海吧!十几岁的妈妈被弄得不知所措,幸好被卫士发现才拉开了他俩。 在外公、妈妈以至很多好心人的关爱下,岸青舅舅后来虽然搬出了中南海,但在大连休养的那段时间病情大有起色。他还做了很长一段俄语翻译工作(工作时的他思维清晰,根本不像病人),退休后始终过着平静的老年生活,而人们也并没有忘记外公这位惟一在世,同时又有着坎坷经历的儿子。 岸青舅舅的夫人邵华是岸英舅舅夫人刘思齐的同母异父妹妹。两兄弟娶两姐妹,和外公与泽覃外公和外婆与贺怡姨婆的关系一样,也是毛家一件趣事。舅妈多年照顾病中的舅舅,有“贤妻良母”之称。 舅妈是北大中文系的学生,常有机会和我的外公谈论文学,特别是中国古典诗词。外公和她谈过自己喜欢的诗人,如陆游、曹操、王勃等等,并手书陆游的“夜游宫”留给舅妈。这些年来,她写了许多文章以纪念我的外公和开慧外婆等亲人,有的曾经编进中学语文课本,成为范文。 现在,舅妈邵华,姨妈李讷和我妈妈李敏同为全国政协委员。 岸青舅舅的独子毛新宇比我大两岁。按照我在韶山看到的家谱,他本该是“祖恩贻泽远,世代永承昌”中的“世”字辈。但消除了中国家族制度的外公,已无需给自己的孙子取谱名了。新宇表哥的小名叫毛毛,这和他叔叔辈的毛岸红是一样的。 从《我的伯父毛岸英》一书提供的简历就可知道:他专攻历史,已写下不少论文专著,执导过几部电视长片,俨然一位青年学者。听说,新宇哥哥已经拿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专业的博士证书,这对正在研读博士的我,无疑是又一个颇感鼓舞的好消息。 。 想看书来
第一节 外婆贺子珍的前半生(一)
贺子珍,原名桂圆,又名自珍。生于1909年中秋,江西永新乡绅贺焕文长女。大革命前后入党并投身游击战争,是井冈山第一位女党员。1928年与毛泽东结合,共同度过共产党人最困难的十年岁月,是中央红军长征中“三十女杰”之一。1937年赴苏联疗伤、学习,1947年回国。1959年曾与分别22年的毛泽东会面。1984年在上海逝世。共生三子三女,除女儿李敏外均早夭或失散。 这可能是我外婆第一张照片。那年她22岁,少女时“永新一枝花”的风采,应该还存有些许吧?这里先要从头发说起——外婆贺子珍曾是家乡江西永新县第一任妇女部长、团县委副书记,当时她不过才16岁。当了这两个“官”,外婆觉得从小留起来的又粗又长,又黑又亮的辫子有些与形象不符,一狠心剪掉,变成干净利落的男式西装头。她的工作是宣传鼓动群众,据说20世纪80年代永新城里的老人还记得一场由外婆组织并参加表演的“葡萄仙子”歌舞剧。原来,她曾经是相当活跃的文艺爱好者。 说到歌舞,又把我拉回与外婆在一起的日子。病情自顾不暇的外婆不会知道:身边的小东梅,也是一个爱唱爱跳的丫头。只不过,她因为寂寞、因为羞涩、因为胆小,在上海那座所有工作人员说话走路都静悄悄的洋房里,唱歌跳舞时都是一个人。轻轻的甚至默默的,心里数着节奏和旋律,假想着舞台和观众…… 现在想来,我最成功的一次舞蹈经历是八岁那次:观众是外婆,地点是解放军总医院南楼高干病房——外婆来北京住院的地方。因为,那里有宽敞的客厅、柔软的地毯,最让我满意的,是有一幅横挂在房内,像模像样的大红幕布。一看到它,我就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起来,并把这次即兴表演献给了卧床的外婆。 此后,在成长的岁月中,我歌过、舞过、笑过、哭过。那个独自向隅,亦歌亦舞的小姑娘,似乎已尘封在记忆深处,定格在小小的黑白照片中了。只是到了30岁以后,往事反而清晰起来。经历这些年风雨,我从没像现在这样理解外婆、了解妈妈、化解自己。于是,一点点拾起记忆的碎片,拼凑成各种可能的形状,最终形成这本书。里面装的,其实就是我们祖孙几代人的一些思索。 至于刚才那张照片,我查到了这样的说法:苏区召开第一届工农代表大会时,几个平素要好的女红军看到请来的照相馆师傅,大家嚷嚷着要照。曾碧漪却不情愿,因为她已怀孕,挺个大肚子。彭儒出了个主意:没事,我陪你坐在前面,这样照了看不出来。照片上贺子珍站在后排最右侧,齐耳的短发格外精神。毛泽东在旁开起玩笑:照得好,将来给你们放到博物馆里去呦! 外婆的五位战友: 彭儒(丈夫陈正人),外婆参加过她在井冈山简朴的婚礼,在东北期间曾照顾过她的孩子,外婆豪爽好客的天性决定了当时的热情程度甚至让我妈妈感到嫉妒。 曾碧漪(丈夫古柏),外婆的同事、外公的秘书,外婆广为人知的名字“贺子珍”即出自她的笔误。她们曾被敌机轰炸掀起的泥土没顶多时,险些成了烈士,可谓生死之交。 康克清(丈夫朱德),正如朱、毛之间不可分割的友谊,外婆与朱老总两位夫人——牺牲的伍若兰和江西老乡康克清都是好友。她到北京住院后,第一个来访的就是康奶奶。 钱希均(丈夫毛泽民),外婆的妯娌。在苏区她们携手解放童养媳,长征中在休养连相互扶持。外婆在贵州遭敌机轰炸,弹片入身几乎不治时,多亏她在旁照料才得以苏醒。 周月林(丈夫梁柏台),就是搂着外婆肩膀的那位。长征时被留在苏区,其后被冤屈关押多年,坎坷经历令我不忍重述。在六人中,她所承受的苦难是惟一可与外婆相比的。 。 想看书来
第一节 外婆贺子珍的前半生(二)
外婆早年照片很少,妈妈和我一直都留心收集并将其放进本书。真感谢《西行漫记》作者——美国记者斯诺先生,他拍摄并翻拍了大量红军苏区时期和陕北时期照片,也保留了其中外婆的形象。更何况他还撰写了《毛泽东夫人贺子珍小传》,使外婆第一次在红区以外广为人知。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三年后当他再次见到外公时,毛夫人已是另外一位了。 前面这幅照片,恐怕是外婆与外公照片中被引用最多的。究其原因,也许是外公没戴帽子(据斯诺说:他当时头发太长,而且也不愿戴帽子),蓬松向后的长发透露出隐藏不住的诗人气质。而外婆戴着帽子,则引出了又一个与女人头发有关的故事。 原来,之所以外婆在陕北的照片都无一例外戴着帽子,除了她以军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之外,真正的原因是:长征的艰苦环境让女战士暂时别离了爱美的天性,让如影随形、挥之不去的虱子消失的最好办法就是剃光头,与外婆一起剃的还有张闻天之妻刘英奶奶。一直到她们俩为赴苏而结伴去西安、兰州时,那缕缕青丝才慢慢冒将出来。 我无法想象,照片中的外婆刚以伤病之躯走过万里长征。这使她与父母和儿子生离死别;十几年思念生死未卜的哥哥、妹妹;惨失弟弟(被自己同志所错杀);痛别女儿(生下后却不能带走),除了这些人伦巨变,身上还多了十几块异物——经常阵阵作痛,刺激神经的弹片,又落下一身疾病:贫血、晕眩……即便如此,她仍在微笑。我想:除了长期征战后的短暂和平、充实的学习和工作以外,这是因为她有一个相伴走过人间绝境的丈夫。 为掩护战友遭敌机轰炸,十几块弹片嵌入身体那次,无疑是外婆十年征战中最危险的时刻。当时她用微弱的声音告诉外公:我不能工作,还让人抬着,心里很不安。润芝,把我留下,你们走吧。革命胜利后,我们再相见。外公一阵心酸,劝慰妻子说:我们决不会把你留下,抬也要抬到目的地。若不是他下了死命令把妻子抬走,外婆一定会因伤重牺牲在贵州。 被外公外婆忠贞战地爱情而感动,写到此处,我过了好一阵情绪才平静下来。是啊,还要继续前行,外婆后50年的传奇人生等待着我去追寻。 在美国记者斯诺眼中和他的《西行漫记》里,毛先生和毛夫人是颇和谐的一对。在他记录外公自述时,外婆被丈夫那些从未说过的内心独白而吸引,成了入迷的听众。她捉到一只油灯下的飞蛾,夫妻俩像儿童似的一边惊叹它的美丽,一边小心地把它夹在书中。斯诺还把外婆发展成牌友俱乐部中的一员,人们时常见到她和其他首长夫人出没于斯诺的窑洞中。 说来也怪,近年全国多处发现由《西行漫记》辑出的单行本《毛泽东自传》。它就像外婆一样,被遗忘多年后,逐渐显露出应有的价值。须知:这是截至外公去世,国内出版的惟一一本刊登夫妻照片的外公自传。 还好,外婆除了上述夫妻合影,还留下了这张集体合影。显而易见,她是所有人中惟一的女性。从井冈山烽火中走来的她,随丈夫丈量了中国十余省的土地。好不容易在陕北有了落脚的地方,为了治疗严重困扰她的伤痛,又马不停蹄赶奔万里之外的国度,从此结束了军人生涯,告别了照片中的同志和战友们。 第二节 外婆贺子珍的前半生(三) 即使作为外孙女,我觉得也毋庸讳言:外婆十年苏联之旅,从头到尾由一连串的决策错误组成。时光荏苒,她身边那个胆小怕羞的小姑娘20多年后也踏出国门,经历了异乡生活。当然这不是说我就具备了足以评判外婆的经验。这里要写的,一是那些公认的和她自己也承认的错误,二是为什么出错。当然,只是最粗浅的分析。后人总是容易一边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得以省力,一边又苛责前人长得不高,这是我尽量避免的倾向。 十年军旅生涯,给外婆“颁发”的不是纪念章,而是深埋体内的十余块弹片。这给她带来的痛苦,非我们这些毫无体验的后辈所能理解。她急需取出它们,同时还想治愈自己多年来积累下的其它伤痛,这是理所当然的。 众所周知:抗战初被友军误伤的林彪不就赴苏治疗多年吗?但子弹擦伤神经的后果一直没办法治疗,苏联专家下的猛药反而给他带来终身怕水、怕光、怕风的“毛病”,其实他确实一直是个没被治好的病人。另外,给妈妈起名的邓颖超不也以化名住进北平西山,治疗她在长征中发作的肺结核吗?外婆本来也是想在国内解决问题,她想的是当时医术最高明的上海。可惜又耽误了时机,准备出发时日本已发动侵华战争,上海首当其冲成为“八·一三”战场。邓奶奶也是在美国朋友斯诺的掩护下才惊险逃离北平敌特搜查的。 对这个理由,外公有自己的看法:延安现在穷,但会发展的,也会有自己的医生,条件会好起来的,何必非大老远去苏联呢?这也已被事实验证,如果外婆不走,肯定会得到来华并到过延安的名医——比如非常佩服外公的白求恩大夫精心的治疗。当然,外人可以说:弹片不在你身上,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