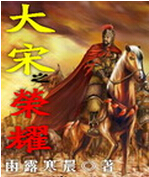大宋遗事-第8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应手续俱全,也动弹不得的。只好驳回上诉,让刘老太太呼天抢地去了。
刘老太太虽然败了诉,御史们却胜诉了。他们一得到消息,就纷纷上书,告张方平以权谋私,低价强买管下商人住房。既是铁证如山,房子即使手续合法动不了,三司使是断然不能当了。一纸诰书下来,叫他出知陈州,后来又改成知应天府。接替他的,是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吏部侍郎、集贤殿修撰宋祁。可宋祁位子还没坐热,就落职知郑州去了。
原来,宋祁也不干净。
他知定州时,让家人白借了好多公使钱用了,州治也搞得不像样子。到调益州当知州,还是老毛病,纵情游宴,吃喝玩乐。这都是摆在面上的事情,人人看得见。御史们当时就上章弹劾了,说他根本不配做理财官。加上他老哥宋庠正做枢密使,弟兄俩不能同在中枢,他需要回避。最后,到底被调到郑州去了。
要找个干净的人做三司使,可真不容易。找来找去,合适的唯有阎罗老包包拯。他不还在做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吗?一道命令,便改成了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他虽然清白,可还是挡不住有人说话。
这次,问题出在包龙图自己的嘴上。原来,上书扳倒两个前任,都有他包龙图的份儿。他是言官,一向又耿直好事,眼里揉不得沙子,他要说话,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说张方平,是直接去的中书,大骂宰相用人不当,竟将这样少廉寡耻的东西放在财政大位上!说宋祁,平和一点了,只是上书,既提他益州游乐无度,也说他弟兄俩不能同在中枢。既然攻走了两个前任,自己李代桃僵,却连假心假意推辞都不推辞一下,就那么理直气壮地上了班,这是什么事儿呵?
他这里一上班,攻的人就摇旗呐喊,蜂拥而上了。包龙图是个直肠子,缺的就是弯弯绕。否则,只要稍微绕个弯儿,他也会想到,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躲还躲不及呢,怎么冲着三司使的位子,就那么直截了当去坐了!不是没事找事吗?可他愣是想不到!
起先,他仍然理直气壮。到欧阳修也上书攻他,他才悟出问题的严重了。
欧阳修打的旗号是:全包拯名节,保朝廷风俗。
他自然有他的道理。
这治理天下,重在用人。用人之法,各有所宜。将士先才能,朝臣先名节。为什么呢?军旅要成功,唯恐将士们不趋赏争利,自然只能以才能为先。朝廷主教化,臣子们的行为,直接关乎风俗厚薄、政治清明,自然只能以名节为先。既是这样,做臣子就应该自尊自重,做君上也应该处处爱惜、保全臣下的名节。包拯逐其人而代其位,就是无心,也说不清楚。你把手伸到人家口袋里拿东西,嘴上再说不想要,也没个人信你不是?而蹊田夺牛,又岂能无过!这都是因为包拯尽管峭直,却不太注重学问,所以临事不能处之以义,有所为而有所不为。朝廷要真正爱惜包拯的名节,就应当在他看不到的时候拉他一把,不管让他做什么,就是不要让他做三司使!
大宋遗事 第四十二回(5)
除此之外,欧阳修看得还要深远,竟看到了这件事的未来影响。道理也很简单。有所不取才是廉,有所不为才有耻。从来言谏官说话都不带有个人目的,这已经成了风气。现在叫包拯这么一闹,取其不当取,为其不当为,不管怎么说,也会诱使人跟着起哄,将带着个人目的说话,当成正当行为。那么,已经形成的好风气,不就要毁于一旦了吗?这实在太可怕了!
说得这么义正词严,理直气壮,任你是阎罗老包,还敢再无动于衷吗?他躲在家里再不上班了!
也不知道朝廷是顾不上,还是不以为然,竟没有解除包龙图的职。不但不解,连包阎罗辞职也不准。既然这样,总不能老躲在家里,最后还是上班了。可经过这么一折腾,就是包阎罗,还有多少心气儿去理事,也不能不打个折扣了。他这三司使到底没当长,很快就改了枢密副使。不久,便一病而亡了。朝廷虽褒奖有加,赠了他礼部尚书,谥号孝肃,毕竟都是虚的,指望他大刀阔斧去张罗经济之道,再也甭想了!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大宋遗事 第四十三回(1)
先达后至途径有自
你辞他让才性所宜
安石到三司任度支判官,司马光已先在三司任度支员外郎了,只是主管的部门不同而已。他不是随庞籍到并州去当通判了吗?那是早几年的事情了。他在并州闯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纰漏,早调过好几任了。
当通判当得好好的,怎么会闯什么纰漏呢?这话,说起来就稍微有点长了。
早在庆历八年正月,争天夺地的西夏国主元昊到底挣不过命去,一命呜呼了,死的时候才不过四十六岁。他虽然死了,可国势已经确立,西夏国仍旧稳如泰山。他们也是长子继承制,由长子谅祚继承了皇位。谅祚小名叫宁令哥。“宁令”是西夏话的译音,翻成汉语就是“欢嘉”,一样透着吉祥喜庆的意思。跟他一起执掌山河的,是他舅家的讹庞。谅祚从小是在舅舅家长大的,自然母舅一族的人来得亲热。这一亲热不要紧,有两个人可就倒了血霉了!谁?就是左、右丞相张元、吴昊。
讹庞的理由很简单:“咱们鲜卑人的家,怎么能叫两个汉人把持?要是这样,咱们干吗还要立国?在赵家皇帝手下做顺民,不更省事?”
谅祚觉得不错:“是呵,早该夺权!只是,拿他们怎么办呢?他们也做过不少好事。”
讹庞自有主意:“皇上不必担心。也不是要将他们怎么样。先皇帝早就托梦给我了,他那儿正缺大臣!左右丞相不去辅助他,怎么成?请皇上加封他俩为王,赐他们自裁,追随先皇去吧!”
于是,两个人一个成了石王,一个成了韦王:石王封地在石州,韦王封地在韦州。两个人正为封王加爵高兴呢,讹庞又宣布了皇上的旨意:“现有御赐琼浆两杯,着两位新王立饮,好侍奉先帝。先帝托梦给我,一定要两位大人去,只好有劳二位了!”两个人这才傻了眼,吴昊很快就号啕大哭了。
张元到底比吴昊痛快大气,不但没哭,略傻了一会儿,就劝吴昊说:“甭哼哼唧唧的了,上路吧!我叫张元,你叫吴昊,去了姓,加起来就是元昊,正合了先帝的名字。我们与先帝一场,风云际会,该是因缘凑合。他既去了,我们还能久吗?国舅爷的梦,哪里会虚做呢!体体面面地死去,不比不招人待见,满门抄斩,血溅法场强多了!哈哈哈!”
吴昊还在发木呢,张元又突然高歌起来:
中土无缘,缘在外边。夷华两违,有泪空垂。
中土无号,号在毡包。胡汉成仇,有泪空流。
唱到“胡汉成仇,有泪空流”,张元再也忍不住,到底涕泪滂沱了!一面流泪,又随口吟道:
叛离中华,难入胡夏。风云叱咤,做鬼无家!
吟罢,又是哈哈一笑,朝讹庞一拱手:“国舅爷,请了!”端起赐酒,一仰脖子就干了。喝毕,又找补了一句:“但愿皇上将来也能梦见国舅爷,咱们地下见吧!”
吴昊听了张元的解嘲,蓦然想起大觉寺的住持觉踪,似乎也明白什么了,破涕为笑道:“说的也是,说的也是。国舅爷请了,洒家也去了,等您!”也端起御酒干了。
也许是这最后的悲壮打动了讹庞,讹庞竟没有计较两位的期待,朝他们一一拱手:“朝廷也有苦衷,请二位大人原谅。二位这也是为国尽忠,皇上不会忘了你们的功劳!不仅要厚葬,也会照南朝的规矩谥以尊号;你们的亲属,也会受到应有的关照。”
可两位新王已经蹬腿而去,什么也听不到了。
为了掩人耳目,讹庞又建议谅祚,下令全境改服汉人衣冠,还巴巴地将这事专门报告了大宋。虽然如此,可那政策方略却一点儿也没改变:还是与大宋朝明争暗斗。麟州州城朝西七十里,才是边界。可西夏人的耕地,却过了窟野河,愣是耕到了麟州西城门门楼底下。西夏人为了保耕保收,常常还要派军队过来护卫。麟州的官员与将士,早有人想乘西夏人退走的时候,跨过窟野河筑两座城堡,派兵守卫,一来增强边防,二来阻止西夏人前来耕种。庞籍不是河东路经略安抚使嘛,麟州正在辖下。司马光受庞籍之命去巡边,他们又说了。司马光想想,很好嘛!回来就竭力怂恿庞籍。庞籍对君实从来言听计从,终于拍了板,跨过边境,离窟野河二十来里,修了两座新城堡。西夏人自然不干,跑来挑衅,用的还是老办法:诱敌深入。一仗下来,大宋将军死的死,俘的俘,兵士、物资损失惨重。司马光这才悟出自己当了冤大头!这么多年,守边官员之所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是没看到问题,而是边衅根本就不可兴!可事情已经出了,懊悔也晚了。
朝廷追查责任的时候,战场失利的军官及相关责任人,首先被贬了官;跟着,庞籍也被贬到青州去了。庞籍死活不提事情是由司马光挑起来的,连他的上书都隐而不报,全由自己兜了,好歹将司马光保了下来。司马光不过意,也上书请求处分,可到底没人动他。不但没动,很快,朝廷还赐了他五品官服,升他做了开封府的推官。
奇怪吗?一点也不。朝中无人不做官哪!
庞籍毕竟是做过宰相的人,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就是下台去位,眼下又因为直接责任被贬了官,可那影响、势力毕竟还在;老于仕途的人,得意失意,从来都不将事情做绝。留一线,好见面啊!说不准什么时候,乾坤颠倒,自己反倒要求着人家了。所以,很少有人根本不买这下台宰相的账。庞籍不但竭力保住司马君实不受处理,还要乘着辩护的由头,鼎力举荐他升官晋爵。自然只有大官僚,才会有这样丰富的想像、胆识与马力;一般的官僚,甭说想,连做梦也做不到这一点。有庞籍这样的后台玩命出力,司马君实早已有了五成胜算。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大宋遗事 第四十三回(2)
还有五成,就是君实自己的修为了。并州出事,他的恩公贬官,他没有推卸责任,而是也要求承担自己应有的一份。不管这种行为出于主动,还是出于无奈,它比一推了事,文过饰非,落井下石,总要好得多。在官场上,这就是一种难得的品格了。见惯了官场险恶的人,谁不愿意将这样一个可以信赖的人,网罗到自己的麾下?
二五得十。有了十成胜算,不可能的事也就可能了。再不可能,反倒怪了。
庞籍走的是富弼的路子。他不是说过富弼的坏话吗?没错。可谁说自己看不上的人,就不能求他呢?要是那样,官场也就不叫官场了。不但求了富弼,他还认定这位好好先生一准会帮这个忙。
果然,富弼对送信的人说:“告诉你们庞大人,请他放心。司马光这个人,朝廷是要用的。不但要用,还要大用。是人,谁能没个错?知道错了,能改,就行了。何况,并州这事,司马光责任虽有,也很有限。”
不久,就用了敕命,任司马光为直秘阁、开封府推官,赐五品官服。
司马光却有些诚惶诚恐。他的老家不是陕州夏县吗,他想的,是到离老家不远的虢州或庆成军去做个州官什么的。离家近了,一可以慰解思乡之渴,二可以照顾祖上坟茔;而没有说出口的理由,则是并州的事叫他害怕,他想找个事少任简的地方息息肩。开封府的官本来就让人谈虎色变,推官管的又是刑狱诸事,事繁任重,张嘴就可能得罪权贵,连并州都没法儿比,这不是往坑里跳吗?这么想着,当时就上书推辞了,直接请求去知虢州或庆成军。可朝廷不准,他只好勉强上任了。
见了富弼,他还想请他帮忙:“丞相,您知道的,我这个人生来愚笨,根本不是吏治的材料。开封府推官事繁职重,更弄不来了。这么着下去,于公于私都不好。请大人关心,还是让我去虢州或庆成军吧!我已经上过折子,大人是不是看到了?”
富弼一笑:“君实,庞大人既将你托付给我,我能不关照你吗?折子早看到了,你的难处与想法我也理解,熬一熬就过去了嘛。越是难做的官,才越容易出彩!尤其是京官,天子脚下,近水楼台,你打个喷嚏,就顶得上边远州郡炸个响雷。老夫的这一番用心,你该明白?”
这是掏心窝的话,君实能不明白吗?除了感谢,也真说不出别的了。
好不容易熬了半年,连身体都顶不住了。这么熬下去,哪儿是个头呢?顾不得许多了,他又去找了富弼:“丞相,您老救救我!再这么熬下去,不等出头,我怕就要干了!”
富弼是做过开封府推官的,并没觉着什么,哪里会弄到这个地步?可看看他一脸气急败坏的样子,不像是假话,便问道:“哪里就到了这个份上?你想去哪儿?”
君实说:“最近身体精神都不好,我只想找个闲散地方。听说虢州有缺,我还是想去虢州。如果虢州已经派了人,让我去判登闻鼓院或尚书省的任何一个闲慢司局,都成。大人的爱护栽培我不是不知道,实在熬不下去了!”
富弼想想,或者真是禀性所系,不能强求的?便安慰君实:“你上个折子吧,我来设法给你挪一挪。”
君实回去就上了个折子。批复下来,升他去三司判度支局院。理财?又是一个让他头痛的差事!他当即上了一本,除了请求改派虢州、登闻鼓院或闲慢司局等等,怕没有空缺,作为替补,又提出陕州附近的绛州、乾州或者在京的任何一个闲慢差事。
说给富弼,富弼这回也烦了。虽还是笑嘻嘻的,话却没有仔细掂量:“君实,多一种繁难,不是多一份历练吗?这也怕难,那也嫌烦,你干脆别出来做官好了!无官才一身轻哪!既当官,哪有不烦的?好好去做一段时间,再说吧!”
跟着朝廷也批复不准,君实没辙了,只好去三司当度支员外郎了。这一当,就当了两年。安石来时,他还在任上呢。
两人虽同在三司,除官职小有不同,还有一个区别:一个带馆职,一个不带。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