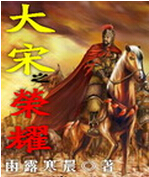大宋遗事-第6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更要胜过千倍万倍。
他从不讳言这种乐趣,总好对人说:“读书,不能不背书。只有背熟了,才能真正领略它的意思。凡经典,我都是这样读的。马背上,灯影下,床笫间,甚至稠人广众之中,背上一段圣贤书,反复推敲领会,那种乐趣实在无法形容!凡圣贤之作,不这样读,也还真难了解它的微言大义。”
这种迂劲儿,要真正付诸实践,除他之外,恐怕也真难再找到第二个人了。对此,司马光自己似乎也很清楚,还颇有点儿为它而自豪:干脆就自称迂叟了,将自己所著的书也就称做《迂书》。不但为《迂书》写了序,说明它何以取名《迂书》,还专门写了一篇《释迂》、一篇《辨庸》,为自己的迂而庸作了专题辩护。这,又岂是一般人所能想像的呢!
既这么迷书,信起来当然会更痴,更势不可挡了。
司马光的父亲叫司马池,字和中,历任真宗、仁宗两朝,做过转运使、三司副使、几任知州,一直做到天章阁待制、尚书吏部郎中。虽然清直有名,吏事上却不大能干,最后也就栽在这上头:由杭州贬到虢州,再调晋州,晋州没满任就去世了。司马光因为有父亲的荫庇,十五岁就当了官:补了郊社斋郎,再升就做将作监主簿了。皇恩这么浩荡,做臣子的能不殚精竭虑想着报答吗?从此,他就日日夜夜想着这件事了。
睡得正香呢,他能突然一个鲤鱼打挺坐起来,很快穿上官服,拿上手板,到一切就绪,就端坐在那儿再也不动了,一坐就是一两个时辰。家里人先还吃惊,及至看他常常如此,又知道他有那么个痴性,也就见怪不怪,连问都不去问他了。
大宋遗事 第三十回(2)
后来跟他编《资治通鉴》的范祖禹,有意问他:“司马大人,有件事一直想问您,又不大好启齿。”
祖禹是司马光好友范镇的堂孙,司马光一向将他当子孙辈看,又跟他修书多时,这么慎重其事,当然叫司马光纳闷,他不禁反问道:“难道有什么隐秘,要这么郑重其事?我一生所作所为,从来没有见不得人的,件件可以公开。你只管问。”
范祖禹说:“那我可就问了!”
“不是说了吗?”
“大家都说您年轻的时候,常常睡着睡着就一个惊打醒了,然后穿起官服,拿上手板,一坐就是一两个时辰,有这事吗?”
“有。”
“您干吗呢?”
司马光忍不住笑了:“嘿,就问这个?这有什么?那时年轻,刚刚做官,常常猛不丁想起国家的事情。一想,就再睡不着了,索性坐起来想想明白。”
范祖禹一听这样,也忍不住笑了。
做官做到这个份上,又有几个人能比呢?
圣贤们最重礼、乐,司马光自然也特看重它们。
他治家,那叫一个严。
洒扫庭除,长幼有序,进退中节,昏定晨省,等等,一般常礼不用说了。单有两点,就可以想见一斑。
一是,他主张“男治外事,女治内事”。所有妇女,没有特别事情,都不得超过中门一步,不但不准出来,连随便看看也不准。不仅主人如此,连女仆也一样。实在有事要出来,怎么办?得戴上盖头:用一方幅紫罗盖在头上,遮住头脸与上半个身子。女人既不准出来,男人——主要是男仆,当然也就不准随意进出中门以内了。实在有事进去,必须事先通报,好让女人们及时回避;要是事变仓促,来不及呢,女人得用自己的衣袖蒙住头脸,千万甭叫男人们看见了。这是男女大防,不准失礼。要是真的失了,就得受到严厉惩处。幸亏司马家几代人做官,在京中榆林巷附近也有三进以上的房子。要是连个中门也没有,这内外之别,还真没法儿弄呢!司马光的这些讲究,也真有影响:弄得妓女们出门,也不得不弄个盖头系在冠子上,让它满城迎风飘扬。
从来上元节都有几天灯会,万民同欢。一年到头,似乎也只有这么几天,男女界限特别松动,不能轻易出门的妇女都被允许上街瞅瞅热闹。司马光的夫人张夫人原是大家闺秀,本来就懂礼,又遇到丈夫这么严格家道,自然更守礼如仪。可再怎么守礼,也不会心如死水呀!至少,好奇心多少总会有一些的。
她也想去看看灯会。
知道司马光不好说话,张夫人只好先拐点弯子:“相公,知道今儿是几吗?”
这当然知道,司马光不用思考就答道:“怎么,连今儿是什么日子都忘了?十五呵。”
“这我知道。十五是什么节?”
“夫人今天是怎么啦,连上元节都要问我?”司马光已经觉着奇怪了。
“上元节又叫什么?”夫人又垫了一句。
“上元节嘛——”司马光想了想,才又接着说道,“又叫元宵节。”
“又叫灯节!今儿是灯节,我想出去看看灯!”张夫人见司马光老是不上正题,急了,再顾不上拐弯抹角,干脆直言摆上了。
“灯有什么好看?家里有的是,还用得着出去看?”司马光大惑不解。
“不是看灯,我想出去看看人!”张夫人急中生智,突然冒出这么一句。
“我难道是鬼?”司马光也扔出一个让张夫人想都没法儿想的问题。
张夫人一下被打蒙了,再也不提出去看什么灯了。
司马光不仅对别人严,他对自己也一毫不肯放松。
司马池有两个好朋友,一个叫张存,一个叫庞籍。两个人都是高官:张存做到礼部尚书,庞籍更做到宰相。司马光打还不大懂事起,就随着父亲与这两个人周旋,这两个人还能不看好他吗?这种荫庇是无形的,远不是一个小小的郊社斋郎所能比拟的。张存爱屋及乌,干脆将女儿嫁给了司马光,就是张夫人了;庞籍既不能再嫁女儿,就竭力从其他方面给司马光实实在在的关怀。这种关心因为有权力做后盾,当然更实惠,叫司马光终身受益。
司马光与张夫人虽结婚多年,却没生儿子。司马池、张存都已经过世,关心这件事的只有庞籍老两口了。两个人一商量,决定给司马光买个小妾。
张夫人是个懂事守礼的人,特开通。征求她意见时,她说:“子嗣上的事,我也着急着呢!这再好不过了。只是——”
“只是什么?”庞籍的老伴刘夫人以为她要找借口,赶紧问道。
“我家相公与一般人不一样。这事我也多次与他提过,他只是不肯。我怕他又要弄性子,辜负了两位老人家的一番心意!”
刘夫人听了,微微一笑:“嘿,他怕是假撇清吧!普天之下,哪有猫儿不吃腥的!这事你甭管了,交给我好了。”
刘夫人叫来媒婆,花大价钱买来一个好人家儿女,起名翠红,才十六七岁,聪明伶俐不说,长得也算水灵,悄悄送到司马光府上。本想不久两个人就会颠鸾倒凤,谁知过了一两个月,仍然虾不动鱼不跳。
庞籍说:“肯定是张丫头霸着不让贤,光说得好听。”
刘夫人说:“张丫头不像那种人,你不要乱说。”
大宋遗事 第三十回(3)
庞籍说:“女人都是这个德性!”
刘夫人一听这话,火了:“说话别带意思,指桑骂槐!都七八个小老婆了,你还不够!”
庞籍只好缴械:“好了好了,我又不是说你,你疑什么心?哪个也不能比夫人大度!赶紧想办法了了那边的事吧!”
“本来嘛!”刘夫人这才收了兵,赶着去设计布阵了。
她先交代了翠红几句,就将张夫人接回家赏花去了:“咱娘们儿且到我家赏花去,也给人家留个机会。”
张夫人虽听着别扭,也无可推托,只好跟着一起走了。
翠红浓妆艳抹,端着茶水扭扭捏捏进了书房:“相公请用茶!”
司马光一听声音不对,抬头一看,是个姑娘,打扮得十分齐整,认得是翠红,眉头一皱,问道:“夫人不在家,你跑到书房来干什么?”
翠红脸一红,丢下茶杯就跑了。
跑也不是办法呵!刘夫人与主母早就有过交代,自己进门,又为着什么?还得前去兜搭。
这次是去沏茶,或收茶杯。
司马光正看书,没在意。站了好一会儿,见司马光还是心不在焉,翠红只好开口问道:“老爷,还要茶不要?”
司马光这才发现翠红又来了,皱皱眉问道:“你怎么还在这儿?宝儿呢?”宝儿是跟司马光的小厮,也被刘夫人打发走了。
“都有事去了,刘夫人与夫人特意交代奴婢侍候好老爷!”
司马光听她这么说,不言语了,只是闷头读书。
翠红站了会儿,无聊得慌,见房里稍微有些零乱,就动手收拾起来。刚捡起几卷书要归拢,就听司马光叫道:“呵呀,那是《尚书》!你怎么能动《尚书》呢?得罪,得罪!”
一面说,一面已经走过来,对着那几本书忙不迭地打躬作揖。羞得翠红再也站不住,一扭身朝外跑去。还没到门口,就“哇”的一声哭了。
司马光摇摇头:“毛病!动了《尚书》,我还没找她算账,她倒先委屈起来了!”
这件事传出去之后,又被人添油加醋渲染一番,变得更离奇了。有那嘴损的,便刻意挖苦说:“嘿,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司马相如当年那么怜香惜玉,到司马大人这一代,不要说不会弹琴,连个找上门来的卓文君,也愣是给他活活气跑了!”
重礼之外,就是重乐了。因为下的是死工夫,记诵之学根底不薄,关于音乐的那些琐事,他也真能说个一二三四。李照反对王朴,改乐不是改得莫衷一是吗?仁宗始终放不下这件事,大臣们也有一直抓住不放的。祠部员外郎、直秘阁、判吏部南曹范镇,字景仁,就倒拎书袋,掰着手数黍粒儿,说现在的乐器都不合古制,应当重新改过。怎么改呢?他提出一套新规格,要等找到“真黍”,再重新铸造乐器。范镇斩钉截铁地强调,唯有自己得的才是古法,只有自己的规格才是唯一合乎古制的正宗。司马光正当集贤校理,也倒拎着书袋,掰着手儿细数了一下,觉得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当即也上了一本,将范镇驳得体无完肤。范镇既是唯一得到古法的,岂能任人信口雌黄?当然要反驳。这样,两人你来我往,竟扯得难解难分。好歹说的都不着边际,两个人又都主张“乐者,和气也”,还不至于伤着什么和气。世上真正懂钟律之学的几乎没有,自然难得插嘴,只好任他们两个争得昏天黑地了。
重礼,重乐,自然要重道德建设。司马光在馆阁待过,能读到秘阁的藏书。有一天突然发现了一本《古文孝经传注》,甭说有多高兴了!这《古文孝经》是先秦古书,不靠这本传注,早就湮没了。他当时就写了一卷《古文孝经指解》,在传注的基础上又将孝经条分缕析了一番,加上一篇序文,献给了皇上。那意思,自然是希望皇上一看就明白,然后身体力行,将它推而广之。孝悌原来就是圣人持家治国的根本,那账在孔夫子那里就算得特清楚了:为人孝悌的,绝不会犯上作乱。没人犯上作乱,自然会长治久安。司马光将孝道当作圣人道德的极点,安邦治国的本源,正是秉承了圣人的遗训。只是皇上并不那么热心,不过批了几个字,将他的《指解》直接送到秘阁去了。秘阁又多了一本藏书,倒也不能算是坏事。
说到官运,因为有父亲及张存、庞籍有形无形的荫庇,司马光自然要比一般人亨通得多。斋郎虽也是官,毕竟太小,作为起点实在太低。到二十岁,他终于凭着自己的本事考得一个进士。在官场,有无进士出身,本来就大不一样;如有外力,有了进士托身,别人也才好着力。先是父母双亡得辞官守孝,庞籍他们自己也还没得意,司马光只能蹭蹬。到庞籍做了枢密副使,第一个就推荐他应试,做了馆阁校勘、同知礼院;后来又升了殿中丞、集贤校理。他比安石只大两岁,做官的资历却早了###年;前后加起来,做京官的时间,也长得安石没法儿比。不是阴错阳差,司马光该不会只与安石平起平坐的。
虽有这些不同,安石与司马光处得倒还比较融洽。
安石自己是个爱读书的,这就先有了共同语言。他也同样推崇先王先圣之道,虽不至于那么琐碎,对人家讲究礼、乐,自然要举双手赞成。自己为人呢,也同样一丝不苟。有时,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大宋遗事 第三十回(4)
为了照顾安石,淑贤也曾为安石买过一个小妾。安石先不知道,到她单独过来侍候,才发现原来是个陌生女子,不禁吃了一惊,问道:“你是哪里来的,怎么跑到我家来了?”
小妾说:“贱妾是夫人买来侍候老爷的。”
安石更吃惊了,气道:“岂有此理!你叫什么名字?怎么被人卖了?”
一句话问得小妾泪水淋淋,哽咽道:“贱妾姓孙,名艳娥,原是有夫家的。”
“有这种事?有夫家,怎么又被卖了呢?”安石根本想不到会有这种事。
“奴婢的丈夫原是个军将,在船纲上运米。倒霉米船失事,家产赔尽了还不够,只好将奴婢也卖了凑数!”说到这里,艳娥早哭得肝肠寸断了。
安石皱着眉头问道:“你还愿意回去吗?”
艳娥没说话,越发哭得伤心了。
安石劝道:“你也不必伤心了,我这就送你回去。你去将夫人请来。”
艳娥迟疑着不肯走,安石只好又催了一遍:“去呵,请夫人过来,我有话交代她。”
艳娥不敢再赖着不动,只好赶到前面请来了淑贤。安石一见,就责备道:“夫人一向做事深明大义,怎么这次倒要悄悄陷我于大不义之中哪?”
安石夫妇从来相敬如宾,连大气都没出过,何曾说过这样的重话!淑贤不知何意,连耳根都羞红了。
安石见她这样,也懊悔自己话太重了,叹了口气,道:“唉,不知者不怪,艳娥你也不要太怪夫人!”跟着,就将事情原委说了一遍。
夫人红了眼睛,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到底没说出来。
安石知道她委屈,安慰她说:“好了,好了,夫人全都是为我好,这我能不知道吗?我先谢谢了,下不为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