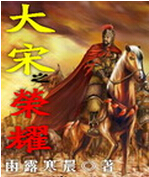大宋遗事-第3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既是这样一个捣不破、煮不烂的铜豆子,顺逆都有理由处之泰然,气壮山河,事事都只率意直行,不管不顾,想怎么来就怎么来,也就毫不奇怪了。先前,仁宗宠爱尚美人、杨美人,他写信刺得仁宗跳天;眼下他在国子监任直讲,目睹仁宗有些改革图新的意思,又按捺不住,要一吐为快了。
这回写的是四言颂诗:《庆历圣德诗》。
开宗明义,说是:皇帝龙兴,徐出闱闼。晨坐太极,昼开阊阖。躬揽英才,手锄奸孽。跟着,就借用皇帝的口吻,将丞相章得象、晏殊,参知政事贾昌朝,枢密院杜衍、范仲淹、韩琦、富弼,及谏官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等,一一大加褒奖。最后收束,又将皇上退奸进贤的圣德,拢共歌颂了一遍。
仁宗不过刚刚摆开了一点儿架势,章得象、晏殊、贾昌朝、杜衍都是朝中老人,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等则刚到新位置,一切都尚未开始,石介的颂诗,也写得太早点儿。而且,锋芒也太露了。
颂诗传到他的老师孙复那儿,孙复一读完就气急败坏,仰天叹道:“什么‘举擢俊良,扫除妖魃。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有这样写诗的吗?守道、守道,我怕你从此不得安宁了!”
范仲淹也特恼火,对韩琦骂道:“这鬼东西要干什么?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不过,暂时什么事都还没有。
那一面,欧阳修他们则真正在不遗余力地廓清战场,扩大战果。
已经罢去的吕夷简,还可能卷土重来,或死灰复燃,首先得将他敲死。
吕夷简授太尉致仕的时候,还有特别礼遇——朔、望及大朝会参朝,准他与中书、门下官员一起排班,还赐官给他的子弟。欧阳修上书皇上,请求罢免。理由自然也很充分:二十多年来,吕夷简隳毁纲纪,坏乱天下,享尽了荣华富贵,现在一拍屁股走了,将一个烂摊子丢给陛下。这样十恶不赦的人,早该严惩。皇上宽厚仁慈,优待保全,已是天高地厚的恩德了。是他有负于皇上,不是皇上有无负于他,根本无需再加恩!至于他的子弟,沾老子的光,早已恩典至极。如今边庭多事,在外面辛劳王事的有功之臣,都不能得到额外升赏,再让这些大奸大恶之家的愚呆子弟非分得赏,也太不公平了,请一定罢去无端恩典!
请罢旧恩之外,就是堵死他的干政之路了。
夷简既已致仕,就没有正常渠道说话了。他想了一个新招,不是经常有太医一类人给他看病送药吗,他有奏章,就通过御药局悄悄递上去。
这事也没逃过欧阳修的眼睛,他立马去找皇上:“陛下,听说已经致仕的吕丞相,常常通过御药局呈密折上来,有这事儿吗?”
皇上只问:“你听说什么了?”
“陛下,吕丞相当国二十多年,将国家搞得一塌糊涂,现在更神昏智耗,哪里还能再干预国家大事!他自己也早该闭门休养,不问世事。即便真有什么想法,原该光明正大地去政事堂、都堂和大臣们说,这么悄悄地递密折,是要惑乱圣听,绝不是什么好事儿!还有一层也不能不防。丞相自己风瘫昏聩,早不能握笔了。有折子,也一定是别人代劳的。他的子弟都呆傻不肖,难免有人作假,这就非同小可了!圣上固然圣明,不会上当,但外人不知道内情,光知道吕夷简还在干预国政,难免人心浮动。陛下,古人常说任贤勿贰,去邪勿疑,您可要坚定不移呵!请陛下从此杜绝密折,再不让一个已经致仕的无功之臣惑乱圣听。”
这话面面俱到,不管怎样,皇上心里也得过一遍。夷简既已致仕,声势体能也没了还手之力,差不多只能逆来顺受了。
旧邪既已敲定,该防着新邪了。
干旱的时候,有个翰林学士、礼部郎中、知制诰苏绅,向皇上奏了一本,说:“《洪范》五事,说:‘言之不从,是谓不NB836。厥咎僭,厥罚常。’又说:‘刑赏妄加,群阴不附,则阳气胜,故其罚常旸。’说的就是号令不专于上,权威下移于臣子,任他们哗众取宠,僭越陵上,必将导致阴阳失调,阴衰阳亢。久旱不雨,正是老天爷的一种惩罚警示。陛下不从为政的弊病上找根源,光祈祷,恐怕不成!”矛头所向,主要就是几个新任的谏官。他们什么都指责,苏绅一干人早已无法容忍。
。。
大宋遗事 第十一回(2)
苏绅这样的人,当然不能放过。
也是天遂人愿,不久,苏绅竟自己撞到枪口上来了,他推荐太常博士马端做监察御史。
这马端是有隐私的。而这隐私,恰好又落在欧阳修手里。
铜器可以铸铜钱、兵器,朝廷严令禁止民间收藏铜器。马端的老妈有个大铜佛,说什么也不愿交出来。马端怕受严惩,跑去告了官,官家来人没收了铜佛,又将他老妈拖去打了一顿板子。欧阳修将始末说完,就上纲上线道:“陛下,这做儿子的不能以礼防闲,坑他娘老子犯法;犯了法之后又不能容忍隐瞒,倒跑去首告,叫他亲娘老子吃板子。这样的人实在不齿于人类,连做个普通官员都不配,还能做言官,纠正朝中不法无礼的事吗?就是普天下没有一个好人,也不能用这种人!何况,正人君子还多得很呢!马端的事,人人都知道。苏绅什么人都不荐,偏偏举荐这种人,不是同流合污,明目张胆地欺君罔上吗?这样的事都敢干,什么事不敢干!请皇上收回成命,苏绅这样的人也不宜留在皇上身边,应当调他出去。”
皇上的亲娘惨遭不幸,他一辈子心里都有个大疙瘩,特重孝道,果然动了怒,马端官没升成,苏绅也放了外任。其实,这里有个忠孝两难的暗结。只是仁宗盛怒之下,想不到许多罢了。
范仲淹前面还有一个障碍,参知政事位子没空,有人。除了贾昌朝,就是知制诰、翰林学士、右谏议大夫王举正。举正也是个有来头的人,先父王化基,在太宗手里就做到参知政事了。他自己也是进士出身,写得一手好文章,办事也还有些原则。
陕西用兵,中书、枢密不是都管兵吗,朝廷让宰相吕夷简判枢密院。举正不同意,说:“管兵应当。用‘判’,名义太重,不能不避一避。”原来这大宋官制用字,有个不成文的习惯:级品相同管事,用“知”;低职位管高职位的事,用“权”,是代理、摄守的意思;高职位管低职位的事,才用“判”。宰相在政事堂办公,枢密使在都堂办公,一管文,一管武,号称“二府”,原是平级的。现在宰相因特殊需要参与管兵,用“判”字当然不合适。举正说的在理,到底改“判”为“兼”了。官场嘛,该讲究的,一个字也得“抠”!
拜举正为参知政事的前一天,他正在家里请客,中书的堂吏就先来报喜了:“恭喜大人!已经草麻,一两天之内您就要拜参知政事了!”
他不但不道谢,还绷着脸将这个堂吏教训了一顿:“嘿,你怎么能随便泄漏宫禁中的消息!”
那人连杯喜酒也没喝上,灰溜溜地走了。
第二天果然有诏书,拜他为参知政事。
他去宫里拜谢皇上,皇上问他:“爱卿知道为什么拜你为参知政事吗?”
举正只是磕头:“总是皇上不次之恩!”
这是答非所问。皇上也不计较,自己先回答了:“不为别的,就为你淡泊名利,从来不以一己之利干谒朝廷,所以才不次提拔。”
举正讷讷地说道:“其实、其实,也不尽然。”
那样子,连仁宗也忍不住笑了。
可是这个王举正,拗起来也很够瞧。
他有个连襟叫李徽之,现在工部任屯田员外郎,夫人是举正夫人的小妹。御史台要推荐李徽之做御史,也不知为什么,举正就是不同意。
李徽之请他吃饭化解,他不去;老丈人出来调解,没用;最后请出夫人,还是不成。李徽之的御史,硬是叫举正搅黄了!
胳膊怎么着也要往里拐呵,他倒好,却来了个家鬼害家人。这么干,这仇要不深如东海,可就怪了!李徽之告了一状,说王举正怕老婆,请罢了他的参知政事。逻辑是铁的,无可动摇:连家里的凶脸婆子都制服不了,还能治理一个国家吗?
既是连襟说的这话,不由人不信。还有一条,也让人无可怀疑,举正的丈人不是等闲之辈,乃是大名鼎鼎的陈尧佐。尧佐的父亲陈省华在太宗手下做过左谏议大夫,死后特赠太子少师。尧佐与哥哥尧叟、弟弟尧咨,都是进士出身。尧叟是真宗朝的宰相,尧咨也是做到节度使的人物。尧佐更是正儿八经的当朝宰相,调职以后,避亲的举正才做了参知政事。这样一个世倾朝野的岳父家,举正即便来头不小,也还是没法儿相比。从来女以家贵,妻子既有这么一个炙手可热的显赫家庭,举正要畏她三分,也就理所当然了。按一般道理,妻子应该向着小妹,举正越是怕老婆,越该帮连襟一把才对。可大家庭的事情,要比市井小民复杂得多,不能以常理来推论的。既然举正怕老婆,又死活要拉连襟下马,总该是她两姐妹不睦?这种事在官宦之家,正是屡见不鲜。
欧阳修、余靖、蔡襄正搜集炮弹,李徽之突然送货上门,哪有不用之理?当即连本上奏,请求罢免王举正,那理由自然更富有论辩色彩:《礼记?大学》说“欲治其国者,先治其家”;“家齐然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王举正视妻如虎,治家尚且不能,何以治国?任职以来,唯知怯懦缄默,一无所为,亟待罢去。罢去之后,谁任参知政事?笔锋一转,就转到了范仲淹身上:枢密副使范仲淹独具宰辅之才,岂可久在兵府?以范代王,最为合适。
仁宗不是从来就耳朵根软吗?既然多人连本上奏,王举正也确有怕老婆之嫌,不免他职也难了。好在王举正还有点儿自知之明,先自己上了一本辞职书。皇上顺水推舟,让他心满意足地去任外职了。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大宋遗事 第十一回(3)
可范仲淹的参知政事,却依然毫无动静。
自打进京任枢密副使,范仲淹、韩琦只在枢密院上班,朝参也只随班进退,从来没有什么特殊表现。
他们奏事,一般也只限于枢密院当管的事,绝不妄言其他。
有人上本请朝廷节减费用,朝廷下旨罢了陕西方面同州、解州等九个州军的公使钱一千八百贯。这公使钱,说白了就是官家的招待费,专供往来官员吃喝。这个钱没了,往来的官员就只能自己折腾酒饭了。范仲淹、韩琦当即上了一本,请仍旧拨放这笔款子。他们算了一笔账:一百贯只能养一个士兵,一千八百贯,不过养几十个士兵而已,而公费招待来往官员,可是《周礼?地官》早有明文记载的古礼。何况,这些州郡每年春后还要接待前来驻泊的军队,招待费也得在这一千八百贯里动支。为这么一点儿小钱,废了十几个州郡的待官、待将之礼,实在因小失大,断断不能。赶着其他地方也有人上书反对停拨公使钱,朝廷到底将诏书废了。
陕西营田,是要募兵开垦沿边肥沃的空地,增收节支,本来是件好事。可近边州县官员为了邀功请赏,愣是改弦易辙。一是,将逃亡人家废弃的瘦地,强迫分给人租种,让他们纳税纳捐;再就是,增加缘由佃农租种的官地的赋税。表面看去,营田收入增加了不少,实际都走了样子,不过敲诈佃农而已。范仲淹、韩琦上书,请求干脆彻底罢了陕西近里州县的营田,免得百姓无端增加负担。这也恩准了。
陕西方面的商业税收,远远无法满足边防费用的需要,先前已经有人请求卖官筹饷。范仲淹也上书请朝廷不妨网开一面,让有钱的人出钱赞助边防,朝廷给他们一顶纱帽,让他们过过官瘾。至于有人请求放松盐、茶等的专卖,减免商人的税收,他则坚决反对。国用已经不足,再放松专卖,减免商业税收,找谁要钱去?不取之于商贾,只能取之于农民。与其伤农,不如取之于商贾更为合理。
皇上那边呢,似乎也听之任之,没有一点单独召见、听取国是的意思。
两边都不着边儿,这事不是要黄吗?
欧阳修再也沉不住气了,借口西夏和议尚未定夺,赶着去见皇上。几句话说完,就直奔主题了:“陛下,其实,西夏的事问谁都多余,只有两个人心里像明镜似的。”
“谁?”皇上不由得问道。
“明摆着的,范仲淹、韩琦!他们两人在陕西边境多年,熟悉西夏事情,经历也多,胸襟见识又与众不同,肯定会有高见,别人看不到的。陛下一定单独召见垂询过了?”
皇上不吭声。
欧阳修吃惊道:“怎么,难道陛下至今没有单独召见他们?我记着,他们从陕西来京,也该有好几个月了?皇上不会不召见他们!”
“都几个月啦?除了朝参大囫囵见过,或者随两府官员一起议事谈谈,还真没单独召见过他们。”
欧阳修若有所思:“那就是了。我也纳闷,怎么皇上单独召见他们,我这个做谏官的连一点儿消息也不知道?这样下去,我还配做陛下的耳目吗?今天才算解开了疙瘩。”
说得皇帝也笑了:“谁叫你这么多心?没影子的事情,你到哪儿知道呢?”
欧阳修也笑了:“陛下,您今天还帮我解开了一个疙瘩。”
“哦,你疙瘩还真不少哪?说说看,又是什么疙瘩?”仁宗今天心情似乎不坏,也和欧阳修开起了玩笑。
“我一直在纳闷,范仲淹、韩琦进京天数不少,怎么说的都是一些寻常事体,没议过一件大事,更没有一件大的建树?照他们的见识与为官态度,不至于这样呵?今儿我才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朕倒糊涂起来了。”
“陛下圣明。您想呵,陛下既没有单独召见问对,让他们从从容容说出心中的见解,他们又不敢斗胆请求单独召见,就是满肚子经纶、见地,也没机会说出来呵!”
“你肯定他们有话要说?”
“他们在外面多年,又赤胆忠心,怎么会没有话说呢?陛下干吗不抽空在便殿约他们单独谈谈,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