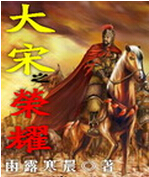大宋遗事-第14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大宋遗事 第七十三回(2)
凡被推荐的人,朝廷一律以举者多少决定是否入选。一旦入选,就无需再参加州县考试,直接进京参加进士或诸科考试就行了。关于考试,他倒也赞成取消诗赋及帖经、墨义,只考经义、时务策问。
保举法是首选。如果朝廷觉得不合适,那就该退而求其次了,就是办好学校,从学校取人。他对庆历以来州县学校有名无实,极为痛心,要求加强学校的建设管理,配备能真正为人师表的专职教授,对学生也要加强约束,实行严格的考试、升级等学籍管理制度。
神宗拿着司马光的奏折,问安石:“司马光的这道折子,爱卿觉着怎样?”
“关于保举,说得有些迂,也不尽符合实际。学校与考试的建议,倒都是好的。”安石如实回道。
“保举的问题,在哪儿呢?”神宗想更进一步听听意见。
“陛下,保举推荐制度,由来弊端丛生。东汉有一首民谣说:‘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将那汉代保举制度的弊病,说得再生动不过了。魏晋以后的九品中正制度,通过所谓推荐保举,更将天下官吏禄位,全让豪门贵族独占了,出身低寒的人,竟连一点儿上进的机会也没有!晋朝刘毅有一句话,说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最是贴切不过。隋唐科举,可以说是对保举推荐制度的最好纠正。虽然它自身也有许多值得改进之处,但那也只是改进的问题,不能完全取消。完全取消,取人也就没有相对公平的标准了。”
安石说的也是故实,却更实在,更具体,不由神宗不信:“爱卿说得在理。这科举制度,大框子确实不能动,举人还得由州县考来。”
司马光的折子,虽然保守,不合时宜,还不失为一种建设性的意见。苏轼的折子,差不多就完全是唱反调了。
折子一开头,他就说,得人之道,在于知人;而知人之法,则在于责实。假如皇上丞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责实之政,那么,就是小官小吏里头也有的是人才,更甭说通过学校、贡举了。果真这样,如今的一切制度条令,就绰绰有余,根本用不着去改。假如皇上丞相没有知人之才,朝廷也没有责实之政,那么,达官大臣里面常常都找不到合用的人才,还想从学校、贡举里去找有用的人吗?要是这样,即使完全恢复古代制度,也多半是白搭,没用的。
苏轼毕竟不同凡响,不愧是做文章的高手,一开头就亮出刀子,将以变求治的皇上与丞相置于无法自拔的险恶困境:无论你选择什么,都只有失败一条路。承认自己是知人之才,用不着变;承认自己不是知人之才,变了也没用。正也好,反也好,就是不能变。
接下来,他就逐条驳斥他所听到的各种求变论点了。
先说办学。
未说之前,先是一段排比。说是时有可否,物有废兴。一件东西,要是应时而安,就是暴君也没法儿将它废了;要是到它合该被淘汰,就是有圣人出面,也不能让它恢复生机。所以,法制从来是随着风俗的改变而改变的。这就像治理长江大河,顺着它的走向因势利导,就能事半功倍;硬与它对着来,只能坏事。学校的事,也是一样。假如三代圣人活在当今,他们要选贤养才,也会由道而行,根本用不着学校。这意思自然不难明了。那些堂堂正正、无可辩驳的大话,不过是一种故作气势的比喻,意在强调,学校的兴废,根本不是人工能够扶持的事情,只能听其自然;而由圣人看来,学校是根本用不着的。
说过道理,他又摆出事实。学校不是没办过,庆历年间不是办过很多学校吗?当时以为太平可以转瞬而至,如今怎么样?不过徒有空名而已!皇上要是真想办学,靠办学求治,必然要大兴土木,置官立师;而那些不愿接受教育的人,又必然会受到排斥,甚至驱逐。结果,不但会劳民伤财,还会引起纷乱,徒然叫老百姓受苦受累,何必呢?要是不想大动干戈,与庆历又没什么两样了。
说来说去,结论是什么呢?就是维持现状,一切不动。他说得很明白:“今之学校,只可因循旧制,使先王之旧物不废于吾世,足矣!”
说过学校,他就说到贡举之法了。总的结论是,目下的方式,已经实施一百年了,治乱盛衰,根本与它没有什么干系,同样用不着改。凡认为应当改的几种主张,其实全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就说只重德行,而忽略文章,就根本站不住脚。德行固然重要,但要立为科名取人,就只能叫天下人为着功名利禄都去作假了。上面以孝取人,勇敢不怕死的就会割股孝亲,胆小怕死的则要结庐墓旁;上面以廉取人,天下又都争着乘鄙车骑瘦马、穿恶衣吃恶食了。只要能叫上面中意,可以博取功名,就没有不能干的事情。这不是败坏德行吗?如何能做?
他最不满的,是专取策论而罢去诗赋,说得也最多。
首先,从文章而言,固然可以说策论有用,诗赋没用,但从治政的实际需要来看,策论实际上与诗赋一样,都没有用处。明知没用,为什么一直又用它们来考选人才呢?因为考试取人,不过如此,实在再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就是尧舜时代,也不免进人以言,试人以功。就是先看看他是不是善于辞令,再看他是不是言行一致,而不只是嘴上功夫。这是有意矮化策论,将它与诗赋扯平,各打二十大板。既然两个都一样,要抬一个灭一个,就没有道理了。
大宋遗事 第七十三回(3)
其次,靠策论定人,也很难立得住脚。说到文辞华靡,本朝怕再没有人能超过杨亿杨大年的了。可他的清亮耿直,也一样叫人钦敬。怎么能因为他文辞华靡,就不承认他品格高尚呢?同样,通经博古的,本朝莫过于孙复、石介了,但他们却迂阔怪诞、矫情自傲,很难让他们从政。且不说他们,再远点儿,自唐代至今,诗赋好而又不失为名臣的,数不胜数,他们什么时候负过天下?既然如此,为什么偏偏要将诗赋给废了呢?
策论就那么高明?不过是东拼西凑,临时剽窃,糊弄考官罢了,哪里有什么真才实学!它的弊病,较之诗赋,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硬将它抬那么高,也实在站不住脚。
连帖经、墨义,他也主张不必动它。不管怎么考试,都与理政没有多大关系,又何必厚此薄彼,而不网开一面呢?
能将反调唱得理直气壮,洋洋洒洒,不也是一种功夫吗?苏轼的文章就有那功夫,没理也能说出三分理,让你读来爱不释手,从容入彀中。何况,里面也不全是胡扯,甚至还夹有他自己的经历体会。他一考进士,二考制科,说是道非,讲古论今,纷纷不已,不过也是为了功名,在那里东拼西凑,鼓唇饶舌而已,哪有什么真学问、真见地!这一点,虽然直到老去才有了清醒的认识,可那时,潜意识里的自我反省,也不能说一点儿影子也没有!
读完苏轼的折子,神宗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恍然有所领悟。至于究竟领悟了什么,他也没去想,朦朦胧胧的。再读一遍,才发现苏轼原来是个反对派,兴学与贡举改革,他竟一样都不赞成,只说什么都别动才好!原来这样!这怎么行?他能将无理说成有理,而且还叫你轻易就信了,不能不说是他的能耐!而且,有些话也不都错。像诗赋不全坏,策论不全好,就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他的文名,是早就知道的。由这篇折子看来,果然不为虚传。应当见他一见。神宗当时就要内侍,传苏轼见驾。
“陛下,您为什么要召见臣下?”见礼之后,子瞻突然反客为主,问起皇上来。
神宗不禁吃了一惊。看着一团和气的样儿,竟还有些锋芒?先解释一下吧:“您的折子,朕已经看了。说的与别人不一样,也不无道理,所以想请您来谈谈。”
“这么说,陛下就错了!”子瞻又劈头来了一句。
神宗一头雾水:“朕怎么错了?”
“做臣子的,无不都以皇上召见为荣。如今皇上并不真正了解微臣,只是凭着一个折子就召见我,这不是以言进人吗?传扬出去,恐怕人人都要找这空子钻了!”子瞻教训道。
初次见面,就给朕一个下马威?文人恃才傲物,矫情作态,就有这样的!刚刚不还说尧舜也要进人以言、试人以功吗?我因为言论召见您,有什么错呢?神宗一笑,也不去计较,只转口道:“好,朕喜欢您这样心直口快。身为馆职官员,都应当时时替朕想着治乱安危、成败得失,而且,还要想到就说,毫不隐瞒。”
“谢谢陛下鼓励。”苏轼也开始谦虚起来。
“除了贡举,对于朝政,您还有什么意见,欢迎您也直言不讳。”神宗说。召见的目的,本来就是想多听听他的意见。
“没有。微臣不敢乱言。”苏轼推辞说。
“不敢说,不等于没的说。不要有顾虑嘛!”神宗听出他话里有话,鼓励说,“不是说了吗?治乱安危,成败得失,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用不着顾忌。尤其是当前的政治,有什么不妥当的,更要说!就是朕本人有什么不对,也都可以说,没有必要忌讳。”
既这么说,苏轼就不客气了:“陛下有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怕就怕陛下求治太急,进人太快,听言太广。孔圣人说:‘欲速,则不达。’陛下要时时警惕才好。”
“能具体说说吗?”神宗问。
“陛下,这只是臣的一点儿直觉。要说,也只能说出一点儿印象。”
苏轼垫了这么一句,就滔滔不绝地说起他的那么“一点儿印象”来了:无非是刚任命的那些官员的是是非非——从王安石说到吕惠卿、程颢等等,只对章子厚多少包涵了一点。
神宗硬着头皮听了几句,到底打断了他:“爱卿说的三件事,朕已记在心里,会好好考虑的。”
皇上既这么说,苏轼只好不再说了,又谈了几句别的,也就告退了。
神宗将苏轼的折子又转给安石看了,问他说:“爱卿看着苏轼的折子怎么样?”
“苏轼很会做文章,无理也能辩出三分理。”安石笑着说,“只是一较之事实,就很难说服人了。如今人才缺乏,思想不一,异论纷呈,不为别的,只为道德不能统一。要统一道德,只有办好学校。学校不是一时两时能办得好的,所以先得改革贡举。苏轼说,进士一科,虽然诗赋、策论什么都考,也还是得了许多人才,倒也不能算错。可那是因为除了进士,读书的没有别的当官路子好走,都一窝蜂拥到这儿来了。既都拥来了,还能没有几个有用之材?这并不能说明进士制度就完美无缺了,动也不必动。人一生正当少壮的时候,不去讲究天下正理,学些切实有用的东西,只是关起门来平上去入,不是诗就是赋,能好吗?凭着这一身平上去入的本事,虽侥幸得了个一官半职,办起事情来却一窍不通,行吗?所以,说到败坏人才,再没有比这更害人的了。不改,怎么成?”
大宋遗事 第七十三回(4)
安石说到最后,多少有些调侃,神宗也笑了:“朕倒也这么想。不过,偏尽管偏,苏轼这人还是能够想事的,文章也是真好,很雄辩,不由人不入彀。”突然又想起那天他们还谈到用兵,就又补充说,“苏轼对朕说:‘用兵之道,先动的为客,后动的为主。为主的常胜为客的,为客的总是吃败仗。治理天下,也是这么个道理。皇上也不要先动,只能以静待动,应之于后,才能无往而不胜。’爱卿看着,他这话是不是有道理?”
“苏轼这话,倒也不无道理,就看怎么看。天下之道,有经有变。他说的是道之经,而不是道之变。要想畅通无阻,总要通经达变才成。圣人治理天下,感而后应,合的正是道之经。就这一点而论,苏轼说得在理。可天下的事情,变化无常,不能拘泥固执,只用一种方式,必须随机应变才成。也拿用兵说,哪里都是后出兵才胜、先出击就一定失败?不过根据时势,权宜而行罢了!”安石很耐心地解释说。
“还是爱卿解得透彻。”神宗赞同说。跟着,又话锋一转,征询安石,“爱卿说这苏轼,给他件把小事试试怎样?”
“用人先试之以事,是应该的。”安石同意。
但究竟让苏轼做什么事,神宗并没有设想,这事也就搁下了。
过了两天,中书奏事的时候,神宗又想起这档子事,便问曾公亮:“苏轼奏对明敏,是不是弄件事让他试试?”
曾公亮想了想,苏轼不在官告院吗,也算是有职事的,还试什么?陛下的意思,显然是要将他升职?可目下哪儿人都满了,并没有什么空位子,只好实话实说:“陛下,目下朝廷没有空缺,京师暂时没什么事情好试。”
“让他到中书去修条例,可以吗?”神宗提出了设想。
修中书条例,是执掌中书文字的文秘官员,事关中书政事及政策条例的制订、发布等等,官轻位重。就文字能力而言,苏轼当然再合适不过。可他处处显山露水,爱独树一帜,与中书似乎很难配合,这位子能适合他吗?勉强用了,他自己处处别扭不说,没准也会误了中书的大事!
“就能力而言,苏轼去中书应该没有问题,可也有不利的一面。他个性强,又好说好动,未必能与中书步调一致。怕就怕经常与中书产生矛盾,那就要误事了。”公亮说出了心中的顾虑。
“爱卿怎么看?”神宗转过来又问安石。
“丞相说得有理。中书条例的事,烦琐得很,又牵动大局,责任重大,从来大官小官谁都不大愿意做。目下的事情,更难做了。我私下里瞅着苏轼,也觉着他不是个勇于承担责任、肯违众济事的人,而且,似乎也好与人不同。要是在中书标新立异起来,怎么办?那是非坏事不可的。况且,用人得再三考察,确实可用,才好使用。陛下对苏轼,也只是听到他的一些意见,这意见还不尽正确,未必可用。到中书,是不是暂时缓一缓,让他试试别的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