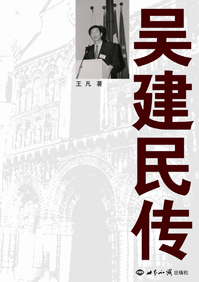吴建民传-第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看不见的纽带连接着。吴建民的感受也是:“中国人吃匈牙利餐还是比较容易习惯的,我当时吃着觉得蛮好。”布达佩斯的饭菜虽然好吃,可要做好在布达佩斯的工作却相当的艰辛,因为中国同苏联关系趋于恶化,中国人在东欧已经感觉有些冷峻肃杀的氛围。更何况吴建民长年所习是外国语,而并没有受过外交专业的训练。虽说他曾有幸几度置身外交场合,但从熟悉外国语到适应外交工作,这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跨度。
几十年之后,吴建民受命出任外交学院院长,回溯起当年情景,他才意识到自己是在懵懵懂懂中一步跨入外交领域的,从一个学生到一个合格的外交工作者,要走过怎样漫长的摸索领悟的里程。因此,对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说外交部新来的青年人对外交工作不得其门而入,他体会颇深,上任不久就在学院开设了外交案例的教程,并亲自授课。
以吴建民的勤奋,如果在刚踏入外交领域的时候,能有本入门的书读一读,有几则外交案例借鉴,他会入道更快一些。但他们这一代外交工作者,命中注定要和他们的前一辈外交家一样,要靠自己的观察、摸索,自己的琢磨、总结,积累经验,卓然自立于外交舞台。
有人曾这样描述过新中国的前三代外交家:第一代是将军;第二代是省委书记;第三代是翻译。他们都没有受过系统的外交专业熏陶,又都赶上了“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时代,因此他们也只能在外交实践中认识外交,驾驭外交,像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的那样:“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
虽说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是由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共青团主导的世界青年组织。但在吴建民到来之际,联盟内一团和气的时光已如逝川,中苏之间的政治分野已日趋明显,这里就快要成为中苏口舌激烈论争的风口浪尖了。“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是吴建民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而实际上也是将人置于一个速成的环境,在这个环境里很艰辛、很费神,很疲惫,但也会积蓄起在其他环境中不可能获取的宝贵财富。
在1960 年的4 月,中共中央组织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的列宁的道路前进》、《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三篇文章,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当前时代、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社会主义革命、帝国主义本性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的观点,文章虽未直斥赫鲁晓夫和苏共领导人是“修正主义者”,但明眼人很清楚文章的由来和矛头所指。
到了6 月,苏共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发动突然袭击,对中国共产党大肆攻讦,将分歧公开化。7月,苏联政府又单方面决定立即召回在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废除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各项协议。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对当时处于经济困难中的中国无疑是雪上加霜,因而严重损害了中苏两党和两国关系。
11 月,在有81 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参加的莫斯科会议上,赫鲁晓夫在众人瞩目的大会发言中借题发挥,向中国共产党发起了新一轮攻击。
邓小平在随后的发言中对赫的言论一一反驳,中苏分歧被更清晰地展现于世界共产党和工人组织面前。邓小平形容当时的情势时说:他们丢辣椒,我们也得丢辣椒。在尔后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中共和苏共互丢辣椒的场面更经常化了。
在党的多边会议上出现的情形很快也就感染到团的多边会议上,当时在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内最主要的争端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工作重点选择上的分歧。具体表现为怎样对待当时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怎样评价其地位与作用。苏共当时的工作重点是资本主义国家内非共产党的、宗教性的青年组织,中间性的社会团体,包括北欧的一些禁酒组织;而中国方面则根据自己的经验加之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提出应着重通过青年组织来支持、推动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二是在工作方式上的分歧。即中国不赞成苏共及苏联共青团在处理国家间关系及多边活动中的大国沙文主义作风。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外交的独特节奏(2)
20 世纪50 年代后期,苏联共青团越来越明显地将世界青运的工作中心放在裁军、议会斗争上,循着这一逻辑轨迹,在对待亚、非、拉地区民族解放问题上,采取了极力控制、尽力不要“惹祸”的态度。中国则强烈地提出,对帝国主义不能软弱、退让,对民族解放运动更旗帜鲜明地支持,因为青年是反对殖民主义的主力军、保卫和平的主力军。这种争执,也随着中、苏两党的争论逐步扩大化。
1963 年9 月,中苏两党的公开论战开启,从一评《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开始,此后每一篇评论都会及时发送到常驻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的中国代表团。中国将苏联的国际政策归纳为“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并言辞犀利地予以批判,把武装斗争提到很高很高的地位,吴建民印象中当时最频繁出现的一句话,就是“武装斗争是民族解放的唯一道路”。吴建民他们因此又多了一项工作,就是向各国常驻联盟总部的代表们散发这类小册子,并为维护这一观点与苏联等国家的代表在会上会下角力。
平心而论,持续了十几年的论战,中国共产党也有失当的一面,邓小平在数十年后总结说:双方都有值得检讨的地方。可是在当年,吴建民他们是非常认真地看有关的小册子、听有关的广播的。
作为翻译的吴建民,是最不能对这些言辞掉以轻心的人,他必须琢磨如何把这些论述用法语、英语等外国语言准确地表达出来,因为在会议上、交谈中,中国代表时常要援引这些言论,阐述中国的观点,与持不同观点的他国代表进行争辩。在这些场合,中文说错了,可以在翻译时矫正,但翻译后的言语出错,那就是大问题了。在反反复复阅读和听广播的过程中,吴建民曾一次次地被其中的论述鼓动得热血沸腾,并为寻找最贴切到位的对应词汇而殚精竭智。
那时,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会议也多,重要会议往往要通过一个大会报告。联盟内的主要争端,自然会反映到这样的报告表述上面。在中共发表的“###”中,法国共产党领导人多列士和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等,都被点名批评,来自意大利共青团和法国共青团的民主青年联盟主席、总书记,调子自然和受到中国批评的苏联的主张很相近,大会报告的主旋律,往往受到他们调子的影响。每逢出现这样的情况,中国方面就要通过争议或其他方式,以使己方的观念反映到报告中。
吴建民还清楚地记得有一年,联盟大会报告初稿把中国特别强调的武装斗争内容拿掉了。中国不能接受这样一份报告,随即酝酿对报告进行修改。为了使修改报告能够通过,必须做有关国家代表的工作,请他们出面要求修改,并提出修改报告稿。
为此,吴建民先将法文的报告初稿翻译成中文,供代表研究修改,随后又在晤谈中担任翻译工作。当新的中文报告草稿拟就,吴建民又连夜翻译成法文,打印出来后,给印度尼西亚代表马尔多诺,由他提交给联盟大会。其实与会者都猜得出来,马尔多诺的背后是中国人。
1965 年暮春时节,吴建民和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的各国代表,到刚果(布拉柴维尔)参加一个反对殖民主义统治的会议。那是他第一次踏上非洲的土地,非洲人民对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代表很热情,许多非洲青年登上代表们乘坐的车,用唱歌表达他们的欢迎之情。
当时青年们唱的那些歌曲,充满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统治,争取独立解放的渴望与豪情,比如“昨天我们还受压迫,今天我们自由了”。因为歌是用法语唱的,吴建民都能听懂。看着唱歌的人们的激情和喜悦,吴建民也心潮澎湃,感到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潮流势不可挡。
吴建民和代表一起积极主动地与非洲青年们接触,与他们谈论非洲的形势,探讨非洲国家的独立解放运动中的问题,并把参加会议的代表请到中国大使馆,和中国大使谈论非洲问题,向他们介绍中国武装斗争的经验。
在纷争日益激烈的那些年,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成了中国和苏联较量的又一前沿,中国驻联盟的代表和翻译的工作生活因之也变得异常紧张而辛苦。当时的会议比较多,由于意见不一致,常常会对某个问题争执很久,不乏一天的会拖上十几个小时的情况。。 最好的txt下载网
外交的独特节奏(3)
翻译要对代表的发言做同声翻译,就一两个翻译盯着,没有人替换。他要把中国代表的发言,翻译成法语;把其他各国代表的发言,转述给中国代表。会上争辩,会下还要听反应,摸情况,与关系比较好的国家的代表交换意见,准备可能持续进行的争辩。这种高频度的语言使用,思辩性极强的论战,使吴建民的外语水平提高得很快,他一度有些得意:“我翻译的速度比我们的对手要快。”
但这样的会议一天开下来,往往累得疲惫不堪,而且连续几天,都没多少休息时间。苏联的代表有时为了使体现他们意旨的重要议案免受中国方面的批评阻滞,往往拖到夜深人静、大多代表比较困倦的时候才端出来,以期趁人们精力不够集中而匆忙表决获得通过。
中国方面对苏联人的这一做法非常警惕,时时提防苏联人搞小动作,不让中国难以接受的议案获得通过。所以即便是中国代表不准备到席、也没安排中国翻译轮班的夜间会议,中国翻译也必须到会场盯着,而且越是在这样的场合,神经绷得越紧,不敢忽略任何一个细节,否则就可能出大的政治问题。这就是外交的独特节奏,时间有时是那样的悬于分秒;有时又是那样的漫无边崖,一些策略和玄机,就藏在外交节奏的控制里面。这一点,在后来吴建民到联合国时,又有了更深的感受。
每遇这样的会议,还没有领略其中玄机和奥妙的吴建民,最分明的感觉就是特别的累。在列宁格勒的一次会议期间,吴建民吃罢晚餐就睁不开眼了。一阵电话铃响,催促他上会场,他嘴上答应着好好,可放下电话就又睡过去了。1964 年,吴建民到布加勒斯特开了几天会,又是通宵达旦。会议结束有一天休息,他蒙头大睡了24 小时,连饭也没起来吃。
吴建民对朱良的报告内容和表述留意起来/出现被围攻被动局面,吴建民感觉很窝火/钱里仁对吴建民说:“你的嗓门儿不能超过我的嗓门儿!”/吴建民在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工作了三年多,跨了四个年头,先后为三任代表做翻译。第一个是朱良,继而是梁畊,再后来是贾学谦。吴建民和朱良、梁畊接触的时间比较长,对他们评价颇高。他还清楚地记得朱良在每次交锋时的沉着神态。朱良讲话不多,就那么几句话,但很得体。吴建民为他翻译也感觉很顺畅、轻松、利落。看得出来,各国代表对朱良都比较尊重。
那时驻外的代表参加每次会议,都要给国内写报告。朱良报告写好后,誊抄的任务都由吴建民完成。在誊抄过程中,吴建民发现,朱良笔下记述的事情,自己也经历了,可朱良写出来就很有内容,归纳很有条理。报告分析形势,分析苏联代表的动向,分析亚、非、拉代表的心态,很有深度。
事情就是这样,一样的路走过来,有的人收获丰盈很快跃上新的高度;有的人却总在一个平面踯躅蹭蹬。差别就在于有的人观察敏锐,洞悉透彻,并习惯于归纳总结。吴建民对朱良的报告内容和表述留意起来,报告的关注点在哪里,分析推演的逻辑等等,从这中间他学到了不少东西。
因为誊抄大都是在晚上,有时很晚了,虽然吴建民很用心,但在誊抄中也难免会有出错的时候。朱良看到这种情况,一般不郑重其事地批评,而是好像漫不经心地说:“哟,是不是抄得太晚了?”
朱良的这种批评很有艺术性,很委婉,既让人明白以后要注意,办事再严谨些,但又能让人容易接受,精神上也不会背很重的负担。这更赢得吴建民由衷的佩服敬重,觉得遇到这样的领导很幸运。也是在朱良在任期间,吴建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的介绍人就是朱良和朱善卿。
而吴建民对梁畊的相知则经历了一些曲折。梁畊来的时候,吴建民已经当了一年多的翻译,就对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的了解而言,他比梁畊更熟悉情况,更清楚一些议题的来龙去脉,甚至经历过更多的复杂场面。因此在新领导面前,他有时候讲话就流露出过分自信,甚至在内心轻率地下评断。
此时中苏的纷争升级,在会议中的争执更频繁和激烈。由于梁畊对一些争议事务的前因不太知晓或了解尚不全面,发言时曾让人家抓住把柄,被围攻得很猛,出现过比较被动的局面。遇到这种情况,初来乍到的梁畊也比较紧张,吴建民做翻译就更感觉到压力。事后内心仍会感到不太舒坦,觉得特别窝囊。
外交的独特节奏(4)
1963年在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工作期间,与哥伦比亚代表在布达佩斯。
还有一次,梁畊见一位外国代表,见完之后,梁畊送了出去。吴建民记得朱良过去送外国来客,总是到一个地方就停下来,所以在走到那个位置时,他对梁畊说:送到这儿就可以了。梁畊当时没有理会,等送客人回来,对吴建民发起了脾气,他拍着桌子说:“是你见外宾还是我见外宾?这些事是我决定还是你决定?”
梁畊是四川人,他这种拍桌子的方式,与上海人朱良的和风细雨有着分明的差异,不那么容易承受。再想到在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的会议上曾经出现的被动局面,吴建民一度认为梁畊来了以后,情况不如朱良在的时候,对梁畊的能力有几分猜疑。直到又经过一段时间后,吴建民才逐渐对梁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