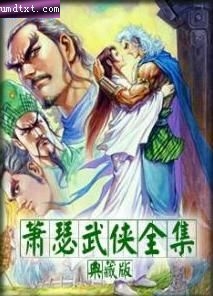拿破仑-第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同,这是他主要思考的问题。学习历史他得以知道社会的各种形成。但他不希望停留在理论上。他讲求实际,追根究底,考察入微。军队、航海、外交、财政、贸易,有确凿的事实根据,有具体的日期和数字,他力求从整个资料中掌握根本。他就这样查阅资料,做笔记,写摘要,他的那些笔记本涉及大量名著:孟德斯鸠、罗兰、马布利、米拉波、马蒙帖尔、比隆。他研究*人、土耳其人和波斯、英国、瑞士的历史。他费了很长时间研究拉克鲁瓦的地理,从那里才知道世界上有圣赫勒拿岛的存在:“圣赫勒拿,大西洋小岛,英国殖民地……”他记下这几个字后,也许因为疏忽,也许受到打扰,这一页留下了空白……
他对文学的兴趣也很浓。他反复阅读高乃依、拉辛、伏尔泰的剧本。小说也没少看:《德·科曼热伯爵》、《雷斯蒂夫的同代女人》,读来颇有兴味;《保罗与维吉妮》、《印第安茅屋》,他读得入了迷。
他读的东西太多了,满肚子学问,情不自禁地在同学面前高谈阔论,有时候甚至达到令人厌烦的程度。他拉开话匣子,不断加重南方口音,兴高采烈。他有时候因咬文嚼字而不知所云,但他的思想绝大部分时间是果断的,言辞是强有力的,跟他原来的性格是一致的。德·马齐斯逗他:
“什么?难道您的血肉与别人不同?一种乱七八糟的科学会导致什么?对1000年以前发生的事情我该做什么呢?”
后来,德·马齐斯对一个阿德莱德姑娘献殷勤,他打算娶她为妻。波拿巴数落他软弱。他最瞧不起跟女人这样消磨时间。
“老是大话空话!”拿破仑使劲喊了起来,“不要限制这高傲的灵魂,不用限制这颗赤诚的心,这颗心过去是那样信任的一颗心,原来是如此狭窄。你,倒在一个女人的脚下!不如把你身边的混蛋一个个打倒吧!”
德·马齐斯哈哈大笑。拿破仑耸了耸肩,重又登楼回到自己的房间。很可能就在这一天他对爱情留下了这段笔记:“我认为它有害于社会,有害于人的个人幸福,总而言之,我认为,爱情弊多利少,倘若我们和世界能够摆脱爱情的纠缠,这就是上帝的大恩大德了。”但他后来说的并不都是这样。
他经常下笔千言,一泻千里,但却是粗制滥造,以至于自己都认不出自己乱涂乱画的东西。他主要是写些有关炮兵的观测和报告。他向严厉而又和蔼的泰伊校长呈上一份关于炮弹射程的备忘录,他那严密的逻辑性和计算的巧妙令将军喜出望外。但他又很快掉过头来写他个人的论文。他把《菲利皮尼》改头换面,苦心经营他那部关于科西嘉的著作,他想把它献给内凯尔。他将它送交给他在布里埃纳的老师迪皮伊神父修改,因为他曾建议拿破仑缓和对法国的口气。
为了消遣,他草就一些小短篇:《埃塞克斯伯爵》、《蒙面预言家》,老实说,文笔平庸,枯燥无味,浮华的词句也难以掩盖和补救,但其中也不乏一两行像金子般闪光的言简意赅的优美句子。
“我除了用功之外别无对策,”1789年7月他这样写道,“我八天才换一次衣服,自从生病以来,我睡眠极少,这是令人难以相信的,我10点钟睡觉,4点钟就爬起来。我每天只吃一顿饭。”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荒野雄狮(10)
在他的笔记本上,他曾拟制这样的计划:“草拟论王权一文。确定欧洲12个王朝中国王享受篡夺政权的特殊性。众多国王中,很少有例外不应该被推翻的……”
他声称支持人民起义以反抗专制君主。他想,真正的光荣根本不是通过征服获取的,而是通过对祖国的爱和对人民的仁慈得到的。他对流弊、等级、特权深恶痛绝,相信善良的本性,相信法的至高无上,他声明反对狂热和盲从。他与一切宗教信仰背道而驰。当听到一条使他痛苦或令他气愤的消息时,他仍然会情不自禁地像她母亲那样,以意大利的习惯画一个“十”字,并口中念念有词:“耶稣!”他一直没有改变这种习惯。除了相信一个模糊而散乱的上帝外,他什么也不迷信。他以理性的名义与宗教仪式分庭抗礼,强烈抨击神父左右人们灵魂的权力。
“确有这样的情况,基督教,甚至是经过改革的基督教,”他写道,“摧毁了国家的统一。”在他心目中国家统治一切。
这就是大革命的星星之火刚开始闪烁光辉时期拿破仑的真实思想。这次大革命的爆发,究其根源,一大部分则都是亲爱的卢梭阐述的,一旦拿破仑看到大革命可能产生的后果,即推翻一个他判决为陈腐的政治组织,诞生一种崭新的秩序,这位20岁的军官怎么会不把大革命当作曙光来欢迎呢?大革命以其令人陶醉的思想意识,会给他的故乡带来自由的希望,为他自己带来大显身手的机遇。
“可以提高我的地位,平等思想使我迷恋。”后来他承认这一点。1789年4月,他奉命同其他炮手一起到瑟尔去恢复秩序,那里带头闹事的人屠杀了两名小麦商人。他第一次与闹事的人接触以平息骚乱。此时此刻,他内心那种专制与纪律的倾向急剧加强。他在那里并不耀武扬威,行为粗暴。他把人群驱散,高喊道:“是好人统统回家去,我只对坏蛋开火!”大街小巷一下子空无一人。
平乱后他回到了奥松,只见全城受巴黎接二连三的事件所震撼。三级会议、第三等级奋起反抗君主政体、攻占巴士底狱,搅得人心激荡。7月19日,下等人造反,侵占并洗劫贩卖人口和入市税办公室。人们用枪威胁他们,才勉强控制住局势。但拉费尔炮兵团早已同情叛乱群众。8月16日,该团造反,强迫上校交出不法扣发的津贴。炮手们也分到了好处,从小酒馆回来,对他们的军官骂不绝口。
拿破仑怒气冲冲。然而,在他内心,关心的并不是奥松,而是科西嘉。科西嘉形势如何?他的同胞们会不会从革命事件中渔利?对波拿巴家族,对拿破仑自己,这可是千载难逢的进取良机!
他写信给保利,保利是他的楷模,即将趁法国大乱之机以胜利者自居凯旋科西嘉岛。他在信中对老首领顶礼膜拜,希望收在他麾下当中尉:
“将军,我生于祖国沦亡之时。3万法国人涌向我们的海岸,把自由的宝座淹没在血浪之中,这就是我降生世界后第一个扑向我的眼睛的可憎景象……我们屈服的代价就是沦为奴隶,我们的同胞们在士兵、法官和税官三重重压下生活,受尽冷眼,苦不堪言……”
保利没有回信。这种不理睬令拿破仑不安,他很快不再对回信抱有希望,他必须回科西嘉去。在法国,一切都松动了。他趁机请了一个假,一获得准假,便装了一箱子书,出发下马赛。他在瓦朗斯稍事停留以访亲问友。德·圣吕夫教士同拿破仑谈到大革命时,开玩笑说:
“波拿巴先生,照这样下去,每个人都可以当国王,要是轮到您当国王,您就和基督教和解吧,您会从中感到称心如意。”
年轻人笑着回答说,如果他当了国王,他一定要立红衣主教。他到了科西嘉,发现什么也没有改变。人们对大革命发生的事件所知甚少,这些事件对岛上的行政管理还未曾发生影响。不过,人们的思想已经活跃沸腾起来,人们热情地争论着问题。
拿破仑一眼就看到自己应当扮演什么角色。他对命运寄予无限的希望,何不在科西嘉立一个行省督,凭借氏族集团来统治他的土地?他梦寐以求的前景此时此刻正清楚地展开在眼前。
他走访朋友,在街头巷尾与他们侃侃而谈。由于他的倡议,同胞们一个个拿起三色标志,开了一个俱乐部。他的两个兄弟——约瑟夫和吕西安成了他的左右手。拿破仑以家长自居,后来也始终如此,约瑟夫虽然当了律师,却只为一个案件辩护过。他受过良好的教育,生性懒散,但又审慎固执,虚荣心很强。他肯定拿破仑当前是先为自己打算的。他的长子权同他的功德一样将首先受益,会给他带来最美好的地位。他承揽民事案件,很少是出于兴趣,较多地考虑利益。他的建议往往适可而止。
吕西安还是翩翩少年,却像一团活跃的火苗。他在神学院聪明好学,成绩不错。从神学院回来,他喜欢想入非非,比拿破仑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血液里有政治在活动。
巴斯提亚当时是科西嘉的首府,首先要在那里开展斗争。拿破仑赶到巴斯提亚,到处煽风点火。造反的烈火像丛林里无意中点着的星星之火,在夏风的鼓吹下逐渐地燎原开来了。
此时此刻,巴黎才终于关心起这个远方的岛屿。国民议会根据米拉博的建议,将科西嘉整个纳入“法兰西帝国”的怀抱。它把那些曾为科西嘉的自由战斗过的流亡者召回岛来。
城乡张灯结彩,热烈欢呼法兰西,唱起感恩赞美的颂歌。拿破仑也被卷进这浪潮里。昨天他只感到自己是科西嘉人,而今天他认识到是法国人了。
“法国为我们敞开了她的怀抱,”他欢呼道,“从此我们有了共同的利害、共同的忧患。大海再也不能把我们分开!”正是他在波拿巴家门前挂了一面长条旗子,上面写着:“民族万岁!保利万岁!米拉博万岁!”
他以普通战士的身份,在阿雅克修的国民自卫军服役。大选之前,他也出谋献策,频频活动。尽管约瑟夫按法律规定还太年轻,但他却鼓动哥哥参加大选,约瑟夫已被提名为候选人。全科西嘉的代表都到奥雷扎*。为了去奥雷扎,也是为了去会见保利。保利在国民议会上被当作英雄欢迎。
保利宣布要回科西嘉岛。拿破仑便以生病为借口又请了一次假。不过,他的身体的确很瘦弱,他同他的兄弟们一起在萨利纳散步时又得了风寒,发了烧。但有一股精神力量在支持着他。他骑马陪约瑟夫到奥雷扎,让他坐在前面,好让他说话。
保利终于来到巴斯提亚。他那高大的身躯、那男子汉的面孔、蓝色的眼睛、苍白的头发激起长时间的欢呼。全科西嘉岛重新掌握在他手里。他大权在握,军权、民权、一切权力。拿破仑曾对他远而敬之,拿破仑向保利表示阿雅克修的祝愿时,正好是在当年科西嘉大败的纽沃桥头与他相见的。但论辈分,巴博(族长)是主人。夏尔·波拿巴原来是保利的忠诚战士,他的孩子们就应当站在保利的两边。保利对拿破仑的接待是冷淡的。这个投敌变节分子的儿子,又是法国养大的,现在却企图来投靠他,他不由产生一种强烈的不信任感,他感到拿破仑既粗鲁又危险。然而,为了管住他,便吹捧了他一番:“咳,拿破仑,你一点也没有现代派头嘛,你完全属于普鲁塔克笔下的人物。”
回到阿雅克修,尽管假期已到,但拿破仑仍迟迟不归队。他在阿雅克修“环球”俱乐部宣读了一封信,对保利的对手、科西嘉议员比塔非奥科展开了口诛笔伐。波拿巴中尉的檄文受到了欢迎,俱乐部对这封信给予极大的关注。
那以后没几天,拿破仑动身去奥松,两次被风浪打回海岸,后来还是上路了,这回是他的小弟弟路易陪他。
虽然长时间离队,拿破仑仍然受到炮兵团的欢迎。该团是保王党军官预备队,保王党军官们对他的雅各宾腔调提出指责。他带着弟弟住在隆巴尔家里,他的家就在沃邦街上,一大间一小间,家具十分简单。孩子(路易只有13岁)睡在小间简易床铺上。他们两个人每天只有3镑钱维持生活。拿破仑成天不出门,也不到咖啡馆去走动走动。正如他说的那样,贫困把他死死地关在门内。他自己做家务,自己做饭,他对弟弟却关怀备至,和风细雨,给他上课,甚至在他弟弟初领圣体时,让他反复背诵入门教程。也有时候不耐烦起来,给他一记耳光。但他爱自己的弟弟,对路易的进步分外高兴,甚至要弟弟学他的样子,当一名军官。他写信给约瑟夫,充满着爱怜的骄傲:“他会成为德才兼备之人。……本地的女人没有不喜欢他的。他说一口流利的法国语,小腔调地道而且轻巧,他进入社交场合,受到宠爱和欢迎,日常问题也一本正经,表现出30岁人的尊严。我早就看出,他比我们四个人有出息。的确,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有好的教养。”
拿破仑让多尔的印刷厂商若利为他排印“致比塔非奥科的公开信”。他带着路易步行到多尔校对清样。大清早4点从奥松出发,回来已经晌午了,来回走了32公里,著名公开信一印好,波拿巴首先给保利寄去好几份。同时他还请保利给他提供一些材料,以便完成他那部关于科西嘉的著作,巴博(族长)回信,逐一加以指责和拒绝。他警告波拿巴:“历史不是在青年时代写成。”
几次激烈的争论使他同好几位维系旧政权的同学闹翻了。有一天,他们之中的两个人威胁他,要把他扔到河里去。他们指责拿破仑在炮兵团的士官和士兵中宣传新思想。的确,他给他手下的人读最激进的报纸,主张军民联盟,到处煽风点火。他来到尼伊参加他的朋友加桑迪的婚礼时,也不放过炫耀自己的观点。炮兵团的许多军官都收到请帖。加桑迪是保王派,而岳父却是爱国者。讨论政治问题一度使人忘了结婚喜庆,波拿巴狂热地支持其岳父从前的观点。晚上,他应邀到当地最富丽堂皇的府邸,竟当着贵宾们的面同人争论起国家大事来。多尔小城街谈巷议这位扮演护民官角色的令人不可理解的军人,几天余音未了。
此时,军事当局改组炮兵。随之而来的是加官晋级。波拿巴从二等中尉提为一等中尉。十分遗憾的是,他必须离开拉费尔炮团,调往格勒诺布尔炮团,该团驻防瓦朗斯。他在奥松留下了真挚的友谊,他对此终生难忘。
拿破仑带着弟弟一起离开了奥松,又回到布老小姐那里租下原来的那间房子,并在“三鸽”旅店包了伙。路易则交给老板娘照顾,他与一位公证人的儿子做了伙伴,他叫弗朗索瓦·梅藏热尔,与路易同龄,后来托路易的洪福,从路易的青云直上中沾了光。
拿破仑当年的老熟人许多都不在了。圣·吕夫神父未能等到加冠就死了。德·洛朗森小姐已经结婚。但德·科隆比埃夫人和可爱的卡罗利娜在乡间别墅愉快地招待了他。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