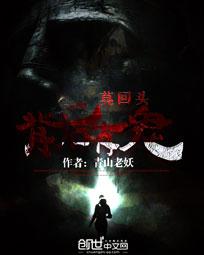快走!慢回-第3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老太太把他们让进了客厅,在让他们坐下来之前用手拍了拍长凳。
“现在,警察局里也有女的了?”她蔑视地朝埃莱娜·弗罗瓦西扫了一眼,“我可不想恭维你们。现在玩武器的男人已经够多了,还要女人也跟着玩?你们有时不会有其他想法?”
克莱芒蒂娜说的“有时”带有乡下口音。
她叹了一声,走进厨房,端来一个盘子,上面放着酒杯,还有一碟糕点。
“人类缺乏的永远是想像力,”她把盘子放在印花软垫长凳前一张铺着桌布的小桌子上,说,“烧酒、奶皮馅饼,你们喜欢吗?”
亚当斯贝格惊讶地看着她,几乎都被她苍老而沉重的脸迷住了。凯尔诺基恩向探长示意他想吃馅饼,在车上吃的三明治早就消化掉了。
“多吃点,”克莱芒蒂娜说,“可惜,现在已经找不到奶皮了。奶已经变成了水。我只好用奶油来代替。”
克莱芒蒂娜倒了五杯酒,喝了一小口,然后看着他们。
“不开玩笑了,”她点着一根烟,“你们到这里来有什么事?”
“为阿尔诺·达马斯·埃莱尔…德维尔的事。”亚当斯贝格拿起一小块馅饼,说。
“对不起,应该说阿尔诺·达马斯·维吉尼耶,”克莱芒蒂娜说,“他喜欢这样叫。在这屋里,我们不说埃莱尔…德维尔。如果你一定要说,那就请到外面去说。”
“他是你的外孙?”
“哎,愁眉苦脸的美男子,”克莱芒蒂娜朝亚当斯贝格扬扬下巴,“别把我当傻瓜。如果你不知道,你不会到这里来的,不是吗?这些馅饼怎么样?好吃还是不好吃?”
“好吃。”亚当斯贝格肯定道。
“好吃极了。”当格拉尔也说,他真的觉得好吃。说实话,他至少已经有40年没有吃到过这么好吃的馅饼了,他开心得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不开玩笑了,”老太太说。她一直站着,打量着这四个警察,“给我一点时间,让我换掉围裙,关上煤气,通知一下女邻居,然后就跟你们走。”
“克莱芒蒂娜·库尔贝,”亚当斯贝格说,“我有搜查证。我们要看看屋子。”
“你叫什么?”
“让…巴蒂斯特·亚当斯贝格。”
“让…巴蒂斯特·亚当斯贝格,我没有习惯让没有伤害过我的人去冒险,不管他们是不是警察。老鼠在阁楼上,”她指着天花板,“382只老鼠,加上12只死老鼠,它们的身上布满了饥饿的跳蚤,我劝你们不要接近,否则,我不能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如果你们想上去看看,必须先消毒。别碰了头。养殖的东西在上面,阿尔诺的机器,他用来写信的打字机在小房间里,信封也在那里。你们还对什么感兴趣?”
“书房。”当格拉尔说。
“也在阁楼上,但必须在老鼠前面经过。400本书,够吗?”
“关于鼠疫的?”
“还能关于什么?”
“克莱芒蒂娜,”亚当斯贝格又拿起一块馅饼,轻声地说,“你不想坐下来吗?”
克莱芒蒂娜胖胖的身子在一张雕花椅子上坐下来,交抱着双臂。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亚当斯贝格问,“为什么不否认?”
“否认什么?传播鼠疫?”
“五个受害者。”
“去他的受害者,”克莱芒蒂娜说,“他们是刽子手。”
“是刽子手,”亚当斯贝格说,“施刑者。”
“他们可以死了。他们死得越快,阿尔诺便复活得越快。他们夺走了他的一切,把他打进了十八层地狱。阿尔诺必须复活,但如果这些败类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他就不可能复活。”
“这些败类不会自行消灭的。”
“真是令人难以置信。这些败类的生命力比荆棘还强。”
“得给他帮忙吗,克莱芒蒂娜?”
“只需帮一点点。”
“为什么要选择鼠疫?”
“茹尔诺家族是鼠疫专家,”克莱芒蒂娜说,口气十分生硬,“总之,不该伤害茹尔诺家族的人。”
“否则会怎么样?”
“否则,茹尔诺家族的人会给他寄鼠疫。他们是研究这一大灾难的专家。”
“克莱芒蒂娜,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亚当斯贝格又问。
“而不是怎么样?”
“而不是沉默。”
“你们已经找到我了,不是吗?孩子昨天就已经被关起来了。所以,不用开玩笑了。跟你们走就是了,这不完了嘛!这有什么不一样呢?”
“一切都不一样。”亚当斯贝格说。
“没有什么不一样,”克莱芒蒂娜强笑着,“工作已经结束。你明白了吗,探长?结束了。敌人就在广场上。还有三个人一星期之内就要死,不管发生什么事,不管我在这里还是在别的地方。太晚了。工作已经结束,他们八个人都得死。”
“八个人?”
“六个动手的人,包括那个残忍的女人和幕后策划者。对我来说他们是八个人。你们知道还是不知道?”
“达马斯没有说。”
“这很正常。在他不肯定工作是否结束之前,他不可能说。我们就是这样约定的,假如我们当中有一个人被捕的话。你们是怎么发现他的?”
“通过他的钻戒。”
“他把它藏起来了。”
“被我看见了。”
“啊,”克莱芒蒂娜说,“你知道一些,知道一些关于上帝之祸的事。这我们倒没想到。”
“我试图学得快点。”
“但已经太晚了。工作已经完成了,敌人就在广场上。”
“跳蚤?”
“是的。他们身上已经有跳蚤了,他们已经受传染了。”
“他们叫什么名字?克莱芒蒂娜?”
“你们就追查吧。你们还想救他们的命?这是他们的命运,事情已经结束。不该伤害茹尔诺家族的人,但他们伤害了,探长,他们伤害了他和他所爱的女孩,那可怜的女孩,从窗口跳了出去。”
亚当斯贝格摇摇头。
“克莱芒蒂娜,是你劝他们报复的吗?”
“坐牢的时候几乎每天都说起这事。他是曾祖父的继承人,也是那枚钻戒的继承人。阿尔诺必须抬起头来,就像传染病爆发时的埃米尔一样。”
“你们不怕坐牢?你不怕,达马斯也不怕?”
“坐牢?”克莱芒蒂娜用双手一拍大腿,“探长,你是在开玩笑吧?我和阿尔诺没有杀过任何人。”
“那是谁杀的?”
“跳蚤。”
“释放感染了病菌的跳蚤,就像向人开枪一样。”
“等等,跳蚤并不一定会咬人。那是上帝之祸,它爱落到谁身上就落到谁身上。如果说有谁杀了人,那就是上帝。你们也打算逮捕上帝吗?”
亚当斯贝格凝视着克莱芒蒂娜·库尔贝的脸,她跟她孙子一样平静。现在,亚当斯贝格明白了达马斯为什么那么平静,那么雷打不动:他们俩认为自己刚刚杀了五个人,计划还要再杀三个人,这完全是正义的。
“不开玩笑了,”克莱芒蒂娜说,“现在该说的都说了,我是跟你们走呢还是留下?”
“我要你跟我们走一趟,克莱芒蒂娜·库尔贝,”亚当斯贝格站了起来,说,“让你去作证。你被拘留了。”
“我无所谓,”克莱芒蒂娜也站了起来,“这样,我就能见到那孩子了。”
克莱芒蒂娜整理桌子,灭了火,关了煤气,这时,凯尔诺基恩却示意亚当斯贝格他不敢上阁楼搜查。
“她没有感染,”亚当斯贝格说,“你要这个老太太到哪里去找有鼠疫的老鼠?她在梦想,凯尔诺基恩,她是在幻想。”
“她可不是这样说的。”凯尔诺基恩神色忧郁地回答说。
“她每天都在弄那些东西,却没有感染。”
“探长,茹尔诺家族的人是受到保护的。”
“茹尔诺家族的人在做梦。你不会有事的,相信我吧!他们只进攻试图摧毁茹尔诺家族的人。”
“这么说,是家族复仇?”
“一点没错。带点木炭走,送到实验室去,快!”
老太太的到来,在警队里引起了好奇。她带来了一个大盒子,里面装着满满的馅饼。她来到达马斯面前,怜爱地把饼递给他。达马斯笑了。
“别担心,阿尔诺,”她一点都没有压低声音,“工作已经结束。他们全都染上了。”
达马斯笑得更欢了,他抓住老太太隔着铁栅门递过来的盒子,转过身,平静地在长凳上坐下。
“在达马斯的监室旁边给她找间房,”亚当斯贝格命令道,“再从衣帽间里给她拿个床垫,尽量让她住得舒服点。克莱芒蒂娜已经90岁了。”说完,他回到老太太身边,“不开玩笑了,现在作证还是先休息一会儿?你是不是累了?”
“现在就作证。”克莱芒蒂娜坚决地说。
傍晚,快到六点的时候,亚当斯贝格又出去散步了,他脑袋昏沉沉的,满脑子都是克莱芒蒂娜·茹尔诺,也就是库尔贝的妻子的事。他听她说话听了两个小时,然后把祖孙的说法进行对照。他们一点也不怀疑最后三个虐待者就要死亡,亚当斯贝格告诉他们,放置跳蚤和受害者死亡之间的时间太短,短得不可能在死者身上放置感染了鼠疫的跳蚤,但无济于事。“那种灾难随时准备着,听从上帝的指挥。上帝高兴的时候便派遣和降临这种灾难。”克莱芒蒂娜曾回答说。她准确无误地背诵着9月19日的“特别广告”。亚当斯贝格向他们指出,化验的结果为阴性,这证明他们的跳蚤完全没有病菌;他把受害者被掐死的照片给他们看,但没有用,他们对跳蚤的信任仍然不可动摇,他们尤其相信那三个人很快就将死亡,一个在巴黎,一个在特洛伊,最后一个在沙泰勒罗。
亚当斯贝格在马路上散了一个多小时的步,最后在疯人院对面站住了。楼上,有个病人从栅栏中伸出一只脚。总是有人伸出脚,在阿拉戈大道的上空摇晃。没有一只手,总是脚。没有穿袜子,赤着脚。有个家伙像他一样,想到外面来散步。亚当斯贝格看着那只脚,想起了克莱芒蒂娜的脚,然后又想起达马斯的脚,他们的脚以天空为背景,缠绕在一起了。他不相信他们疯到了这种程度,除非是在这条走廊中,他们是被幽灵引到这里的。当那只脚突然缩回牢房时,亚当斯贝格突然醒悟过来:第三者仍在墙外,带着活结,准备完成已经在巴黎、特洛伊和沙泰勒罗开始的工作。
《快走!慢回》第八部分
三十五
亚当斯贝格斜着走向蒙帕纳斯,来到了埃德加…基内广场。一刻钟后,贝尔丹将敲响吃晚饭的洪钟。
他推开海盗小饭店的门,心想那个诺曼底人今晚是否敢抓住他的衣领,就像昨晚对待那个客人一样。但亚当斯贝格溜进海盗船的龙头下面,来到他那张桌子前的时候,贝尔丹并没有动。他没有动,但也没有跟亚当斯贝格打招呼。亚当斯贝格一坐下,他就从柜台里走出来。亚当斯贝格知道,两分钟之后,广场上的人都将知道抓达马斯的警察正在小饭店里,很快,所有的人都会盯着他。这正是他到这里来的目的,甚至,德康布雷的晚餐也许会破例搬到“海盗”来吃。他把手机放在桌子上,等待着。
五分钟后,一群满怀敌意的人推开了小饭店的门,走在前面的是德康布雷,后面跟着丽丝贝特、卡斯蒂永、勒盖恩、埃娃等人,只有勒盖恩对事情有点无动于衷。这些让人不安的消息早就不能再让他不安了。
“坐下吧,”亚当斯贝格几乎是在命令他们。他抬起头,面对着那些把他团团围住的充满敌意的面孔,“那女孩在哪?”他在寻找玛丽…贝尔。
“她病了,”埃娃瓮声瓮气地说,“她躺在床上。都是因为你。”
“埃娃,你也坐下来。”亚当斯贝格说。
那个年轻的女人一天之间就完全变了一个人,亚当斯贝格从她脸上明白无误地看出了仇恨,这种仇恨使她失去了忧郁的古典美。昨天她还那么楚楚动人,今晚她却咄咄逼人。
“探长,把达马斯放出来,”德康布雷打破了沉默,“你搞错了,大错特错。达马斯是个爱好和平的人,一个温顺的人。他从来没有杀过人。从来没有。”
亚当斯贝格没有回答,而是走到厕所去给当格拉尔打电话,要他派两个警察在国民公会路玛丽…贝尔的住处附近监视。然后,他又回到桌边,面对着那个老文人,德康布雷不屑地看着他。
“五分钟,德康布雷,”亚当斯贝格举起一只手,五指分开,“我讲一个故事。我才不管大家讨不讨厌呢!我要讲。讲的时候,我要采取我的节奏和我的语言。有时,我的助手都会听得打瞌睡。”
德康布雷扬起头,没有说话。
“1918年,”亚当斯贝格说,“捡破烂的埃米尔·茹尔诺平安地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回来了。”
“我们才不管他那么多呢!”丽丝贝特说。
“别说话,丽丝贝特,他在说话,让他说下去。”
“在前线打了四年仗,毫发未损,”亚当斯贝格接着说,“可以说是一个奇迹。1915年,这个捡破烂的人在无人地带背回了受了伤的上尉,救了上尉的命。为了感谢他,上尉在撤到后方去治伤之前,把自己的戒指送给了列兵茹尔诺。”
“探长,”丽丝贝特说,“我们不是到这里来听过去的美好故事的,别采取疲劳战术了。我们到这里来是来谈达马斯的事的。”
亚当斯贝格看了丽丝贝特一眼。她脸色苍白,亚当斯贝格第一次看见黑皮肤发白,丽丝贝特的肤色变成了灰白色。
“可是丽丝贝特,达马斯的故事是美好的过去的一个古老的故事,”亚当斯贝格说,“我接着说。列兵茹尔诺没有白白浪费时间。上尉的戒指上有颗钻石,那个钻石比扁豆还要大。在整个战争期间,埃米尔·茹尔诺都戴着这枚钻戒,面朝里,包着泥土,以免被人夺走。1918年退伍后,他回到了克里希,重新生活在贫穷中,但他没有卖这枚钻戒。对于埃米尔·茹尔诺来说,这是救命的钻戒,是神圣的。两年后,鼠疫在他所住的小镇爆发,整条小巷的人都死光了,但茹尔诺家族的人,埃米尔、他的妻子和他们六岁的女儿克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