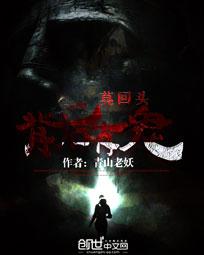快走!慢回-第2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你敢肯定吗,旺多斯勒?”
“当然。1720年5月25日,‘圣安东尼大帝号’ 载着一包包受鼠疫感染的丝绸,从叙利亚和塞浦路斯来到了伊夫城堡群岛,船上的船员已经发病死亡。名字没有写出来的医生是佩索内尔父子俩,他们发出了警报。那篇东西很出名,那种传染病也同样,那场灾难夺走了马赛差不多一半人的生命。”
“那个小伙子,也就是那个埃萨勒,医生们去哪儿给他看病?”
“林奇广场,现在叫林希广场,就在老港北部码头后面。最初染上鼠疫的那座屋子毁了埃斯卡尔路。那条路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不会弄错吧?”
“绝不会弄错,是在马赛。如果你想得到证实,我可以把原文复印一份给你。”
“这就没必要了,旺多斯勒。谢谢你。”
亚当斯贝格走出自己办公室,心里七上八下的。当他来到当格拉尔身边时,当格拉尔正和其他30多名警察一起试图对付应接不暇的电话,密切关注那场迷信的龙卷风带来的后果。大办公室里充满了啤酒的味道,到处都是汗臭。
“快了,”当格拉尔说,他一边放下电话,一边记下一个数字,“巴黎全城很快就要没有绘画颜料卖了。”
他朝亚当斯贝格抬起头,额头湿漉漉的。
“那个传播者来自马赛,”亚当斯贝格把那份特别广告放在当格拉尔眼前,说,“当格拉尔,我们动身。”
“天哪!”当格拉尔迅速浏览了一下那篇东西:圣安东尼大帝号来临。
“你听说过这事吗?”
“现在你一说,我就想起来了。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马上把它破译出来。”
“它比其他段落更出名吗?”
“当然。这是法国出现的最后一场传染病,但非常厉害。”
“并不是最后一场,”亚当斯贝格把那篇有关9号病的文章递给他,说,“你读一读就会明白,为什么从今天晚上起,没有一个巴黎人会再相信警察说的话。”
当格拉尔看着那篇文章,摇摇头,说:
“一场灾难。”
“别再用这个词了,我求你了,当格拉尔。给我接马赛的同事,老港区警察局。”
“老港区由马塞纳负责,”当格拉尔嘀咕了一句,他熟悉全法国的警察局和警察分局,就像熟悉每个地区的首府一样,“一个有用的家伙,不像他的前任,由于想给阿拉伯人放血,毒打和伤害他们,结果被降了职。马塞纳取代了他,马塞纳很正派。”
“希望是这样,”亚当斯贝格说,“因为我们得跟他联系。”
六点零五分,亚当斯贝格已经坐在埃德加…基内广场听当晚的广告,广告没什么新东西。自从传播者不得不通过邮局来寄广告以后,他的时间就受到了局限。亚当斯贝格知道这一点,他到那儿去,是为了看一看围在勒盖恩身边的人的面孔,人群比前两天密集,许多人伸长脖子,想看看那个“广告宣读者”长得什么样。人们就是通过他的口得知那种传染病的。负责长期监视广场的那两个警察现在增加了一项任务,就是保护若斯·勒盖恩的安全,生怕在宣读广告的过程中有人对他发起不友好的攻击。
亚当斯贝格靠在离高台很近的一棵树上,德康布雷给他介绍自己所熟悉的那些人,老文人已经列出一个40多人的名单,并分成三类:铁杆者、忠诚者、不坚决者,附有“相关”的(这是勒盖恩的口头禅)体貌特征。他在那些利用巴黎历史之页来赌菲尼斯太尔海难结果的人名下面划了一道红杠;听完广告后赶紧去工作的人名下面划蓝杠;广告念完还赖着不走,呆在广场或去海盗小饭店继续讨论的人名下面划黄杠;专听市场信息的熟客的名字下面划紫杠。这项工作做得干净利落。德康布雷手里拿着纸,悄悄地给探长指着相关的面孔。
“卡尔美拉号,从波尔多空载出发、前往加的夫的405吨奥地利三桅船,在加斯克…阿尔维莱沉没。船员14人,全部得救。”
若斯结束了宣读,跳下高台。
“快看,”德康布雷说,“那些露出惊讶的神色、皱起眉头、感到莫名其妙的人,就是新来者。”
“也就是划着蓝杠的人。”亚当斯贝格说。
“没错。那些互相讨论、点头挥臂的,是熟客。”
说完,德康布雷就撇下亚当斯贝格去帮丽丝贝特剥四季豆了,那是他们低价成筐买来的。亚当斯贝格走进海盗小饭店,从海盗船的龙首下面钻过,来到那张桌子边坐下,他已经把它作为自己的桌子。就海难打赌的人都聚在小饭店里,钱币在他们手中传递,哗拉哗拉响。贝尔丹拿着打赌的单子,免得有人作弊。由于他出身清白,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靠得住的人,不会接受贿赂。
亚当斯贝格要了一杯咖啡,慢慢地琢磨着玛丽…贝尔的长相。她正在旁边的一张桌子边上写信,非常专心。这是一个长得挺细腻的姑娘,如果嘴唇的线条更清晰些,几乎可以说是一个挺讨人喜欢的女孩。她像她哥哥一样,一头卷曲的浓发,金色的长发垂在肩膀上,但非常干净。她对亚当斯贝格笑了笑,然后又埋头写起信来。旁边,有个叫埃娃的女人在努力帮助她完成任务,埃娃没有玛丽…贝尔那么漂亮,也许是因为她没有玛丽…贝尔那么自由。她的脸很光滑,但神色庄重,眼皮底下有紫圈,亚当斯贝格想起了19世纪被关在外省豪华住宅里的某个女英雄。
“是这样吗?你觉得这样他能看懂吗?”玛丽…贝尔问。
“挺好,”埃娃说,“只是短了一点。”
“要告诉他这里的天气吗?”
“可以。”
玛丽…贝尔又写了起来,手里的钢笔攥得紧紧的。
“‘凉’字是两点水。”埃娃说。
“你能肯定吗?”
“我想是的。让我试试。”
埃娃在草稿纸上试了好几次,然后皱了皱眉头,犹豫不决地说:
“我也拿不准了,我被搞糊涂了。”
玛丽…贝尔向亚当斯贝格扭过头来,“探长,”她有些害羞地说,“‘凉’字是两点水还是三点水?”
在亚当斯贝格的一生中,这还是第一次有人问他生字,他不知如何回答。
“整个句子是这样的:‘达马斯没有着凉。’”玛丽…贝尔具体解释道。
“跟句子没有任何关系。”埃娃低声说,她还趴在桌上研究那张草稿纸。
亚当斯贝格对玛丽…贝尔说,他对书写一窍不通,玛丽…贝尔听了以后感到非常奇怪:“可您是警察啊!”
“这没错,玛丽…贝尔。”
“我走了。”埃娃摸了一下玛丽…贝尔的胳膊,说,“我答应过达马斯帮他算账的。”
“谢谢,”玛丽…贝尔说,“谢谢你替我干活。我要写这封信,所以脱不了身。”
“不用客气,”埃娃说,“我很高兴。”
她悄无声响地消失了,玛丽…贝尔立即朝亚当斯贝格转过身来:
“探长,我能跟她谈谈那……那场……灾难吗?还是尽量什么都不说?”
亚当斯贝格慢慢地摇摇头:
“并没有什么灾难。”
“那4字呢?黑色的尸体呢?”
亚当斯贝格又摇了摇头:
“最多是一个凶手罢了,玛丽…贝尔,这已经够多了。没有鼠疫,连影子都没有。”
“我能相信您吗?”
“完全可以。”
玛丽…贝尔又露出了笑脸,这次,她彻底放松了。
“我怕埃娃爱上达马斯,”她皱起眉头,好像亚当斯贝格既然替她解决了有关鼠疫的问题,也能解决她生活中的其他复杂问题,“顾问说这样挺好,生命复苏了,必须听之任之。可我这次不同意顾问的意见。”
“为什么?”亚当斯贝格问。
“因为达马斯爱上了那个胖胖的丽丝贝特。”
“你不喜欢丽丝贝特?”
玛丽…贝尔撅了撅嘴,然后又说:
“她很勇敢,但太闹了,她这样弄得我有点害怕。不管怎么说,丽丝贝特在这里是谁也不能碰的。顾问说,她就像一棵树,庇护着一些鸟。我很愿意这样,但这棵树吵得让人耳朵受不了。而且,丽丝贝特几乎到处都指手画脚,所有的男人都对她服服帖帖,自觉自愿,因为她经验丰富。”
“你妒忌了。”亚当斯贝格微笑着问。
“顾问说我肯定妒忌了,但我自己没有意识到。让我感到不舒服的是,达马斯每天晚上都往她那里跑。必须承认,如果你听丽丝贝特唱歌,你会被她迷住。达马斯真的被迷住了,他眼里没有埃娃,因为埃娃太静了。当然,埃娃让人烦多了,但毫无疑问,这与她的经历有关。”
玛丽…贝尔向亚当斯贝格投去询问的一瞥,想看看他知不知道埃娃。显然,亚当斯贝格不知道。
“她丈夫打了她几年,”她解释说,“无法再忍受下去,于是她出逃了,她丈夫到处追杀她。您能想像得到吗?警察干吗不首先杀了她丈夫呢?谁也不许知道埃娃的真正姓名,这是顾问的命令,对打听这事的人要小心。顾问知道她的名字,这是他的权力,因为他是顾问。”
亚当斯贝格一边听玛丽…贝尔讲话,一边不时地向广场上扫上一眼,看看那里有些什么情况。勒盖恩正往梧桐树上挂箱子,准备接收晚上用的广告。亚当斯贝觉得从警队一路追随着他的电话铃声慢慢地消失了。谈话声越轻,他心里就越放松。他思考得脑袋都要爆炸了,烦死了。
“是的,”玛丽…贝尔向他转过身来,真心实意地说,“这是为了埃娃好,因为经过这事以后,她看到画成肖像的男人就受不了。这会让她想起往事。见到了达马斯,她才明白,世界上还有比那个揍她的坏蛋更好的男人。这完全是因为,对女人来说,如果没有男人,我觉得这是千真万确的,生活将毫无意义。丽丝贝特不相信这一点,她说所谓的爱情,无非是用来骗人的把戏。她甚至说,那是无聊透顶的东西。您看看。”
“她当过妓女?”亚当斯贝格问。
“没有这回事,”玛丽…贝尔显得很惊讶,“您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亚当斯贝格很后悔问了这个问题。玛丽…贝尔比他想像的还要天真,这就更让人放心了。
“是因为您的职业的缘故,”玛丽…贝尔一副痛苦的样子,“它使您把一切都颠倒了过来。”
“恐怕是这样。”
“您呢,您相信爱情吗?请允许我问东问西,因为在这里,丽丝贝特的话就是最高指示。”
亚当斯贝格没有回答,玛丽…贝尔摇了摇头,最后说:
“这是毫无疑问的,一切您都看见了。但顾问却相信爱情,不管是真是假。他说,自欺欺人总比坐在那里生闷气好。对埃娃来说,这是真的。自从她在晚上帮达马斯算账以来,她显得活泼多了。只是,达马斯不爱她,而是爱丽丝贝特。”
“是的。”亚当斯贝格说。他看见对方在兜圈子,并没有感到不高兴。圈子兜得越远,他越没有话说,鼠疫啊、门啊也就忘得越快。现在,那几百扇门都已经写满了4字。
“丽丝贝特不喜欢达马斯,所以埃娃在努力。当然,达马斯也在努力,丽丝贝特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
玛丽…贝尔在想一个能让大家皆大欢喜的办法。
“你呢,”亚当斯贝格问,“你喜欢什么人吗?”
“我嘛,”玛丽…贝尔脸红了,用手指轻轻地拍打着信纸,说,“我有两个哥哥,我要照顾的男人够多的了。”
“你在给你哥哥写信?”
“是的。我在给我小哥哥写信。他住在罗莫朗坦,他希望经常收到我的信。我每个星期都给他写信或打电话。我想让他到巴黎来,但他害怕巴黎。他和达马斯不是很合得来,而小哥哥更忍受不了达马斯。我什么都要教他,甚至要教他怎样跟女人打交道。我的小哥哥是个英俊的小伙子,一头金黄的头发。可是,他一直等着我推他,否则他就不动。所以,我甚至得管他结婚,这是当然的啦。我有的是事干,况且达马斯还要空等丽丝贝特好多年。最后,流泪的是谁?顾问说,我没有义务去管这些事。”
“他说得对。”
“他管好多事,好多人的事。他们整天在他书房里进进出出,但他没有诈他们的钱。他的建议并非没有价值。可是,我总不能看到我的兄弟们倒霉。”
“这并不妨碍你爱什么人。”
“当然有妨碍,”玛丽…贝尔坚决地说,“又要忙工作,又要管店铺,我见到的人不多,这是当然的事。在这里,没有一个人讨我喜欢。顾问对我说,到远一点的地方去看看。”
小饭店里的挂钟敲响了,7点半了,玛丽…贝尔惊跳起来,迅速把信叠起来,又在信封上贴上邮票,塞进小包里:
“请原谅,探长。我得走了,达马斯在等着我呢!”
她一路小跑着走了,贝尔丹过来收走了杯子。“她很嗦,”这个诺曼底人好像是来替玛丽…贝尔道歉的,“她说的关于丽丝贝特的事,您不要全信。玛丽…贝尔在吃醋呢!她担心丽丝贝特抢走她哥哥。丽丝贝特是个很人道的女人,不会搀和这些乱七八糟的事。谁都无法理解。您留下来吃晚饭吗?”
“不了,”亚当斯贝格站起身来,说,“我还有事。”
贝尔丹把亚当斯贝格一直送到门口,问:“您说,探长,到底要不要在门上写上4字呢?”
“您是雷公之子,”亚当斯贝格转过身来,“还是我在广场上听到的都是无稽之谈?”
“我的声音就是这么大,”贝尔丹扬起头,说,“是天生的。”
“那好,贝尔丹,如果你不想让你的前辈在你屁股上踹上一脚,要你滚蛋,你还是不要在门上写4字吧!”
贝尔丹关上门,头仍然扬着,突然下定了决心:只要他还活着,海盗小饭店的门上就不会出现4字。
半小时后,丽丝贝特集合房客们吃晚饭。德康布雷用餐刀敲打着酒杯,要大家安静,他觉得这种动作虽然有点庸俗,但有时是必要的。卡斯蒂永很快就明白了他的用意,马上就安静下来。
“我不喜欢向我的客人发布命令,”——德康布雷喜欢用“客人”这个词,而不喜欢用“房客”,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