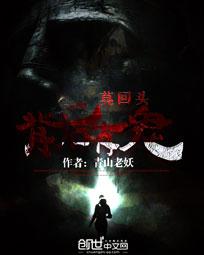快走!慢回-第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若斯早就发现,在巴黎,人们走路的速度要比在吉维内克快。每天早晨,行人们以每小时三节的速度流过马里讷大道。这个星期一,若斯几乎是以每小时三节半的速度赶路,他迟了20分钟,因为咖啡渣全都洒在了厨房的地上。
他并不感到奇怪。若斯早就知道事物本身具有一种神秘而病态的生命。也许除了某些从来没有伤害过他的甲板以上的船舱,在这个布列塔尼水手看来,事物的世界显然充满了活力,随时准备跟人类作对。稍微掌握不好,突然给事物以自由,哪怕一点点自由,都会引起一连串灾难,程度不等,可能仅仅是让人不悦,也可能是酿成悲剧。瓶塞从手指中飞出,就是一个小小的例子和证明。因为飞出去的塞子绝不是落在人们的脚边,而是落在炉子后面。可恶!就像到处觅食的蜘蛛,给它的猎杀者——人类以一系列变化莫测的考验。移开炉子,连接炉子和煤气管的软管脱了下来,厨具掉在了地上,或者烫了手。而今天早晨发生的情况则更加复杂,扔垃圾时犯了一个小错误,垃圾袋太不坚固了,旁边破了,咖啡渣洒在了地上。被奴役的事物理所当然会产生报复思想,虽然不很经常,但时时都想着以其潜在的力量迫人类就范,让他们像狗一样蜷缩成一团,在地上爬着,妇女和儿童也不能幸免。不,若斯从来就不相信事物,也不相信人类和大海。事物会使你失去理智,人类会使你丧失灵魂,而大海则会夺走你的生命。
若斯是一个饱经风霜的人,他没有向命运挑战,而是像狗一样,一把一把地捡起咖啡渣。他一句牢骚都不发,弥补了自己的过失,事物的世界退潮了。早晨的这个小事故并不是一件小事,表面上看起来不过是一件让人不愉快的事情罢了,可以把它忘了,但若斯在这件事上决不会搞错。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表明人类和事物的战斗在继续,在这场战斗中,人类不总是胜者,远非如此。这是悲剧的预兆,远洋巨船断了桅杆,拖网渔船触礁粉碎。8月23日凌晨3时,他的那艘船,“西北风”号在爱尔兰海域漏水,船上有8个人。然而,谁知道若斯是否满足了他那艘拖网渔船让人发疯的苛求,又有谁知道人与船是否达成了妥协。在那个可恶的暴风雨之夜,他突然使尽全力,用拳头猛击船的右舷。当时,“西北风”号几乎已经侧翻,船尾突然进水。机器被淹了,渔船在夜间失控,船员们不停地往外舀水,最后,渔船在黎明时分沉到了珊瑚礁上。那是14年前的事了,死了两个人。14年了,若斯踢翻了船主;14年了,若斯出狱后离开了吉维内克,他因蓄谋杀人并伤害了他人而被判入狱9个月;14年了,他的整个生命几乎都已被海水冲走。
若斯走下盖泰路,牙齿咬得紧紧的,每当想起消失在大海中的“西北风”号,他就气不打一处来。其实,他的火并不是冲着“西北风”号来的,那艘漂亮的旧渔船只不过是年久失修,船身腐烂,顶不住风浪的打击而已。那天晚上,那艘船肯定没有掂量过自己能抗几级风浪,它已经忘了自己多大岁数,忘了自己已年老体衰,吱嘎作响。渔船肯定不愿意让那两名船员死去,至今还傻傻地躺在爱尔兰的海底,它很后悔。若斯常常跟它说话,安慰它,宽恕它,他觉得那艘船现在已经像他一样,终于得到了安息,在海底开始了另一种生活,就像他在这里,在巴黎开始新的生活一样。
然而,宽恕船主,这是不可能的。
“走吧,若斯·勒盖恩,”船主拍了拍他的肩膀,说,“这艘破船,你还可以再开10年。它结实得很呢!你是它的船长。”
“‘西北风’号已经很危险了,”若斯固执地说,不知重复了多少遍,“它的螺丝松了,船底板变形了,船盖破了。我可不敢保证它能抗得住海上的大风浪。这船已经不符合安全规范了。”
“我了解我的船,勒盖恩先生,”船主的口气严肃起来,“如果你害怕驾驶‘西北风’号,我打个响指,马上就有10个人来替换你。他们勇敢大胆,不会像办公室里的白面书生那样无病呻吟,空谈什么安全规范。”
“可船上还有我的7个弟兄。”
船主把他那张油光油亮的脸凑过来,威胁他说:
“若斯·勒盖恩,如果你胆敢到港务监督处去告状,我马上就把你打翻在地。从布雷斯特到圣纳泽尔,你再也找不到一个人雇佣你。船长,我劝你还是好好想想。”
是的,若斯一直后悔,在发生海难的第二天,他没有要那个家伙的狗命,只是打断了他的一只胳膊和他的肋骨。船员们把他拉住了,劝他说,若斯,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他们拦住他,制止了他,使他没能打死船主及其爪牙。他一出狱,他们就把他的名字从花名册上勾掉了。若斯在酒吧里大喊大叫,说港务监督处的官员们受贿,但他后来不得不告别渔船。若斯跑了许多港口,最后在一个星期二的早晨,跳上了一艘从坎佩尔开往巴黎的船只,像在他之前的许多布列塔尼人一样,来到了巴黎的蒙帕纳斯车站广场,撇下了一个要逃跑的女人和9个要杀的男人。
看见爱德加…基内大街的十字路口时,他暂时忘记了昔日的深仇大恨,准备弥补失去的时间。咖啡渣事件、事物的战争和人类的战争至少浪费了他一刻钟。而在他的工作中,守时是最重要的,他要在8点30分第一遍朗读他的广告,12点35分读第二遍,晚上版则在18点10分读。这三个时间段人最多,在这个城市里,听众们太心急了,容不得迟到一点。
若斯把箱子从树上摘下来,用手掂了掂。他是晚上挂上去的,用绳子绕上两圈,打个结,再加两个防盗装置。今天上午,箱子不太满,他可以选得快一点。他微微一笑,抱着箱子走向小店的后间,那地方是达马斯借给他用的。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一些像达马斯那样善良的人的,他们留你一把钥匙,让你使用桌子的一角,不担心你会撬他们的钱箱。达马斯,那是一个人名;他在广场边开了一家店,叫“罗尔…里德”①,他让若斯进店来整理要宣读的公告,免得在外面风吹雨打。罗尔…里德,那是一个店名。
若斯打开了箱子,那是一个大木箱,他亲手做的,他把它叫做“西北风”二号,以纪念他已经失去的心爱的船。对一艘巨大的拖网渔船来说,见自己的残骸沦为巴黎的一个信箱,这也许并不光彩。可这个信箱不同寻常,这是七年前根据一个天才的设计制成的一个天才的信箱,它使得若斯在罐头厂干了三年、在管道厂干了六个月,然后又失业两年后,了不起地重新爬上了斜坡。那个天才的念头是在12月的一个晚上产生的,那天晚上,他手里端着酒杯,沉迷在蒙帕纳斯的一家咖啡馆里,咖啡馆的顾客三分之一都是孤独的布列塔尼人,家乡的方言嗡嗡地响着,不断冲击着他的耳膜。有个家伙谈起了主教桥,结果,1832年诞生在洛克马里亚的曾曾祖父勒盖恩从若斯的脑海里走了出来,双肘支在吧台上,跟他打了个招呼。
“你好。”若斯也回了一声。
“你还记得我吗?”前辈问。
“天哪,”若斯嗫嚅道,“你死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更没有哭。”
“哎,孩子,别胡说八道了,就让我拜访你一次吧!你多大年纪了?”
“50岁。”
“你可活得不怎么样。要努力啊!”
“我不需要你的指教,我没有叫你。你活得也不怎么样嘛!”
“孩子,别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你知道我发起火来会怎么样。”
“是的,大家都知道,尤其是你的老婆,你打了她一辈子。”
“好了,”前辈做了个鬼脸,说,“不要脱离当时的实际嘛!那是时代的要求。”
“去他妈的时代!是你自己想这样。你打伤了她的一只眼睛。”
“过去两个世纪了,还要说那只眼睛的事?”
“当然要说。举个例子嘛。”
“若斯,难道你要给我做榜样?你曾在吉维内克码头差点把一个小伙子踢死?要么是我搞错了?”
“其一,那个人不是妇女;其二,那个人也不是小伙子。那是一个黑心肠的有钱人,为了赚钱,他不惜让其他人去死。”
“是的,不能说你说得不对。这还没完,小毛孩子!你叫我了。”
“我已经告诉过你,我没叫你。”
“你真是个猪头。你有幸继承了我的眼睛,因为我很愿意给你一个机会。设想一下,我之所以出现在这里,是因为你叫了我,就是这样。而且,这不是我习惯去的酒吧,我不喜欢音乐。”
“好吧,”若斯沮丧地说,“要不要我请你喝一杯?”
“你还举得起手来吗?让我告诉你吧,你已经喝多了。”
“别多管闲事,前辈。”
老祖宗耸耸肩。他见过世面,这小毛孩可激怒不了他。勒盖恩家族的人出生高贵,这个若斯,没什么可说的。
“这么说,”老前辈吸着蜂蜜水,说,“你没有老婆,也没有钱?”
“你猜对了,”若斯回答说,“你当时好像没这么聪明。”
“这是因为我变成了鬼。人死了以后,能知道一些以前不知道的东西。”
“别开玩笑了,”若斯说着,无力地向侍者的方向举起手。
“在女人这方面,没必要请教我。那不是我的长项。”
“我应该想得到的。”
“不过,工作吗,小伙子,这并不难。你只要干回家族的老行当就可以了。你没必要去做水管,那是个错误。而且,你知道,做事情必须小心。卷绳吗,还说得过去,但水管,线,我就不提塞子的事了,最好还是出海吧。”
“我知道。”若斯说。
“必须利用自己的遗传基因,干回家族的老行当。”
“我再也不能当水手了。”若斯气愤地说,“我被流放了。”
“谁要你当水手了?天天跟鱼打交道,天哪,真是可悲。你看我当过水手吗?”
若斯端起酒杯,一饮而尽,然而专心考虑起这个问题来。
“不!”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你是个宣读广告的差役,从孔卡诺跑到坎佩尔,在公共场所宣读广告。”
“对了,我的孩子,我对此感到非常自豪。我叫阿尔·巴努尔,是宣读广告的差役。在南部海边,没有比我更好的宣读者了。阿尔·巴努尔每天都进入一个新的村庄,中午时分宣读广告。我可以告诉你,有些人天还没亮就开始等我。我的业务范围包括37个村庄。了不起吧,嗯?人不少,是吗?他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由于什么?由于我宣读的广告。由于谁?由于我,阿尔·巴努尔,菲尼斯泰尔地区最好的广告宣读人。我的声音能从教堂里一直传到盥洗室。我什么字都认识。大家都抬起头来听我宣读。我的声音,它创造了一个世界,创造了一种生活。你要相信,那可不是鱼。”
“没错。”若斯说着,抓起放在柜台上的那瓶酒,对着嘴就喝。
“第二帝国成立就是我宣布的。我一直走到南特去寻找消息,然后用马驮回来,新鲜得很。第三共和国,也是我在海滩宣读的。你会看到那有多热闹。当地的那些琐事我就不说了,比如婚礼、噩耗、谩骂、东西重新找回来了、孩子丢失了、靴子需要重做,这些,都是我宣读的。各村都给我广告宣读。庞马尔角的女孩向圣马里纳的小伙子求爱,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各种各样的丑闻,还有谋杀案。”
“你应该适可而止。”
“这么说吧,是别人付钱让我读的。我干我的活,如果我不宣读,这不是偷顾客的钱吗?勒盖恩家族中也许有粗人,但不会有强盗。他们的悲剧、他们的爱情,他们妒忌出海打鱼的水手,那不关我的事。我自己家里的事都忙不过来。我每个月一次去村里看望孩子们、做弥撒和泄欲。”
若斯端着酒杯叹息了一声。
“然后留下一点钱,”前辈补充道,口气十分坚决,“一个女人和八个孩子,花费大得很哪。但你要相信,有了阿尔·巴努尔,他们从来没有缺少过。”
“缺少耳光?”
“缺少钱,傻瓜。”
“要付那么多吗?”
“你爱付多少就付多少。如果说是世界上有一种产品不会枯竭,那就是广告;如果说有一种渴望永远不会平息,那就是人的好奇心。如果你是个宣读员,你就要哺育整个人类。要保证绝不断奶,绝不断粮。好了,傻瓜,如果你醉成了这个样子,你永远也当不了宣读员。从事这个职业需要思路清晰。”
“我不想让你伤心,前辈,”若斯摇摇头,说,“不过,‘宣读员’更多是一个需要实际经验的职业。你甚至会发现,几乎谁也不懂这个词。‘鞋匠’这个词大家都懂,但‘宣读员’这个词甚至在词典中都找不到。我不知道你死了以后是否还能继续得到信息,但世界上发生了不少变化。谁都不需要别人在教堂前的广场上对着他的耳朵大喊,因为大家都能读报纸、听广播、看电视。如果你在法国的罗克迪里连上网络,你都可以知道是否有人在孟买撒尿。所以,你好好想想吧!”
“你真的把我当作老傻瓜了?”
“我只不过是告诉你一个事实,仅此而已。现在轮到我了。”
“你放下舵了,我可怜的若斯。重新拿起来。你没怎么明白我说的话。”
若斯抬起头,茫然地看着曾曾祖父的身影,他从酒吧的凳子上下来,还摆着架子。阿尔·巴努尔在他那个时代算得上是个高个子,确实很像个粗人。
“宣读员,”前辈把手放在柜台上,有力地说,“就是生活。别对我说谁都不明白这个词的意思,更不要说词典上也没有这个词,或者说勒盖恩家族的人堕落了,不配再当宣读员。生活啊!”
“可怜的老傻瓜。”若斯一边目送着他离开,一边轻声说,“可怜的老嗦鬼。”
他把酒杯重新放在柜台上,冲着前辈走的方向又大叫了一声。
“不管怎么说,我没有叫你!”
“得了,别闹了!”侍者拉住他的胳膊,“别再发疯了,你妨碍大家了。”
“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