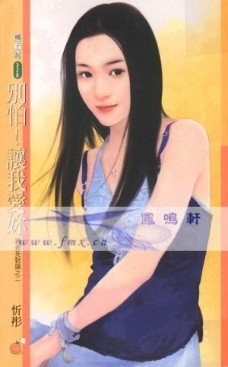我爱你乌般头发雪个肉-第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何必如此绝情?
他不懂她的强硬。
一个妓女,穷到没有爱情,那么她要人格尊严,她没有骗人,没有蒙客,没有耍手段拐男人的心,一直都是买卖公平,倒是她对他,一度丢了心。
她现在再也不肯为他爱到尘中,她要回她的自尊!要回只有凭借刀才能要回的,狐假虎威的,可怜的,一个妓女的自尊。
呵,她不过还是欺骗自身。妓女何来自尊,就如妓女无权索要爱情。
她缓缓地站起了身,他抢身前进,因他看见她手里的刀,抛向了那琴。
如是……他喊道!他不能看着她毁了这千古名琴。
琴即是情。
弦断,可再换,琴毁,难再造。
这绿绮古琴,是他最初送她的礼物,她毁了这千古名琴,也就是铁了心,要埋葬了她曾经付在他身上的一片深情。
谁说他不爱?难得有这样刚烈,用情之深的女人,不是不爱,只是没爱到为她违了礼教,背负骂名。
期望她一生不嫁,只爱他一人。
好自私的男人心!
迟了,慢了, 他眼睁睁地看着刀刃没入琴木,刀柄摇晃如风。
深入三寸,插在他心!
痛!
一旦让她看清,她从来就是爱恨分明,不肯中庸。
他的眼里溢出不舍的泪影。六年呵,六年,虽不可娶,但这爱也不该以这样的方式告终。那么多,那么多风花雪月的日子,割了,舍了,他也连皮带肉,不能不痛。
她看不得他哭,忙忙走出船舱,怕自己软了心。嘱船夫快快把舟摇往岸边,陈先生要走。
陈先生,陈先生,再也不是她亲亲热热的子龙。
那两盏灯笼,那两盏书了蘅芜二字的灯笼,红,一如她心,生生的撕裂,一半挂左,一半挂右。映照的河水,也滴了血,印了红,裂着伤悲的艳渍,提醒着她,爱不在,情已死,陈子龙这个名字,从今而后,不过是一个曾经的恩客的名字。
她立在舟首,衣袂飞扬,不肯回到舱中。
她怕看到他的伤心。
漆金的船,漆金的爱情,终有一天都会剥落,真相裸露,暴尸荒野,人生伶仃。
爱了那么久的人,都靠不住,她没有依靠。
只有靠自身。
送他上岸,含笑道别,礼貌温存,陈先生走好。
说着,亲手摘下那两盏灯笼,他送的字,还给他,从此不要看到,让抱琴和船夫提着,一左一右送行。
断个干净。
夜色如兽,全数吞噬了他的背影,那么那么熟悉的,从今而后,再也不是她心里居住了数载的男人。
十六岁爱上他,二十二岁别了他,他是她青春的证人,他是她最初最后的爱人。
反复的喃喃,子龙,子龙……
不知过了多少时辰。
抱琴回来,递她帕子,姐姐……
这个时候,她才晓得,她的泪早已成河,默默湿了春衫袖,而她却不知道自己在哭!
那夜以后,她明白现世对一个妓女的法则,那便是如若穷到没有爱,有名也好。如若穷到没有名,有钱更好。
总得找一样深深的攥在手中,才能立身。
得有实际的依靠。
找一个男人,比得过陈子龙,胜得了陈子龙。如果无陈子龙的青春,那么就要赢得过陈子龙的钱财,如果没有赢得过陈子龙的钱财,那么就要赢得过陈子龙的名声。
谁能赢得过陈子龙?
第二章
强将手下无弱兵
钱谦益,他有才有势有名,惟一的缺憾是——他已是一个五十八岁的老翁。
可老,也有老的好。
没有谁有力量阻碍一位老人的决定。
她累了,倦了,需要依靠。而他正是她要找的人。
她熟悉他的生平。
这老翁,江东世家之弟,家财颇丰。他生于万历十年,幼时即有文名。25岁中举,28岁中进士,29岁为探花。因诗文名盛,执文坛牛耳,为当世大儒,属东林党人。
他宦海几度,浮浮沉沉,春风得意时官拜礼部侍郎。却于崇祯十一年,因文人狂狷,不适官场斗争,遭人诬陷,处于下风,削去职位,现居老家常熟郊外归隐。
更重要的是,从年轻时起,他在江湖上便赢得“风流元帅”的戏称,为人风雅,生性旷达,豪气干云,是真个的东林浪子,从来不负虚名。
他还记得她吗?
但愿记得,那样更好。
她和他曾有一面之缘,两年前,在杭州西湖。当时他刚刚官场失意,而她正遣舟吴越,结交名士文人。
他是一位和蔼旷达的老人。
既然旷达,不知可有容纳一个妓女余生的心胸?
廉颇老矣,尚能爱否?
她得试上一试,赌上一赌 ,为了自己的后半生。
从春天和陈子龙别过,她闭门谢客,熟读了钱谦益的所有诗文,为此次拜访奠定行程。她不能掉以轻心,让他看轻。
这是个冷冬。
她认为是拜访他的最佳时辰,夏秋天气,以钱谦益的名声,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半野堂门前,访客必然甚众,她去,也没有多少时间属于她一个人。
她需要时间,需要只属于她一个人的时间,来攻掠,猎杀这位老人的心。
冬日冷清。
重新漆过的蘅芜舟在江南常熟的湖面华丽独行,快了,到了。船至渡口,三三两两的路人不由的打量着这不同寻常的小舟。
上得岸来,遇一路人,锦衣华服的公子哥,玉面长身,见他上岸,竟然把疾奔的马儿勒住,停了。
她一笑,抱拳问,公子可晓得半野堂如何走?
那公子哥给她热心指点路径,指点完不但不走,还语言亲昵,要亲送她至半野堂,她心底大叫不好,遇到狎童的男人,忙忙冷淡,谢过,向半野堂挺进。没走多久,那宅子就依山傍水的呈在眼中。
越走越近。
天气不知什么时候阴晦下来,细细密密的雪,下了起来,不大,却冷,尽数落在她的衣衫肩头。落在她心。
雪是雨魂,未来莫测,白蝶纷纷,向西?向东?一如命运。
她无法知道。但得一拼。
既来之,则安之,手指轻轻叩门。
一下,两下,她叩的那是一扇朱门,她叩的是她的下半生!
“吱呀”一声,门开了,探出了一张童子脸,眉毛粗重,一脸不耐,看着他说,我家主人近日闭门研学,不面客。
显是见烦了访者,一见陌生人的脸,就知是慕名而来叨饶的,先就不客气的打发掉。
她轻轻一笑,从袖里抽出一封拜帖,递予他,且上面压了几钱碎银。
不言自明,是贿赂,求他通报一声。
那童子眉心凝结一处,睇他一眼,眼里有了愤怒,把拜贴随手一抖,碎银一粒一粒落地,七零八落。
雪触地即化,它化不了,是明显的责备,无言的指责,他嫌来客低估了他的人品。
钱,有时候送不对,是一种侮辱。
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儿,他岂是银钱可以收买的?
呵,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强将手下无弱兵,半野堂主人的童子也清高如厮。她不生气,她来对了。
不是恶俗人家可以调教出来的。
于是顺水推舟,击掌笑赞,好,好,半野堂主培养出的好风骨!
好风骨?
第二章
闻所未闻的另类风流
这声音怎么如此温婉,不若男声呢?且当下还这样赞他,可见来者气度不凡,不是一般人物。
那童子忙细细打量过去,只见眼前人物眉目如画,身形娇小。难道……是个女子?
噫,不好!主人莫不是主人的老相好找上门了?忙低头看了看拜帖,拜帖上是几个隽永的字:晚生柳儒士叩拜半野堂主人。
柳儒士?没听过这个名,但敢自称儒士,想来身份不低,他不能慢怠了。于是立马客气起来,笑说一句,不好意思。开了门,转了身,引了路,带她进了客厅,请她等着。
她立身四顾,客厅里皆是古玩字画,她知道钱谦益一向收藏甚丰。
正仰首赏析,身后传来稳健的脚步声。
慢慢转身,不肯差了毫厘半分,一举一动,都应美丽动人。要靠这些兑换日后人生。
他来了。
是老人的脚步,平稳缓慢,不焦不躁。
而她嫣然回头,深深一揖,低头俯首,抱拳一握,举止态度一连串天然珍珠般,光辉灼灼,粒粒圆润。晚生冒昧打扰,请钱老先生见谅。
他站定,惊绝,心下轰鸣。此系何人?如此蜂腰猿背,鹤势螂行,自有一种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另类风流。大有超拔脱俗,放达不羁的竹林七贤的君子风。
柳儒士,柳儒士,不曾交往过这么一个人。
可是文坛后起之秀?
心下一惊,面上却不肯迟了礼仪,他毕竟是五十多岁的老人,深得稳重意味,伸手轻轻一扶,柳贤弟大驾光临,有失远迎。
手与手胶在一处。
黑与白,老与少,男人与女人!
没有男人会长一双这样纤长俊秀柔若无骨的手。他的心一时不知滑落至哪里,不知该放开还是退后。
她一定是一位女子!
怪不得男儿装,女儿态,万般难言的旖旎风度。
她抬起了头,眼里波光流转,诗经一般,风雅颂,赋比兴,种种手法反复重叠 ,念唱的不过是送给他的四个字:敬重爱慕。
男人需要女人的敬重爱慕,女人的敬重爱慕是男人生活的养分,他们靠这个立身于世。霸王死,不过乌江,不仅仅因为兵败,还因为他再也看不到虞姬眼里自身的绝世威武。
她只要——他看到他在她眼里也是一个传奇故事。
她要依靠了他的!
这位老人,肌肤虽老,眉目却不肯老去,眼光火星四射,看定她,握紧她,喜悦万般,眉毛上挑,说,我……认出你来了,桃花得气美人中,柳如是!
他记得,桃花得气美人中,是她做的诗句,他记得!
……
第二章
我没有做古典梦的嗜好
小姐,请问要不要来一杯果汁?甜美的声音,现代的装束。
我做梦了么?眼前是一位空姐,那位日本老人早放开了我的手,替我取了一杯,递过来了。
如是,给你,他说。
天,谁是柳如是?他还这样叫我,我却万万不敢再碰他的手了,我没有做古典梦的嗜好的。
捻了指,轻轻地接过,不肯再次发生身体接触;好似古典女子,男女授受不亲。呵,偏我开的是身体银行。自己也觉得故作姿态,好生厌恶。
于是调侃,山口先生,好像冰激凌喜欢别名,加了点水果就叫圣代。难道我看上去也像一支冰激凌吗?说着,拿了随身的小包,对镜一照。
他轻轻摇头,笑赞,你这个孩子,真是有趣。先不说你是不是如是,这个问题留给以后。我喜欢你,爱爱。
呵,是个聪明的老人,他明白我那话是再次拒绝否定。
爱爱?喜欢?
我心一动。可是真的喜欢?
爱爱这样的称呼,是我父亲的专利,那位遥远的中国农民。从小到大,只有他这样叫我,粗糙的手,粗糙的爱,他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常常困窘的摩擦着自己的双手,不知所措,爱爱,照顾好你弟弟。爱爱,爸没本事。爱爱,我们人穷,不要跟别人争……
可怎么能不争?不争,永无改观。永在底层。就算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不翻身,我的人生,可我弟弟将有另外不同的路,不同的光明。
正在发呆,山口牧斋又叫一句,爱爱。
爱爱!
声音低低,惊雷碾过,有一种液体邂逅而来,汹涌澎湃,四面八方,心脏深处,邂逅而来。
很久以来,没人这么怜爱的叫过我了。爸爸,我那生身的父啊,此时此刻,他可是行在初秋的田野,粮食席地而坐,而他汗流浃背地款待,他是它们的主人,偶然的歇息里会不会想到他引以为傲的女儿,正在北上的路上,寻找生存隙缝?
嗯。我不由自主,应了一声,嗓子一哽,看着窗外。
山雨欲来。
我爱我的父亲。我、父亲、弟弟,我们三人相依为命。
妈妈过早的离弃,让我明白,哭,是一种奇怪的表情,没一点用,就如它的造型,空瞪着白茫茫的眼神,挂一滴白痴的液体,大大地把悲哀裸呈。
这位日本老人,他能触到我的心海。他的低唤,行在浅滩,一句唤声一个水印,轻轻的,轻轻的,一按,水汽氤氲。
他伸出了他黑瘦的手,老树一般,要托我脸,托一朵青春之花在他苍劲的枝间。他要迎接,要引我坐上他的枝头。承接悲哀。
不!
我慢慢地推开了他的手,给自己时间。我要笑容灿烂。虽然他是山口牧斋,我也不喜欢自己轻易的就在他的面前把心敞开。
日日面客,早学会了变脸,卖笑的人不能卖哭,哭,哭给谁看?没有几个人愿意开办同情这一项福利事业。山口先生,北京快到了。我把话题转换。
是的。他叹了口气,看我一眼。他明白他遇到一个谈笑风生,而心理上早已披盔穿甲,刀枪不入,外壳坚硬的人。
飞机着陆,人群鱼贯,候机大厅,弟弟西装革履的站在人群,给我招手。他高了,大了,城市生活令他洗尽了土粒尘埃,修长笔挺,人中龙凤。现在,他修名校硕士生,又不缺钱,身份自然不同,自然会有女子缩在他的臂弯,小鸟依人。
这还是我小时候一口一口喂他饭吃的弟弟吗?他都长大到有了爱情,我应该幸福满胸。
我真心的高兴起来,拉着行李箱,急急的向弟弟走去。越来越近,恍然,我看见一张典雅的脸,在弟弟身后,在人群里一闪。
贵子!
是她,她到来的好快!是迎接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