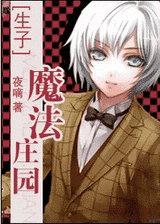庄园-第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叛了我们的感情?你走的时候怎么说的?你要我等你,我等了,可我等来了什么?庄恒你给我说,我等来了什么?!”我用双手圈住自己,试图让自己不再颤抖,试图让自己的脊梁挺起来,试图维持我最后的一份骄傲。
他似乎什么也顾不得了,急急得抢上来,“蕴茹,别这样。我和清珏不是你想得那个样子……………”
清珏?哈哈哈哈哈哈。原来从他口中听到另一个女人的名字是这样的感觉。撕裂的生痛,痛彻心肺。原来我苦苦等待的感情竟是如此荒唐,如此幼稚,如此可笑。
他的嘴巴不停的一开一合,我全然不知他到底说了什么,我只知道,我不要再在这里呆下去了,一秒钟都不要。我摸索着拉开门,跌跌撞撞的冲了出去,全然不顾身后庄恒的大喊,全然不顾旁人的惊呼。我只不停的向前奔着。
到得外面才发现,天不知何时竟下起了雨。呵呵,都说苍天有泪,可不是吗。我冲进雨中,仰起脸来,任凭雨水击打,湿透我的衣衫。我拼命的跑着,想要跑掉所有的心痛,跑掉已然跟了我太久的孤独和辛酸。庄恒焦急的大喊声越来越近,“蕴茹,你快回来。你要怨我,怪我都由你,你不要再折腾自己了。蕴茹………”
我不理会,径直冲进我的车里,看也不看的狠踩油门,发动。我万万没想到,这么晚了,这甚偏的路上居然还有行人,等我看到时,眼看着就要撞上了。说时迟那时快,我狠打了一把方向盘,避开了那人。可再也避不开路边的大树,眼睁睁的撞了上去,前额磕在了方向盘上。
“蕴茹!”一声撕心裂肺的吼声传来,我只模糊间,看到瓢泼的雨中,一把黑伞被风连连刮了好几个跟头,庄恒奔到车前。他一把拉开车门,那一瞬间,我在他的脸上看到了真真切切的恐惧和慌乱;那一瞬间,我在他的眼中读出了珍爱;那一瞬间,我的心居然感到了一阵欢欣。
他把我固定在靠背上,小心翼翼的抚着我的脸颊,我的额发,嘴里乱七八糟的安慰着,“乖,不怕啊,不会有事的。告诉我,有没有哪里不舒服,什么地方还疼?乖乖,别怕,我们这就去医院。乖,不哭啊,坚持住,疼得厉害吗?”。
庄绮家里的三、四个佣人们也跟了过来。一个连忙抢上来给他撑着伞。庄恒急吼道,“去叫司机开车,我们不等急诊车了,这就上医院去。”一个佣人答应着跑走了。
我用力扣了扣他握着我的手的掌心,他立时俯身看我。我勉强摇了摇头,“没事,不用去医院。磕破了一点而已。”他拧起眉,依稀仍是当初对着胡搅蛮缠时的我的样子,放柔了声音道,“听话,跟我去医院作个详细检查。”
这个人真是的,我们都这么一身落汤鸡般的狼狈样,我还伤了额头,就这么跑到医院,给媒体知道了,还不定怎么大做文章呢。
正要说话,司机把车开了过来,庄恒轻柔的抱起我,坐进了后座,然后吩咐司机,“回九龙塘我的公寓。”我惊讶的抬头看他,他点点头说道,“你想的也有道理。先去我那里,我们再作打算。”
车子载着我们驶向九龙塘庄恒的寓所。一路上,他一手紧紧地将我搂在怀里,一手拿了佣人刚刚递上的毛巾,一边拭着我一头一脸的雨水,一边小心翼翼的查看着我额上的伤处。我这才感觉到伤口一丝丝的生疼,不禁的倒吸口冷气。他惊觉,连连的安慰着,又像哄孩子般朝着我的伤口处吹着气,还不停的说,“乖,呼呼就不疼了,不疼了……………”
我们的衣服全都是湿的,还有雨水顺着一点点滴下,冰凉冰凉的,却又死死的贴在一起。我靠在他怀里,不动,不作声,听着他低低的劝哄,带着满心的困惑,迷茫,心酸,甜蜜,留恋,无以自处。早已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流到嘴边,苦苦的,咸咸的。
车停在他楼下,他冲司机交代道,“告诉你们太太不用担心,我晚一点再给她电话。”然后便不由分说,抱了我出来。门口坐着的那个管理员王伯,见了我们这个样子,有一瞬间掩不住的惊诧,然后便是笑得极其暧昧隐晦,意味深长,“庄先生,施小姐,回来了啊。”我毕竟脸嫩,微微害羞的往庄恒怀里缩了缩,庄恒倒是波澜不惊的样子,冲他稍一点头,就抱着我进电梯去了。天知道王伯的脑子里将会勾勒出怎样一幅情景,脱不了男欢女爱,浓情蜜意就是了。现在怕是全天下都觉得我们早已是顺理成章的一对儿,可讽刺的是,独独是当事人的我,弄不清我们这段情该何去何从。
进得门去,按亮了玄关的灯,他方才放我下来,冲我道,“我去放水,你好好泡个澡,这一身的湿衣服可再穿不得了。”说罢便径自往浴室去了。我下意识的环视这间房子,是熟得不能再熟了。以宝蓝和深紫为主色调,简洁而大气。就是四周挂着的小风铃,摆着的绒娃娃,很有点显得不伦不类,那是我的“杰作”了。记得以前上来的时候,总嚷嚷着说,这屋子太空旷肃冷了,要给它添上活力。于是便时不时的弄些小玩意儿,东一处,西一处的瞎摆。每每庄恒见了,都止不住地皱眉,却也由得我去摆弄,倒也没有要把它们除之后快就是了。庄恒不在这半年,我起先还上来坐坐,看看。可实在有太多的属于我俩的回忆,冷不丁的就从某个角落了蹦出来,甜蜜得让我心疼,让我不敢再呆下去,落荒而逃。
“蕴茹,水放好了,快去吧。”庄恒打断了我的思量。他走近我,又拿了个止血贴,轻轻地给我占上。“先贴上这个,省得你一会儿又碰湿了。”
我愣愣的点头,自去浴室。泡在温热的水里,让暖暖的水一点点将满身的寒意逼走。冷了太久了,我实在是累了,乏了,也实在是太需要温暖牢牢的将我包围着了。
半晌,正打算起身,才想起我在这里可是没有换洗的衣服啊。我跟庄恒恋爱这近三年,这里虽然是来了无数次,可从来没有留在这里过过夜。我有我的矜持,庄恒有他的坚持。他要我堂堂正正的在新婚之夜做他的新娘子,我亦然。
这下可好了。正急得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庄恒的声音适时响起,“蕴茹,我刚下去买了些你可能需要的东西,给你放在门口了。”说罢又离开了。
我探着身子稍稍拉开门,把门口椅子上的东西拿了进来。嗬,还挺齐全的,大浴巾,贴身小衣裤,还有一件长长的大睡衣,应该是庄恒自己的了。我赶快穿好,梳了梳湿漉漉的头发,又看看额上的小伤口,还好,不大,不至于弄得破相。(:。。)整 理完,便走了出去。
客厅里,庄恒正背着我,正对着一副放大成油画一般的相片,负手而立。我顺着他的视线看去,相片里,我偎在他怀里,笑得灿烂;照片里,他拥着我,笑得满足;我们的身后是浪潮滚滚,海天一色。
第13章
多美的一段岁月,多美的一份情缘,多美的曾经拥有。美的似梦似幻却又真真正正。难道就这么碎了,断了?难道就这么放手,逝去?
心里一阵翻滚的疼,我不再看那相片,转而把目光移到庄恒身上。这人,还穿着刚刚在雨里淋了的衣服,湿湿的就那么贴在身上。光知道说我,自己就不怕凉着?刚想出声要他去换洗,突然,我看到了他紧贴着脊背的淡蓝衬衫上一道隐隐透着一道血红,我眨了眨眼睛,再看。没错,像是什么伤口崩裂了,渗出的血迹一般。他身上有伤?我不禁惊呼出声,跑上前去。他此时方回过神来,忙要转身,却被我喝住了。“你别动,让我看看。你流血了。”
“没有,蕴如,没有的事儿。你快点再披件外衣去,夜里还是凉的很,刚刚才淋过的…………………”他掩饰着想把我固定在他的身前。
“庄恒,你到底还要瞒我多少事?让我看看。”我怒了。明明身上带着伤,这都不让我知道,我们是真生疏到了互无瓜葛的地步了还是怎么的。要真是这样,我撞车时他何必那般紧张;又何必站在我们的相片前缅怀那些曾经的过去?
他看我急了,连声说,“好好,你看,你看,真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轻轻掀起他的衬衣,露出他的背部。没什么大不了?可展现在我面前的又是什么?一道道交错的鞭痕,有深有浅。有的已然结痂,淡去;有的依然发红,未愈;还有两道很深的鞭伤,看样子虽然日子已经不浅了,似乎是好了又裂了,还隐隐的渗着血迹。我难以置信的看着这些狰狞的伤痕,用牙齿咬着自己的手指,泪早已流下。
他到底受了多少罪?吃了多少苦头?
他惊觉我的不对,赶快放下衣服转身,手忙脚乱的给我擦着泪,“好了,蕴如,都没事儿了。不哭了,乖,不哭了。”说着,牵了我的手,进了房间。他让我坐在床上,跟我说,“来,把被子盖上。你好好的睡一觉。今天你太累了。”我点了头,纵我有千万问题,也得等他让先梳洗一下。他万不能穿着湿衣服了呆下去了,身上的伤也要赶紧处理。看我点头躺下,他方才走了出去。
相处这一场,他绝对很清楚,我不可能也什么不想,不问的就这么睡去。果然,没过多久,他便一身干净清爽的走了进来。看我已坐起身来等着,便先道,“姐姐已经给往你家打了电话的,就说她留你陪她住一晚。你父母并未说什么。”
我嗯了一声,直直的对上他的眼睛,一字一句的道“庄恒,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总还有这个知道的权利吧。”
他也坐到床边直直的回盯着我,灼灼的目光中包含了太多的情绪,不舍,怜惜,不甘,不忍,矛盾,痛苦………………这一切编织交杂,翻腾奔涌。我有一瞬间的陷入和迷失,看不到源头,也找不到出口。下意识的去抓他的手,双手交叠处,冰凉刺骨。他蓦的一震,缓缓但用力的回握了我的,仿佛终于做了什么决定一般,舒了口气,闭上了眼。再睁开时,眸光里已然平静无波,清明一片。他冲我笑了笑,拍了拍我的手背,又给我把搭在身上的薄被理理好,温然道,“蕴如,听个故事好吗。”
他看我笑了,也明白是怎么回事儿。有些窘然的摸了摸鼻子,随即正色。半年的时光并没有让他讲故事的水平有什么飞跃的进步,但这是他的故事,主人公是他自己。随着他娓娓的讲述,我总算是明白了当日发生了什么。
“要返港前的那个晚上,我遇到了一位熟人。他说他暂时回不来,要我带点东西回来给他的……………,他的朋友。我答应了,他交给我一个小皮箱子。我只觉得提在手里还挺重的,也没有在意。第二天中午过关的时候,执岗的那人看了好几遍我的证件,又盯着我来回的打量,随后便示意我到一边站着。很快,来了一队带着徽章的人,拿了我的行李,又让我跟着他们走。我心知不对劲了,可实在也弄不清楚出了什么问题。当时同行的只有我一个人,我刚要大喊,后背就有东西顶了上来,我知道,是枪。他们把我押进了一间小屋子里,门一关上,便撬开我所有的行李,我才清清楚楚的看到,那个人托我带的小皮箱里全是金条,银币,和成包成包的零部件。我彻底的傻了,我知道那是多大的罪。他们把我按在地上,我挣扎着,他们又用手铐扣住了我。当中一个当头的阴侧侧的说,“这次的线人还真是不错。精彩的窝里反。”我震惊中隐约有些明白,也不想再辩解什么。后来他们蒙着我的头,把我扔进了另一处暗室一般地方,要我在一张认罪书上画押签字,我抵死不从。开头几天,我还给了许多电话号码给他们,希望他们帮着联系外面的朋友和香港这边,可都没有回音。渐渐他们的耐性也没了,便动上了鞭子,照三餐打。每次打完都扔下一句,“人证物证都全了,你趁早坦白。争取宽大处理。不然的话,有得苦头你吃的。”我虽绝望,可也知道这一个押画下去,我这一辈子也算彻底完了,所以我只能撑着。那间暗室阴冷之极,伤口又感染,我发起高烧。迷迷糊糊中,听到有人说,“看看人死没死,还有气的话,上面有交待,把他弄出去算了。”就这样,我被拖到一个大门外面,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庄恒讲着这段遭遇时,一直很平静,所有的痛苦屈辱他都轻描淡写的一笔带过了。可他身上那一道道至今仍未消退的鞭痕已是铁一般的证明了。我没有问那熟人是谁,早已认定了是黎隆源。所以庄恒才会百般维护,那样的情况下都不肯申辩一句。也正因为这样,我可以想象他的心,伤得有多重。我死死的攥着他的手,纵然明明知道事情都已过去,他人就在眼前了,但心里全是会失去他的恐惧。原来,他真的这么近的和死亡擦肩而过;原来,我真的很可能永远也等不到他。在那一刻,我只有一个念头,我要抓住他,我不能失去他。他安抚地笑着,目光中尽是了然。
很久之后,我轻轻问,“然后呢?”我真的很傻,很痴。明明已经知道然后便是美人救英雄的浪漫了,可我还是问了。期待什么?我自己都不知道了。庄恒犹疑的看着我,怕我再做出什么冲动的事情来。我毫不躲闪的回看他,既然我们谁都避不开这既成的事实,索性摊开了也好。我会作何反应,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承受不起再次失去面前的这个男人。
其实接下来的事情,一点也不离奇,顺理成章的很。那个叫骆清珏的女子救了他。请了大夫给他治伤,又端汤送药的贴身照顾了他几个月,直至送他返港。按说像庄恒这样被边检查到过的人,是不可能再被允许回到香港的。可能是凭了几分运气,再加上庄恒由始自终都没有认过罪,证件什么的也没被扣下,骆清珏又打点了几个关节,这才使得庄恒得以重新归来。
无可否认,庄恒欠了这个叫骆清珏的女人莫大的恩情。时也;命也!
我自己都不知道是该感谢天降贵人,佑得庄恒大难不死;还是应该叹息天意弄人,在庄恒最需要人照顾的时候,在他身边的,不是我。
“她人呢?”我问。庄恒苦笑,“不知道。安排好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