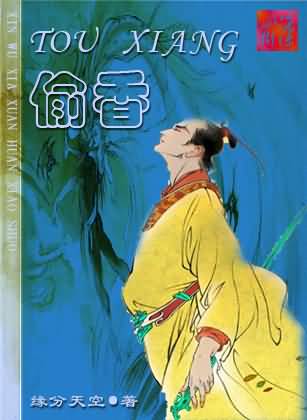星雨兰花香-第1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能力从哪里来?大学吗!好了不要争辩了,就为了我们三年的拼搏,为了父母,为了我,好吧……”
若兰那种冷峻的眼神,从来没有出现过。我想让她明天高考有个好心情,又给她讲的那些酸酸甜甜搞笑的往事。
学校为了高考前改善伙食,打算统一订餐,结果整得一个人拿一饭盆连打三回饭,交了钱的饿着肚子骂娘,没交钱的吃完抬脚走人,比当年的白狗子都气势。结果食堂门口坐了一票绝食的,吃饱饭的也跟那坐着看热闹。校长一看这小阵仗,吓得直道歉,直接把集体订餐取消了,这顿学校请!这顿学校请!这才摆平了。老头擦了把汗赶紧回去量体温了,这老头活得还真用心。
放假几天来,学校的气氛一直就活跃着,晚上三楼丫们直接可窗户上放了一大音箱,把《国际歌》放的山响。大伙听了跃跃欲试,直接就想把苏维埃的红旗插在教学楼顶,感觉拿下高考就跟当年斯大林猛攻柏林一样。
晚上哥几个打完牌,侃完山,横着就进了宿舍,一看子瑜正在吃药,眉毛紧锁着,脸色暗黄里透着惨白,套身清朝的僵尸装,给点灯光,直接能去《僵尸先生》里跑龙套。后来一看他吃了几片退烧药顺便加了几片安眠的,把哥几个吓坏了。可他说,没事,我头晕眼花,恶心,想睡个好觉,第二天有精神。感觉心里挺恐慌的,可能是看电视剧多了,一听安眠药就渗的慌。
晚上丫们搞得都挺凝重,说话都特收敛,洗漱回来才九点多,一看那几位静悄悄的关灯都不动了。我躺床上,就一直翻过来倒过去,一直提醒自己,我就是一高唱凯歌的大尾巴狼,我就是一玉树临风的小喇叭花,我还在乎什么?...后来不管用,数到一千多只绵羊,感觉哥几个都在数,我笑了笑想把哥几个叫起来打开灯一块数。犹豫了一下继续自己数了。
子瑜就跟喝了仙人醉似的,有潜力睡20年。哥几个看着子瑜打着鼾,流着汗,口水都快流出来了。敢情到这时候,睡觉都有人羡慕。
于是一直闭着眼骗自己:我是披着羊皮的小白狼,我睡得比谁都香。结果一宿下来,自己对自己什么对白都记得一清二楚,透过窗子感觉外边亮了,贼也似的爬了起来。幸亏受过高等教育,要不然培养成一贼都有可能,夜里怎么就那么精神。
到楼外透了口气,洗漱了一下,想想小若兰,感慨了一会,周围出现了人烟。想来感慨的时间也不算短,一进宿舍,哥几个都起来了,只是子瑜还在沉沉的睡,都有热气冒出来,就跟张三丰闭关似的。可人家是内力催的,这哥哥是发烧烧的。我们能做的也只有帮忙偷偷的买药,帮忙瞒住学校。那种无奈,又跟无力回天那词挂钩了。
老班定的七点半集合,喊子瑜说什么也不起,后来哥几个一块喊,一边推一边说考试了,这便蹭得起来了,直接奔外边跑,没站稳直接摔地上了。一摸头,烫得跟小熨斗似的。我们几个看着实在不行,打算跟老班说了。子瑜死也不肯。
老班鼓了阵士气,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感觉,我甩了甩头发,鼓励了一下若兰,钢钢的就冲进考场了。哥几个谁也没分在一场,只是子瑜分在我的隔壁25场。
我验了证件,交了半月的体温记录表,量了体温才算过了关,后来隔壁25场吵起来了,丫老师也不让出去看热闹。整得我们干听着着急,好像是发现一疑似。纳闷了好一阵,题就发下来了,看了一会,狞笑了一下,居然哪道都有思路,算了一会,我又苦笑起来,哪道都没把握。监考的老娘子见我的表情,一直给我递面巾纸。我想起八路军,我想跟她说,老乡,等打赢了鬼子就有好日子过了。可现在自身都难保,哪有余力去照顾老乡。
总算出了考场,丫们撒了花似的骂,有几搁戏台上能拈兰花指的小女生直接蹲墙角哭,哭得那叫一伤心。见这小场面我心里稍稍爽了点,想来也够损的,减少自己的痛苦居然是建立在别人更痛苦上。
一出门口,大雨哗哗的,其实我心里挺平静,可能是还没来得及考虑应该有多伤心。
集合点临时换到餐厅里,老班凝重的说,子瑜被送去了隔离场,考到一半旧病复发,送进了医院抢救。接下来丫狠狠地批了我们,说我们隐瞒病情就跟纵容朝核发展一样危险。想想后果这么严重,再想想做的那个幼稚的决定,想想子瑜可能…心里特恐慌,总感觉自己是一铁皮小坦克,这回下边直接放了一炸药包,拽也拽不起来了,只想哭。
我们一块哥几个就要向医院冲,老班拦住了,说考试完才可以,一来是非典闹得最凶的时候,二来高考又这么紧张。
考语文还算有点人性,写了一洋洋洒洒的小文章,给自己心里垫了点底。感觉那就是整个高考再继续下去的精神支柱。考完这场,整夜的疲倦袭上了头,吃了俩馒头俩鸡腿就回去睡了。
…只见子瑜罩在氧气罩下面,眼睛大大的瞪着,红红的全是血丝,他就这样直直的望着天一动不动,望着…望着…
心电图从屏幕上一波一波不分彼此的掠过,我站在旁边,无所适从,心乱如麻。突然子瑜头一扭,眼睛瞪得更大了,心电图停止了波动。
啊…我吓得大叫,不知所措,我想跑出去叫人,却怎么也跑不动,子瑜那双可怖的大眼睛死死的盯着我。眨眼间从床上跳了起来,“诈尸啊…。”我嗓子都哑了,还没来得及逃脱就被子瑜卡住了脖子,“你还我若兰!为什么抢我若兰?…”…
我吓得大叫着坐起来,感觉周围全是鬼,等我揉揉眼睛,原来是场梦,心还在突突直跳,脸上呼呼的出汗。楚超丫几个跟看耍猴似的一直在旁边看我。丫几个说我撞鬼了,我抖了一下,打了个寒颤,跑到水房去了。把丫几个吓坏了。感觉和若兰又有一种隔世的厚障壁了。
第二天,题出得还是很流氓,暴雨仍然如注的下着,麻木中把所有题做完了,那种怅然若失的失落无法形容,想着三年的光阴,想着就要离开的复兴,想着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我从门口摔了一跤,原来下台阶时忘了,我滚下几阶台阶跌进下边一水沟里,磕了嘴一下,感觉浑身无力,真想躺在那歇会,一看周围人都在看,挣扎着爬了起来,这次也没感觉多丢人了。
雨已经停了,看着来来往往搬迁回家的人群,我木木的望着,直到那个白色的小身影出现时,才发现我是在等着若兰。她赶到我身边焦急地问,“你和别人打架啦?”意识到自己的造型不对,摸了摸嘴角的血,我笑了笑,我说,“没有啊,若兰,即使打假,我也要为你打,命我都搭上。”若兰的美目擎着珍珠。我含笑摸去她脸上的泪痕,感觉责任重大,那就是给她撑起一片天。
若兰离家远,先回了家,我跟楚超,范建还几个女生就直接去医院了。等我们感到医院时,看到子瑜的亲属家人都在,有抽泣的,有急得乱转的,另外一些商量对策。子瑜的父亲坐在候诊室里,整个身子蜷在长椅上,两支粗大的手深深嵌入头发里,眼镜低低的挂在鼻梁上,不时的叹着气…他应该是选择了一个成熟稳重男人表达悲痛的最佳方式。
我们刚要前去问个究竟,子瑜的妈妈从病房冲了出来:“若兰…谁…你们哪一个是若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