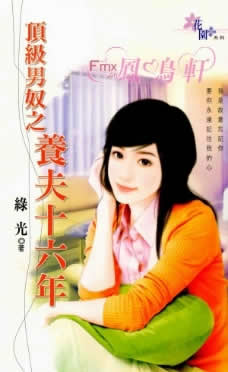养夫-第2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你要是洗的香喷喷的,再把这一头飘逸的乱发束好,外加如果你有一张像她爹一样的美颜的话,那么她就可以勉强原谅你!
裴金玉不喊也不哭,只用一双饱含嫌弃的眼睛将他凝望着。
乞丐正在纳闷,这孩子淡定的太不像孩子了。
那边裴天舒赶到,指树大呼:“我女儿要是少了根头发,老子也不杀你,就拔掉你身上所有的毛,还养着你,等你毛发张齐,再拔!同理,我女儿要是磕破了点儿皮,老子就打断你的胳膊,管接,接好了再打断。周而复始,始而复周。”
尼玛,这就是有杀爹的仇,也得报了!
那乞丐却“哈哈”大笑,腾出一只手指着树下的裴天舒道:“你小子,几年不见,怎么还是这般阴损!”
裴天舒愣了愣神,又走近几步,仔细瞧了瞧那乞丐。
他倒也配合,特地撩撩头发,露出了脸。
裴天舒:你TMD王八蛋,还知道回来啊!
怒吼:“林枞,给老子滚下来。”看老子会不会揍残了你。
林枞这个名字很是耳熟。
裴金玉一抖,忽地想起来,就是这个人千里追击,斩了卫单,却又不领功勋,云游而去。
一时间,还真是百感交集。
林枞抱着她跳下了树,才将她放在地上。
楚氏就飞奔上来,左右看看,确定无事,这才止住了眼泪。
林枞嘿嘿笑着对她行礼:“对不住了嫂嫂,我和侄女闹着玩哩!”
楚氏还在生气,碍于丈夫不好发作,白了他一眼,揽着女儿悻悻退走。
临走的时候,裴金玉又忍不住回头看了林枞一眼。
林枞见她看来,咧嘴一笑,又伸了伸手,示意要不要再抱抱。
裴金玉头疼不已,不是一般嫌弃地对他道:“你还是先洗干净吧!”
此话一出,林枞哭笑不得。
裴天舒却是笑声震天。
要说林枞此人,本是林青峦同族。却是同族不同命,从小便过的甚是凄惨。
先是母亡父丧命,再是叔婶夺产,且设计要灭口。
而后他杀叔斩婶,浪迹天涯。
流浪到武陵与裴天舒相识之时,也不过区区十八。
因着他矫勇善战被林青峦赏识,却又受着林氏其他族人的排挤。
裴天舒和颜学庆皆劝他,“不如你改名换姓!”毕竟顶着个杀神的名号,实在不雅。
他却是个无所谓的,只道自己行不改名坐不改姓。
端的是我杀之人皆该杀,与世人何干,又与族人何关!别人聒噪,我不理。别人指责,咱们拳头底下见真章。
有本事一起上啊!
这就是个比天还狂妄的人。
当然,这些过往并不是裴金玉能够完全知晓的,她不过是想起了卫单,和她同父同母的亲弟弟。
她一直都知道卫单和他们那个皇帝爹一样,并不是个好皇帝,却一向以为他是一个好弟弟。
可笑的是,他那个好弟弟居然打着让她隐姓埋名,深藏后宫的龌蹉心事。
还真是想起来就让人不寒而栗。
****
是夜,裴天舒与林枞喝酒畅聊。
与此同时,一个人喝酒的林青峦拆开了案几上的密信,上书两字——已回。
他将信投进了燃烧的炭盆中,转而将杯中之酒一饮而尽。
宝光忍不住相劝:“皇上,少饮暖身,多饮却是要伤身的。”
林青峦摆摆手,沉默不语。
天已初春,他所在之处却仍需燃烧炭盆鼎炉,他自己的身体他最清楚,他早就嗅到了泥土的腐败。
于是,他仓皇将裴天舒推上了高位,还借机除了庄宁问,又千辛万苦逼回了林枞,他为了林峻游顺利继位做完了他该做的所有事,这尘世之中还有什么是他留恋的呢?
他饮下杯中最后一滴苦酒,醉倒在这空荡的大殿之中。
远处仿佛传来了谁的娇笑声,也仿佛是有歌舞在升起。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金盆洗手止风雨。
不恋红尘,却难舍回忆。
每一段都有你。
年少初遇,常在我心。
多年不减你深情。
江山如画又怎能比拟。
你送我的风景。
柳下闻瑶琴,起舞和一曲。
仿佛映当年,翩若惊鸿影。
谁三言两语,撩拨了情意。
谁一颦一笑,摇曳了星云。
纸扇藏伏笔,玄机诗文里。
紫烟燃心语,留香候人寻。
史书列豪杰,功过有几许。
我今生何求——惟你!
元会六年,三月初一,元会帝林青峦薨,享年三十七岁。
作者有话要说:这个是许嵩和黄龄的《惊鸿一面》,用在这里觉得很符合皇上的心境,“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金盆洗手止风雨,不恋红尘,却难舍回忆,每一段都有你”然后是“史书列豪杰,功过有几许。我今生何求——惟你!”。
还有我觉得,皇帝一死,乃们都*了。
以下是惊鸿的歌词,调子也美,喜欢的可以去听听。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金盆洗手止风雨。
不恋红尘,却难舍回忆。
每一段都有你。
年少初遇,常在我心。
多年不减你深情。
江山如画又怎能比拟。
你送我的风景。
柳下闻瑶琴,起舞和一曲。
仿佛映当年,翩若惊鸿影。
谁三言两语,撩拨了情意。
谁一颦一笑,摇曳了星云。
纸扇藏伏笔,玄机诗文里。
紫烟燃心语,留香候人寻。
史书列豪杰,功过有几许。
我今生何求——惟你!
☆、第37第章 于
元会六年;三月初一;这日是个大晴天。
代王一如往常地去了武陵公主府上课。
只是到的时候;师兄弟们问他:“你怎么又来了?不是说皇上生病了!”
代王只觉莫名;回道:“大夫在呢,成王哥哥在呢,赵王哥哥也在呢!我在那儿没什么事啊!”
好吧!别指望代王能够明白什么叫做床前尽孝;关键是想给他解释清楚,还很浪费口水。
恰逢,赵夫子到了;众人即刻随水推舟呈鸟散状;各回各自的一亩三分地里准备聆听师训。
赵夫子姓赵名朝文,字旭初,号柳客先生,约莫有四十多岁,听说还做过国子学的掌佐博士,不知为何沦落民间,落魄到了租住在城内青楼妓院最多的柳怡巷路口,却是出其不意,越发的积累声名,成了一代豪放名士。
但凡名士,都是孤傲性情古怪的,且还是各有各的古怪,想来要是千篇一律也就不够格叫做名士了。
这位赵夫子的古怪之处,大抵就是一起床开始喝酒,一喝酒就开始作画,作完画开始题诗,关键他题的还都是艳诗。
不过,这位自打被裴天舒请了来,也还知道要给学生竖立一个良好的榜样,倒是有所收敛。
就是不知今日是不是哪个丫头犯了糊涂,难道是将酒水当成了漱口水?或者是老猫馋了,趁着忠义王不在,偷了酒腥。
反正赵夫子一进来,就连坐在最后面的谭中秀都只觉一股酒味扑面而来,闻都闻醉了。
于是,今日要习的课程那就是作画了。
赵夫子大笔一挥,耍了套醉把式,一幅雪中傲梅片刻即成。他忍了忍想要题诗的手,将笔一扔,要底下的学生临摹也行,即兴发挥也行,自己一转身便窝在长廊的木雕栏杆之上睡觉去了。
谭中秀和七里打赌,压上了半月的零花钱,赌赵夫子会从木雕栏杆上摔下来。
除了代王,剩下的几人就堵在窗口那专注地看着,愣是看了好几炷香的时间,别说摔下来了,就听赵夫子鼾声震天,却是稳如泰山一丝一毫都不曾动过。
谭中秀输光了零花钱,悻悻地走回座位,准备研磨作画。
路过代王这厢时,探头看了一眼,只见他掂着笔傻愣了半天,也不知道在想什么,遂问:“王爷,你这是……”
代王抬了头,憨憨地一笑:“我在想怎么画哩,到底是先画树,还是先画雪,或者先画花?”
谭中秀也就是写药方在行了,挠挠头道:“我也不知啊,要不你再想想!”
代王点点头,继续掂着笔,沉思不语。
其他的几人也就各回各位,开始同纸墨笔砚做斗争。
他们画了大约有半个时辰,画的快的,譬如七里和八骏,几近画完。
这时,不知因何缘由满脸通红的代王竟如茅塞顿开,同赵夫子那般挥笔就来,也是片刻的功夫便已画完。
八骏颇觉不可思议,嘴里叫道:“王爷,要是鬼画符的话,夫子会重罚的。”说着,伸头去看,顿时惊愕地无法言语。
原来傻子代王居然颇有作画天赋,他瞧着这一幅居然和赵夫子画的那幅不相上下。
众人也觉得惊奇,将代王围作中央,七嘴八舌地将他称赞。
代王没有回应,只是脸却越来越红,就连额上也滚下了豆大的汗珠。
还是谭中秀首先发觉他的不对,问他:“王爷,你可是哪里不太舒服?”探手一摸,他额间滚烫。
谭中秀赶紧让人散开,正欲为他把脉,他却“咣当”一下直接栽在了地上。
也就是这时,有人奔进了公主府,高声唤道:“皇帝驾崩,快快让公主换孝服进宫。”
****
自打皇帝病重,裴天舒已经连着好几日没有回过公主府了。
楚氏乍听皇帝驾崩的消息,愣了下神,便赶忙命众人全体服丧,又给裴金玉穿上了重孝服,这才拉着她出府上马车,亲自送她进宫。
当然,也顺道带着了昏迷不醒的代王,还有熟悉皇宫的裴筝,以备不时之需。
裴金玉到这时还不曾回神,怎么也不能相信林青峦——他死了。
不是都说祸害活千年的嘛!
等到进了宫,看着到处都挂着白灯和白帐,还有那跪在殿前哭嚎的百官,她的脑子一木,内里空白一片。
别人引着她做什么,她就跟着做什么,也顾不上去想转来转去她竟还是给林青峦服了丧。
然后就有太监来宣旨,说是皇帝临终前下的旨意,加封了裴金玉一个长公主之位,又以不忍为由,免了贤妃陪葬,却赐她道号静闲,且即时生效。
这是嫌弃她嫌弃到死了也不肯跟她睡的地步。那边的贤妃,哦不,静闲道长,“哭”昏了过去。
能不昏嘛!兜兜转转,尼玛又成了姑子。
小太监宣完了旨,也不管那边晕过去的贤妃,倒是特地很小声地对裴金玉说:“长公主,忠义王交代了,你要是累得慌了,直接晕倒就行。旁的已经打点好了,小的……春宝。”
裴金玉木讷着小脸,没什么反应,却待春宝前脚离开,她后脚——果真就“晕”了!
这就又乱作了一团,有人高呼:“不好了,长公主悲伤过度,昏过去了!”
有人掐她人中,她也忍着没有吭气。
就听那人说:“将长公主也送到东宫吧!御医这会儿都在东宫给代王医病呢。”
紧接着就是好一阵摇晃,等到有人将她抱在了床上,不远处传来的是颜学庆的声音,“好了,你们都散开吧,我来给长公主瞧瞧。”
感觉到他的手搭在了她的脉门,她睁了眼睛,正对上他那张黑黑的笑脸。
颜学庆笑着问:“饿不?”
裴金玉眨眨眼睛,摇摇头。
他又说:“那你就只管在这儿玩吧!”还不忘吐槽一句:“你爹他小心眼的很,他说他还没死呢,不许你给别人当孝女。”就是皇帝也不行啊!
这话倒是真像她爹说的,裴金玉想笑,咧了咧嘴。
在颜学庆看来,这笑有些敷衍,遂问:“心情不好?”
裴金玉想了想,点头。
“难过?”
“……不算是。”
“害怕?”
“并不。”
“那你是……”这小娘子还真是难琢磨!
颜学庆下意识抓了抓耳朵,转而一想,到处都有人在哭,就是再好的心情面对这些也是不那么美妙了。
他沉重一点头,又道:“那你就在这儿玩吧!”
说完觉得不对劲,这话他好像刚刚已经说过,挺不自在的又补充了一句:“这会儿没人顾得上来这儿!嗯……我得去看看代王了。”
颜学庆是豪放的“姐妹们”结交的多了,对着良家女子不大会说话,就是对着小娘子也是无话可说。
没话说就没话说吧,但办事还算靠谱。他临走的时候,特地拍了拍裴筝的肩膀,郑重交代:“好好伺候长公主,忠义王他……”很凶残的你的知道!
看着裴筝颔首称“是”,这才晃悠着离开。
代王那儿已经退了烧,他也得找个地方玩儿去!
待颜学庆一走,裴金玉就从床上翻坐起来,叫了一声裴筝道:“我想弹琴。”
既然故人已逝,情也罢,恨也罢,怨已消。
她想仅以一曲——送故人!
不多时,裴筝便寻来了琴。
她吩咐:“你去门外守着。”
裴筝退守门外,却是竖着耳朵听着房中的动静。却待琴声一起,忽地泪流满面,跪倒在房门之前。
这《方恨曲》乃一人所作,这世间也仅有一人会弹。
还是长公主初闻驸马起事之时,惆怅而作,还道:“只知你情深,却忘了你的姓氏。只道你悲苦,却忘了你的本事。到如今,方恨,方恨!情深三千,终抵不过权重位高!你我情意,也终不过是浮梦一场!”
裴筝如大梦初醒,喃喃自语:“怪不得,怪不得!”
一曲终了,裴筝伸手推门,以跪拜之态,进入房中。到了裴金玉跟前,又是重重叩首,泣道:“长公主,奴才……刘铮,是驸马,不,是林青峦替我改了容貌。”
裴金玉一怔,过了很长时间,才缓缓开口:“什么刘铮,你分明是裴筝。”
裴筝也不辩解,还是叩首:“是,奴才是裴筝。”
裴金玉冲他笑了笑,却不知为何,眼前一黑,这回是真的晕了过去。
****
高高的大殿之中,代王林錾自苏醒过来,就是痴痴傻傻地对着横梁不语。
御医都来了好几茬了,皆说无恙。
其实壶嘴心里清楚,他们觉得反正代王是傻的,就是再傻一些,又有什么关系呢!
可到底是贴身伺候了代王几年,伺候出了感情。
代王虽傻,对待他们这些侍从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