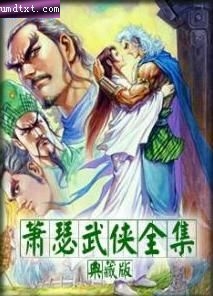书生的欲念-第2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尹焕冬告诉你的?”我直言无忌。
“不全是,只之前,我就听到我的老师常提起你的名字,宁城日报社的宋微澜,老师说你是他的得意门生。刘桓冬曾对我提起过,他曾与你共事过。我曾要求他带我去拜访你,可他一直在搪塞我,没想到,我们竟然这样见面了。”她友好地对我伸手:“我是夏菁菁。”
“你的老师是谁?”她的表现确实失常到令我莫名其妙,手,颤栗不停。
“我和你是校友,陆沛元是我的班主任,他教我们汉语写作。”她眉开眼笑地域我攀亲,完全忘了刚才我与尹焕冬之前的事情。
世界如此渺小,奇遇随时随地。我勉强地笑笑:“不好意思,打搅你们了。你们回去休息吧,时候不早了,我也该回去了。”
“你住哪里?”女孩还很善良地关心道。
“我是来公干的,有宾馆住。”我看看尹焕冬,很想求他送送我,又难以启齿。内心里一阵酸楚,眼泪不争气地掉下来。我低头说我走了,有种说不出的耻辱,抹掉眼泪,冲进夜色里,恨不得找一个隧道,钻进去,永远在这个有他们的世界消失。
深夜里,有阵雨来袭,月亮不知道什么时暗进云朵里,天空黑暗无底,没有一丝光线,没有一线希望,漆黑得要人窒息。海边有狂风呼啸,豆大的雨点凌乱而快速地降临于大地,噼里啪啦地打在我的身上,疼如刀绞。我没找地方躲雨,一口气跑到海边,整个人完全崩溃,无力地倒在沙滩上,失声痛哭。我打电话给何品,他很快就接了,我歇斯底里地吼:“你为什么要欺骗我,为什么!”
何品大概是睡下了,懵懵懂懂地问我怎么了。雨越来越大了,我在大雨中失去了理智:“我在哪里你别管,你先回答我,为什么连你都要隐瞒我,你们这群骗子!”何品知道大事不好,从床上腾起来:“微澜,你是不是见到尹焕冬了?”我没回答他的话,伤心地痛哭起来。
何品听出背景音的嘈杂,急忙追问:“微澜,你现在哪里?”
“我看到了他,不是一个人,假如我知道,我一定不会来,可是你从一开始就欺骗我,给我希望……”
微澜,你自己忘记了,我在最初警告过你。
可你为什么不说明!
“他,他是我的兄弟!你要我如何说?”何品为难而纠结,不停地叹气。
我的神经全崩溃了,哭得撕心裂肺的。何品在电话里大声喂喂喂,问我在哪里。我扔掉手机,朝大海里走,海里漆黑一片,能听见海浪的涌动,我浑身湿透了,也走不动了,突然头脑一阵空白,不知自己身在何方。
大劫大难(1)
这些事情,是后来杨彦告诉我的。
那天,马小爱接到医院的电话,粗声粗气地问你认识宋微澜么?马小爱不耐烦地说你谁啊?我们这里是兴宁派出所。马小爱立刻180°转变,收回原有的嚣张,哆哆嗦嗦地回话:“是,我是,请问找我有事么?”
宋微澜在人民第一医院,你去办理一下手续吧。
她怎么了?马小爱慌了,对方冷冷地说:“她还在昏迷当中,你可以先去看看她,再到公安局做登记。”马小爱说好好好,急忙抓着手机冲到张彼的办公室。张彼在打电话,马小爱不好插嘴,急得她在空中手舞足蹈。张彼看着她莫名其妙,急忙与对方挂断电话,转过脸不厌烦地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已经说很多次了,我在谈事情的时候不要来打搅,还有,在办公室里布市在家,要懂得分寸。”
马小爱心里窝火:“你当你是什么啊?我没有急事才懒得不找自来,我打内线还方便。”
张彼争不过她,虎着脸说有什么事情。
马小爱说,我刚刚接到派出所的电话,说微澜出事了,人现在医院。
张彼惊呆了,眼睛瞪得圆圆的:“这是真的?”马小爱说真不真我不知道,我这不来和你商量要不咱一起去打探,万一是真的呢?
张彼想了想,果断地说:“一定是真的,否则,派出所不会找到你,他们一定是从她的手机里找到你的电话的。”
马小爱着急了,像热锅上的蚂蚁:“既然是真的,咱就开去吧!”说着冲回自己的办公室拿包。
在医院里,他们俩问了医院的很多医生,都不知道谁是宋微澜。有人建议他们到住院部收银台去查,住院部的收银员问他们是不是早晨7点转院来的病人,她正在隔离室做重症监护。马小爱很纳闷,为什么是在隔离室?收银员干巴巴地说:“这个就不清楚了,入院的时候是派出所做的登记,医生要求住隔离病房。”张彼知道了方向转身就走,马小爱碎步小跑跟在他身后,两人同时出现在市医院的病毒隔离室外,透过大玻璃窗,看见隔离室里的人正安静地躺在狭窄的病床上吊点滴,额头上贴着导线,与床头的一台重症监护仪相连,仪器的显示屏上有根绿色的生命线在微弱地跳动着。
马小爱平生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场景,有些不知所措,情绪十分激动,双手拼命地敲玻璃窗,希望能把里面的人叫醒。张彼在旁边吼:“你闹什么啊!”她还傻乎乎地一边拍玻璃一边对张彼叫:“你快帮帮忙啊,把微澜叫醒,不然她会死的!”张彼无奈地摇头,把她拉过一旁,希望她能平静。马小爱却挣开他,继续蹭门拍窗户,张彼恼了:“你疯了?!”马小爱说:“她不能死,不能死,她是我唯一在宁城的朋友,是我的编辑,没有她我今后就完了!”值班女医生以为他们来闹事,走到他们跟前冷冰冰地说:“你们是宋微澜的亲属吗?她现在还处于昏迷状态,需要安静。”
大劫大难(2)
马小爱被“昏迷”两字吓得眼睛瞪直,以为自己听错了,再次确认:你再说一遍,昏迷?她犯了什么病?为什么会被独自关在这里治疗,还不让我们看望。
这时,一个身穿银白色隔离服的护士从他们身边身边绕过,拿着两瓶药走进了隔离室,马小爱想趁机跟进去,被女医生阻拦,马小爱的脾气就来了,气焰嚣张地嚷:“凭什么不给我进去,你们这样做也太过分了,竟然把一个病人给监禁起来,连亲属都不给靠近。”
医生严肃地说:“对不起,请你配合我们的工作,不让亲属接近是为您的安全着想,也是为全社会着想。”
马小爱不懂实情,还以为自己有理,得理不饶人:“为社会着想?我看你们是为自己的收入着想的吧,你告诉我,她躺在这里一天要烧掉多少钱?”
“小姐,我不想和你吵,请你尊重我们的工作。”值班医生尚是年轻,被惹得满腹委屈,眼泪几乎要掉下来。
“我当然尊重了,虽说你们医生是救死扶伤,但杀钱宰人总是不明不白,这要人很难不防一手。”
“你要是连救命的钱都付不起,那么可以转院,我们这里不是慈善机构!”值班医生气得脸色发青。
“呵!见了吧,只要一提钱,蝎子尾巴就翘起来了。”马小爱*地笑了笑,眼睛里充满邪气,有种越战越勇的斗气。眼见争执就此挑起,张彼把马小爱推到自己的身后,厉声道:“马小爱,你要注意分寸,这是医院,不是你家!”
马小爱转过脸不服气地说:“我说的没错,你看他们都心虚了。”
张彼板着脸,低声吼:“你要闹,等回去了我再陪你闹!”像被惊吓到的寄居蟹,立刻收敛安静。张彼转过脸,表情像太监一样的阴柔,连连对女医生解释:“不好意思,她向来是个急性子,说话不用大脑思考。你别和她计较,是我们做得不好,我很抱歉。微澜她究竟是得了什么病,非得住进这样的隔离病房?”
女医生压住委屈,说:“她高烧不止,肺部有明显水肿,我们担心是不是感染了禽流感病毒,所以先隔离治疗,生怕再有人被无辜感染。”
“禽流感”三个字像一道晴天霹雳,横过马小爱的意识里,她本能地跳出来,不问青红皂白地叫:“不可能!你别以为人家发烧了就说是有瘟疫,太胡闹了!若真这样,该隔离的人就多了,每天都有人感冒发烧,你们能有几间隔离房啊?我说呀,你们这样医生的医德真的要反省反省才行。”
女医生拿马小爱没办法,只当她是疯子撒泼,不以为然,她严肃地对张彼说:“你看这些数据,症状与禽流感病毒感染的极为相似,病人在兴市第一人民医院治疗了18个小时,症状不但不消失反而急速恶化,不得已才转入我院的,据说,她是在无人海边被发现的,海滩是海鸟常常出没的地方,我们不能放松警惕。而且,今年全球的疫情十分的令人不乐观,世界各地有关禽流感感染人类的报道,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那是那是,我们作为亲属一定配合。”张彼为马小爱的坏脾气感到颜面扫地,满嘴的赔不是。马小爱嘟着嘴不服气,张彼推了她一把:“还不给医生道歉?!”马小爱傲慢地说:“凭什么?等你到医院结账的时候就知道谁对谁错了!”
这时,医生忍不住说了:“对于她这样的病人,我们一定会严加治疗,假如是真的传染源的病人,我们都会对她进行无偿救治,毕竟这对我们的科研也有一定的帮助,对社会也是一种交代!”
“她有钱,你们会无偿么?再说,我也不希望我的好朋友被当成科研标本!我的意见是转院,你们医院医德太差了!”马小爱刁蛮地抗议,张彼拿她没办法,一把将她掖出去。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故人归来
下午,马小爱打电话去到日报社请病假,对事件不做任何包装,没心没肺地说宋微澜得禽流感,现在正被医院隔离,没法来上班了。闹得整个日报社到处诚惶诚恐,民心不安。
林编设法联系到马小爱,与她核对事件的真实性,那丫头像个没脑的单细胞生物,很肯定地说真是禽流感,你去看她要小心。林编一听又怕又着急,饭也不回家做,打电话交代丈夫带孩子到外面随便吃后,直奔市医院。
在市医院的隔离室前,有一个又高又瘦的男人面朝玻璃窗,深情哀伤。他头发微长,穿黑色瘦身T恤,咸菜绿多袋裤,双手插在前裤袋里,双肩微微隆起,形象佝偻萎缩。林编觉得面熟,探头去寻他的脸,他转头看见林编,友好地招呼:“你好。”
你好。你是……她的……林编有些语无伦次,指指里面,想确认他的身份。
“我是杨彦。她的师兄。”他小声说,生怕被蚊子听见似的,超级腼腆。
“哦,我想起来了,微澜是对我提起过你,还有,在一次作家笔会上也听见过你,就是些那什么小说来着?”林编拍拍脑门,又想到了其他:“对,就是那《爱情飞过布梯屯》,据说是在《人民文学》上发了,被我们的老会长赞得直流口水,说小小年纪就写出如此老道的作品,真可谓是我们省的青年才俊。”
杨彦谦虚地低头,笑得有点僵:“都是此去经年的事情了。”
“此去经年,用得好!呵呵,真是一副文化人的口吻。”林编笑得眉如弯月。
“别用文化人来称赞,我现在已经消受不起了,好久时间不搞小说创作了。”
“那现在都有啥高就啊?”
“做影视创作,准备回来开影视公司。”杨彦率性地说。
眼看人家年轻有为,林编的自尊就被刺伤了,无奈地说:“你们80后啊,生的年份就是好啊,再怎么混势头都比我们70后的猛,出了成绩也容易被领导发现,得到的扶持也大。我们这些可怜的70后就不如你们了,生的时代特殊,不上不下的,青黄不接。题材全别60后的人写烂了,风头也被80后的给抢走了,我们就像一盆夹生饭,吃不成,看不好,怎么摆弄都不像话。”
“别那么说,我们还需要修炼学习,你们70后现在到丰产期了。”
林编突然想到了什么,问:“唉,你也算是作协的人吧,怎么都没见你去参加新年笔会?”
“这几年我老在外头跑,就前几天才刚刚回来。”
“哦,去采风是吧,都去了什么地方?”林编向来是个旅行热,最大的梦想就是一个人徒步大西北。可因为家庭的牵绊,始终不能如愿,但凡是听见别人说旅行,她就特别的羡慕与好奇。
“我去了甘肃,新疆,内蒙古呼伦湖,然后在北京呆了一年。”杨彦注视着隔离室里的场景,淡淡地说。
“北京的影视业很发达,应该比我们这里好。据说那边聚集了很多作家,他们在那里做影视十分的挣钱,稿费比我们写文章的要高出很多很多……”林编把“很多”重复得很长,她本是被关在笼子里憋疯的金丝雀,被杨彦这么一刺激,价值观瞬间膨胀,对北京充满了理想化赞美。
杨彦不温不火地说:“还行吧,我是想回来发展本土影视。”
“有出息,到时候做出规模了,也带动带动我们这些老大姐。”林编极力套近乎,和杨彦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除了感情方面的失败事情不提以外,宋微澜近段的情况都被她这个漏风的喇叭筒全都如是报道给杨彦听,把她与宋微澜之间的交情说得情深似海。林编在日报社一干就是12年,一直写乡村题材小说的,8年的婚姻生活,她早被生活的琐碎围剿得没了一丝年轻人的特称,一开腔,就像一个吃饱饭在村口大树下纳凉的老大娘,没玩没了,婆婆妈妈。
生死关口(1)
我醒来的那天早上,阳光像蚕丝被一般轻柔地照在我的身上,护士穿着隔离服,只露出一双黑漆漆的眼睛,俯视我,说,你感觉怎么样?
“累……”我艰难地吐出一个字,声音嘶哑。
护士转身出去,在门口大声疾呼:“主任,黎主任,宋微澜醒了!”
不一会儿,有几个人进来,一律穿着隔离服。医生命护士给我进行体征测量,一个拿温度计的护士惊叫:“呀!°发低烧了。”
黎主任舒了一口气,如释重担:“没事了,先给她吊葡萄糖缓一缓,然后再抽肺积液!”
我艰难启齿,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