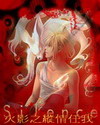������˵-��5����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ҵ�ڰ�������ָ��е�ʵ���൱����������ת�Ʒ���������Բ������������������Ե��г�������ʩ�Ĺ��������������еĹ��е�ͬ������������ת�ƵĹ��ܽ�����ס�����ϣ����ǻ�Ҫ�е���ס���ԵĹ�����Ʒ֧������Զ��Ȼû�ге���������ס���Ĺ��������е��˵�������ȹ���ְ�ܡ�
��������е�����ְ�ܵ����β������г������е����⣬����������Ϊ�Ĺ������Ρ����������г���������ҵ������û������ָ��������ȥ���Ͳ�Ʒ�ļ۸����н�Ӧ������ת�Ƹ����ض���Ӧ�������������Ķ���
�����ص��г���������������ҵ���ṩ�ĸ�����Ʒ��������������������Σ����������Ӧ�ɹ����������������������ͥ��ס���������⣬������������Ʒ�Ĺ�����ʽ�ı���������еIJ��������õ������ͥ�е�ס�����صĸ߶���ý�ֻ�����ӷ����еIJ���ƽ��
�����ղ�����˹����³˹��˵���������������еĽŶ���ͬһ��Ь����Ҳ����ζ�Ų����������е��˶�סͬ���ķ��ӣ�����ͬ������������������ͬ����������Ƹ�����ͼ������ͬ���ġ�Ь�ӡ����������еġ��š�������Ҳͬ����ͽ�͵ġ�
�������й��ĸ�Ů���ԡ����������Ϊ�٣��г����ṩ�����СЬ����ӭ�ϲ����ߵ�������Ů�Ƿ����˲����ϰ��ʱ������������СЬ�Ͳ���ʵ�ˡ����������Ϊ����Ь�IJ����ޣ�ֻ������СЬ���ѻ�û�����ü�����Ľ����¹�����������������Ц���������ǵ��������ڷ����������Ĺ��¡�
����������Ҫʹ�ü�ʮ�����Ʒ����ô�ǰ�����ĵ����ѱ�ȥ��֯���ģ�����������ǰ����е��и���������ȥ��֯�����������ֻͬ������ͨ��ʱ����ƹ滮�ĵ�·��������������ʱ��һ�������в��ò�Ϊ����ʱ���ķ��ٶ���������ؽ������ϼӿ���·�Ĵ��ۡ���������Ҳ�ڴ����ز��20����80�������Ϊ������Ķ�����Ĵ����ͱ�סլ��Ϊʲô�������½�סլ�����и����ѣ��ִ�Ĵ���סլ�����е����������أ��ѵ�һ��Ҫ���µġ�СЬ�������ס���������ⲻ��һ���µ���Դ�˷���
�����ǵ�Сʱ���˹����ҿ����л��ᴩһ˫��Ь����һ�����·��⣬�����ʱ���ǽ�㴩����ԭ�Ǹ��ľ��·����ټ��ϲ���֮���ҡ�
�������Ҽ�����̵��ǣ���һ����������ֵܽ�������ר�ŵ��������ʽ����һ�ź��գ�����������Ƭ�����������Ǹ��Եļ��С�����Ŀ�IJ������Ǵ��ġ��¡��·�������ÿ���˶�����¶�Ž�ֺͷ��Ь��
��������������˲�����Ҫ�����������·��ˣ�ȴ��û�е�������ס���ַ�������ʱ�����ѵ�һ��Ҫ���������ĵİ취���ܽ��ס���������ѵ��ȸ��������˲�Ӧ��ס�Ϻ÷�����ΪʲôΪ�ȸ��������˸Ǻ÷��ӵĿ����̾�һ���ǻ������أ�
�����г����г����£������ṩ��ᱣ���빫����Ʒ���Ȿ�Ƿֹ���ͬ�������£���ÿ�������г�������ʱ�������ܰ�����ᱣ���빫����Ʒ�����г������л����������ƺ��г���ʧ������Ϊ�г�û���ṩ������Ʒ����ᱣ�ϡ��й��ĵ������ͥ�ѵ���Ӧ�����⽻���ý��ס��������
������������ʳ�г���ʱ�������۹����ڴ�ײ��г���ʱ�������۹����ڷ��ӡ�ҽ��������г�����������Ҳ���������ţ�����������Ϊͬһ��ԭ���ֲ����г������������������Ρ����ָ������������ص�Ӱ�����й����г������̡�
����������һ�������ȸ���������ʵ�������Ƿ�����ⶼ����ʵ���ڵģ�����ʵʩ�ԲƸ��ı��������������ȸ������ļ�ͥ�ṩ��������������Ҫ����Ʒ����������ڸǷ��䲻�������⣬Ҳ���������ȸ��������˽��Ƹ�����Ͷ�������ѡ�ͨ���Ϸ������ȸ��������ˣ�Ҳ�ǺϷ����й�����ҲӦ���������������ѵ�Ȩ�����Ƿ��¸�����Ҫ��������Լ������һ���ȸ��������ⲿ�ּ�ͥ��������Ƹ����й�ת���˾��⣬��ôֻ�ܴ����������ʧ������������κ��洦��
�������Ⲣ�������Ѿ���һ���ּ�ͥ�ȸ������ϣ�Ҳ���dz��ڿ����̱���Ϊӭ�ϲ����м�ͥ��������Ʒ���ϡ��������������δ�������ļ�ͥҲ��������������������û�����������г����ķ�ʽ���ס������ʱ����ת��֧���ķ�ʽ������һ�ѣ�������Ҳ�ܹ���������������������Ǹ������Ļ��ᡣ
�����г������г�����Ʒ������Ʒ�������̸ø�ʲô���ӣ����ǻ��ʲô���ӡ�
������2007��1��12�գ�
����������
С�Ǽ���
���ع���Ӱ���ŷ��ۣ������������������ϣ�����������Ϊ���ӹ����������ȶ����ۡ�
����é������ʦ�������˸����ӣ�������ӡ����̣��й����½������ɹ��д��������أ��Ȳ�������Ҫ������ũ�ø��أ�Ҳ������̽��ӵ�п����Դ�ı��أ�Ϊʲô��ֵǮҲû��ȥ���أ�ΪʲôҲû�г�Ϊ�½����еķ������أ�
����������Ҫ�����Ĺ�����Ʒ�����������������������������ز�ֵǮ�����������ϵķ��Ӳ��ڱȽ�֮�����˼۸�IJ�𡣶��������ص����������ģ�Ҳ������ˡ�����ϡΪ��
�������صĹ������ӱ�Ȼ�ٽ���Чס���Ĺ���������������ƽ����Դ�������۸���ȶ����µ��ˡ��г�����ֻ�����������֡������ڹ���Լ۸��Ӱ��֮�䷢�����ã�������Ͷ�ʼ��١����ͣ��ʽ���������ĵ�������ҵת�ơ��ٶ�û��¢�ϵķ��г������أ���ֻ���֡��ͻᷢ��������������ȱ���۸�Ҳ�������徭�õķ�չ��������
�����й��������������ص�¢�Ϲ������в�Ȩ����˲���������˽�л�����һ�����ɵص������ع�������ȱ�����ع������Ķ��پͱ�Ȼ��Է��ӵ��������ͼ۸���������Ӱ�졣
��������˵���ع��������ˣ��������̿�����������֮��ڻ�����������г��з��ӹ������IJ��㣬�Զڻ����ƶ����۵�������
�����ڻ���Լ�м�������ǰ�
����1����Ԥ�����Ч���������ޣ�
����2��Ҫ���㹻���ֽ���֧�ţ�
����3���ڻ���Ŀ����Ҫ����г���ͨ�����٣��Դﵽ¢�����ص�Ŀ�ģ�
����4���ڻ������ս������Ϊ�ڻ�����Ʒ��ֵ��
����Ϊʲôû���˶ڻ������Բ�Ʒ��������֮�ࣩ��Ϊʲôû���˶ڻ���������IJ�Ʒ��Ϊʲôͬ����8��Ǯ��ֵ����Ʊ��ȴ�����ϰ���Ԫ�Ľ��ײ�ۣ�Ϊʲô����Ҫ���չ�������Ŷ���Ϊʲô���˵Ļ��ҵĻ���ֵǮ����ʵ�Ѿ��ڻش���Щ�����ˡ�
�������˵�ִ�ķ��ز��г����п������ڶڻ������뷿�ݣ���˵���Ǵ����Ź���Ӧ�������������صĹ��������õ��Ÿ�ȥ������������Ϊ¢�ϣ��������γɶ���������������ѡ��ֻ������·һ��ȥƴ�۸�����ƶ������ؼ۸�ķ��ǡ�
��������������������־ܾ�������������ж���Ǯ��������������أ������̰�Ǯ�����������ֶڻ�������������������α�������أ����ÿ�������̶�ֻ����һ�����ֶڻ�һ���֣��Ǻô��������أ������ش����������������ص���λ��ֵ��ͬ��ʱ��������ʱ����ȡ�����أ��ֺα��˷��ʽ�ȥ�ڻ��أ�
���������ڶ������������Ҫ��ǰ�������ģ������������ֹ�����ȫ��ͬ��
�����������һЩ�����̶ڻ�����ʱ����������dz�ֵģ���ô��ʱ���и�����ʱ���������г�����������Ϊ���ضڻ�������ʱ���µ�Ͷ�ʽ��벻�������˹�����������ڻ������������ʧ��
�������ǣ���������Ͷ�������������г�ʱ��ȴ��������ȡ�����ص��ż����������棬����γ����������ڵ��˿��ܶڻ����ص���������ǡǡ���õ��ǹ��������ȱ�ݡ�
����Ҳ�����ӹ������Ǵ��ƶڻ�����ð취�����ӹ����Ӵ��˾�������ȻҲ��Լ۸�������Ӱ�죬�����й����øĸ��м۸صĵ�����ȫ��ͬ��
�����¾��²����������������صij�ֹ�����������ӵ������������ÿ����̲��ٶڻ�������˵����������������ǰ�����ᵽ��ǰ����������������DZ�ˮ��н������������𣬷���������ȼ�����á�
�������ڻ����ز������ÿ����̷��ƣ����������ػ�������������ȻҪ���γɽ���֮����ܻ����ʽ�Ͳ����������̶ڻ��������ڴ��ܽ����ظ�ת�ã��������ڴ�����ķ������������ֲ��ʽ�ռ�õ���ʧ���������ع�����֡����Ӷ��ˡ����۲��ǻ��Ƿ����ڳɱ�ʱ���������˶ڻ�������
����û�л���ǰ������ۣ���ֻ����Ϊ��С�Ǽ����ˡ�
������С����ȥ�ж�Ͷ���ߵ��ǻۣ�ǡǡ��һȺ���е��������г�Ҫ������Щ��������������Ͳ����д���������ˣ�
������2007��3��6�գ�
����
����������Ϊ���У�1��
��2002��֮���й��ķ��ز�ҵ��������������ĸ��ֵ��أ����а������������������Դ�ʩ���������е�����������������������ز��������ι������������ι���
�������ټ������£�
����һ���ҹ���û���йؾ�������ס�������ʡ���λ�������빩����ʽ���������������ز����������������Ĺ涨�����������Ժ��Ȩȷ�������õغͷ���Ʒ������ᱣ����ס�����ߡ���Щ���߷�������Ʒ�������ܡ����ز����������Ĺ�Ͻ����Ȼ������ס�������乩�����ߣ�����������ģ�������ṹ�����������һϵ������������
����������Ժ����ع����в�û����ȷ�涨��������ס��ת��֮������÷��ɡ���������ס����������ʱ�����ݹ���Ժ�������������ŵ��������£�����ʵ���ϣ�����������ִ���ж�ͨ��ת�ø�����������������ġ������������ĵض��ˡ����������þ�������ס����ת�ú�������Ʒ������ô���������������˭��Ȩ���ĸ����ɸ��豣�����أ�
���������������ס����Ȼ�ڻ����������ϣ��������ת�ö����ı��������ʻ����������Ŀ���֮��ѭ�����������з��ɹ�Ͻ����ֻ�ܷ�����Ȩ�Ĺ����������¹�Ͻ�����ˡ������Ҫ�ı��������ʣ�תΪ��������Ʒ���ķ��ɹ�Ͻʱ����Ӧ����һ���������ݡ�
���������ز������������жԻ��������Ϸ��ݲ�Ȩת�õ���ȷ�涨�����л������ؿ���תΪ�������غͽ�����Ʒ�����Ĺ涨������ǰ�ᶼ�ǽ��������ɻ����õ�תΪ�����õأ�������ʮ��������
��������������ס����ת�ú�����Ʒ���Ĺ����У����ǰ��˷��ɹ涨������Ҳ���������˹涨��ȡ�˲��������س��ý������𣬵����س��ø�˭���أ����س��ú�ͬ�ķ��������أ�
������������ס�������Ʒ����ת�����ɹ涨���Ȳ��Ƿ�����ߣ�Ҳ���ǵ��淿�ߡ�����Ȩ��������ר�ŵġ�ҵ���Ľ�������������Ȩ���͡������õ�ʹ��Ȩ�����½ڣ����Ҳ��������������ʵķ��ݹ���һ�صķ��ɣ�Ҳ��֪��������ֽ����������������ʵķ��ݵĹ��в��֣����ֲ�ͬ���ʵ������뽨����Ȩ���Ƿ���Ȳ��ɻ�ϣ�Ҳ��֪�������õ�ʹ��Ȩ֤��α����ת�����ջء�
������֮���ҹ���û��һ����ᱣ����ס����ɢ�ķ��ɣ�������ȫ�ı�����ʹ�����ʲ�ʹ֮��������ص���Ʒ��ס���ӹ졣����ʵ���������ȴ���ط������ձ鷢���������ι�Ҳ�ͱ�������ι��ˡ�
�����������۸��жԹ��Ҽ۸������Ȩ���������ϸ���������й�����������������Ȩ������ָ����Ȩ��Ҳͬ�����г�����Ȩ����ô�������ݷ�����Ʒ�۸�����ķ���Ӧ��˾��ְ���ϸ����ط��ɹ涨��
���������۸��⣬���С����ز����������ͽ��貿�ġ�88�������Ʒ���۸�Ĺ������������Ĺ涨��������ȷ�ؿ������й�������ϵ�е���Ʒ���۸������ȫ���г����ڼ۵Ĺ����ƶȣ�Ҳ����˵����Ʒ�����г����ڵ����ɶ���Ȩ�����������Ը������ɽ���������Ԥ��
�����г��е��ʲ��۸���������ǿ�����۶������仯���������ƵĹ���۸��Ƕ��٣�ӵ����ʵ��ӵ�е�ס���ʲ��۸��䣬�������õͼ۸������Ÿ��ʲ���Ȩ�������ҿ���ͨ��ת���ٻ�ԭ�ʲ��۸��������
���������صļ�ֵ�����Ҳ�����б�ʱ�������õ�����ߵ����س��ü۸��Ⲣ��Ӱ�����ؼ�ֵ��ʵ�֡������ص�������ֵ�����Ǵ����������������֣�������ǿ��������ͽ��������ļ�ֵ�������ۻ��������ʦ�Ĵ����Ժ�Ͷ���ߵĻ����ԣ���������������ȥ�ھ����ص�����ֵ����������������ʧ������Ϊ������ص��۶�ƽ�����ܱ����صļ�ֵ��
�������۷����˼�ֵ����ʱ���۸�Ͳ�����г������������ã���ô���ַ����ֻ�Ծ�����ʲô�����ƶ������أ�Ҫ��Ҫ�г����þͳ���Ӱ���й��ĸ﷽����ش������ˡ�
��������Ϊ��ֹ���ʽ����й����ز�ҵ��ijЩ����Ϊ���ۻ���Ϊ����˹��������ǵľ�����������������������ʹ����İ취������һЩ���ž����ϻ��·���һϵ�е��ļ����������뿴����
����������Ϊ���У�2��
������ܾ��뽨�貿�����ڹ淶���ز��г��������й������֪ͨ�������ǡ����ڹ淶���ز��г������������������ȣ����ļ���ȴ���������������й����з��������͵����ʡ�
�������磬�ҹ��ķ������Ĺ涨�������������ھ��������ķ�֧�������������������»������ǰ���˾�������ʷ������ģ���û�з��˵�λ��Ҳ������Ȼ�ˣ�
����ͬʱ�涨�������Ǽǵ�Ȩ����Ӧ�з��˻���Ȼ�˵ĵ�λ����ô��Щû�з��˵�λ�ľ�������ķ�֧�����������������γ��з��ݵIJ�����Ȩ�أ�
�����������������Щ�Ƿ��˻������в�����������Щ�������������þ�������Ҫͨ���й���˾��������豣��ʱ��û�з��˵�λ�ķ�֧������������������ͨ����Ժ�������������أ������Щ��֧���